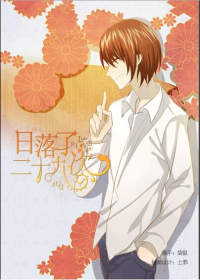��:���������-��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Ҳ����Ժ����������������
������������һ�Բ��������߹�һȦ����ÿ������һ��ƽ�Ȼ�����˸������������ƣ��Լ������յ�����������˵�������������λ�������˱������գ�һ�ɶ�������������
�����������������û�ж���ֻ��������ĬĬ�������˱��еľơ���������
�������������ּ�����ش��������˵������ʿ��ڮ�����ģ����Ľ���ɱ֮����Τִ��ų�����ң�������Τ��֮����в��¸���ģ�����������ն֮��Τ���ֲ�ͬ�⡣�����������������ˣ�ÿ�뵽����������ͽ��ң���⣬���в��졣����������
�����������˲�֪�����к����ģ�����˵����Ω�������䡰�ߡ���һ������������
�����������IJ�����ɫ������˵�������������ж�֧������ʹ������������Ϊ����Ϊ���������������ִ�������Ǯ�����ʹ��ã���ν��Ŀ���á�����������
���������������ϵ��˿����IJ��Ұ��Լ���ô����վ����������Ļ����������˴��Ժ��������Դ��˳��ζ�֧������һ���Բ���Ϊ�⣬�����������﹫����ѣ����ơ����������������Ц̸������������
���������������������������治���ݣ�������������Ϊ����������һ������ת������䣬��������������Ķ����Ɑ�����������״�������ش��ͷ���¡���������
��������������˵��������ĸ�ײ��أ���Ϊ���ι��£���������ҽҩ�����������ղ��ò���ٹ��̣�����Ϊ�����ľ���������Σ�ѣ���Ϊ���ұ������ѡ�һ����ְ���ٰ���������ʱ��֪˭�ܼ�����ģ���һ����������������
�����������������̲�ס�������˼��Գ�Ϊ�����ģ��ֺ������˻ٰ���������������
������������û����˵ʲô��ֻ�Dz�ͣ��Ȱ�ƣ���������Ҳ��˵��������������ޣ��������µ����������ļ���������������˽�һ�˵�����ĸ��������������˼������Ⱦƣ�����һ�˵�����˵�����ǡ�����λ�������������Ҳ��ȥ�ˣ���æ�������ĵظ�֪�����䡣����һ����������Ȼ����������
���������ڶ��죬�����ֹʼ����ݣ����ڻ¹������뵽����Ժ������һ�Σ�����ȴ������������ôǫ���º��ˣ�������������һ��ɱ�������ھ�����ֻ˵��һ�䣺��������
��������������ר����֪��λ��ʥ������ҵ�ѻָ����˿����ڻ�Է�����ã�������ɣ�һ�統�ꡣ������������ն������������
��������˵�꣬�����ȥ��������������һ��ǰ��δ�е�����С��������������˶��е����������ѿ�ʼ��עһ�������������ã����㻹��ʲô���У����¹��������֡���������
������������ʮ���գ�����������������ĸɥȥְ����������ұ㣬�����˶��ּ��졣��������
�������������dz������Σ��������������˺����ʮ�������ҹҹ����ĺ����������衢�����˿�˼�Ʋߣ�ϣ���ܹ���ְ��Τִ�����ڿ����˲����Ѿ���������������ֻ������������ַ�����һ��ͨ�����е�������һ�ɣ������ڲ��ص�˳����Ϊ���Ӳд����������һ�������������ӣ���ȡһЩ������֧�֡�����������һ�ƻ�����Ҫ��������������ÿ�������ڹ��кͶ��Ӹ���������������Ϊ���ࡢ���챱���������Ȼ��ͽȻ�������ֽ���Ϊ��Զ��ʹ���조ƽ���¡�����δ������������£���������λ�����������������Ҫְ�����һ���ӵ����Ȩ�����С�����ɵ�һ�����ˣ�������������˵�ʱ�̱�¶����ȱ������������ȱ�㣬���������ڱ���������Ҫ���ܡ����죬�����Ŵ�����û�л�Ӧ���ں���Ժ�ȵ�ҹ���Ȼ�������£����не����������з��ˣ������з��ˣ����ڶ���������լ���Ӵ˱��Ų�������������
���������ڶ��Ӻ����θ�ʹ���������¹����Ļ��ר�ҳ����ǵ�һ���ܺ��ߣ���ȥ��ʾ��ְ�������Ķ����ϳ���͢����Ϊ������������������
��������ʱ�䵽�����£��ھ�������˿�����ʱ���Ѿ������ˡ�̫�ӵ���˼Ҳ����ȷ��Ŀǰ�ѵ��˽�����в����������ʱ�䡣���������һ�ϼƣ����������з�����Ԯ�����г���֧�֣�������߾����֣�������ʧ������̫��Ӣ����ǣ���Ϊ���֣������¾����ˡ���������
��������������Ѯ�������ǹ��е��˷����������̼����ϵ�����������ͻȻ��ʧ�ˣ���Ҳû��¶���档����˵�����ز����������ڵ�Ϧ�����������ϵij���ţ����Ҳ��ʧ���ټ���������Ҳû�п�������ֻ�Ƿ��ֹ��е�һ���Ե�����������κ��˶��������ڡ���������Щ����û������ʲô�����ע�⡣��������
��������������Ѯ��һ�죬����ѧʿ֣�s�����ι������ĵ��˷�گ�빬����̫���������䡢��������Ѧӯ�䡢Ѧ�������������ǣ������Ļ���һλ���������������䡣������Ժ���ѧʿ����������������ּ����̫��Ȩ�����������¡�����λѧʿ���̲���گھ������������
�����������¶�ʮ���գ�گ�鷢�¡��ٹ��ڶ����ó���̫�ӣ�̫�ӿ�����������ʥ��δ��������Ȩ����Ƕ��ѣ��Ͳ���ٹ��İݺ��ˡ�Ⱥ������������������
��������
��һ�¡������ģ�Ǭ��һ���������ģ�Ǭ��һ���壨8��
���������ˡ�������
��������̫��վ�ڸ����ǰ����������һ�ˣ����������һ�˽�������������
�������������Ѿ����ܶ����Ļʵۣ�̫������˼����ǧ������ʱ����������Ϊʲô���ϳٳ����Ӳ��������ļ̳��ˣ����������ӣ��κ��˶�����Ю�����������£����ο���Щ����������λ�ճ��ӵ�С���أ��뵽�ˣ�̫�Ӳ���ҧ���гݣ��������ģ����ĩ�յ��ˣ�����������
������������һ���ˣ�̫�Ӷ������Dz����жȹ����ز������ĸ����ܹ�˳���ǻ�ֻ��������������һ�������������ţ�ʵ�ڵ�Σ��ȴ����ǰ�������أ���Ȼ�����赲���Ϸ�����Ӵ�λ�������������ʹ�ȥ���Һã������µ�Ŭ���ı�����һ״������ȥ�����Ŀ���ֻ��һ�����µ����ʶ��ѡ�̫��֪����Ҫ�ﵽĿ�Ļ���һЩ�ϰ�����������������е�һ�ж��Ѿ�����η���ˡ�̫�ӵľ������¡���������
�����������¶�ʮ���գ�����µ���ͤ��̫�ӳ�����ʹ�����������Ѹ������𢣬��ʼ��Ȩ�����������¡��Ĺ�������̫�ӵ��ص���Ȼ�����ڴˣ�������һ�������ʱ���ﶼ�����Ŀɿ�֧�����ȵ۵��ڵ���ʹ���ˡ�����������߽����Ļ¹������ܻ��̣�������һ����Ҳ�Ǿ�����һ���ľ����ʩ����̫�Ӹе���ο���ǣ����л������ߵ����̶�һ����Ϊ�����ϵ����强����֧�֣����ϱ���Ҳ���ѡ��������������ǻ�˵�����аٹٴӹ�����������Ҳ�Ѿ��ױ�ʾ������������ˣ��ƺ��������ڵ۹�����Ŀǰ����������״����������
����������Ԫ��ʮһ�꣨��Ԫ805�꣩���³�����̫�Ӽ������������ҹ�̫�Ӻ��������Ŷ������������䡢��ͻ��譼�����һҹ���¡��ڶ��죬��λ�����������������������ʡ�����˰��գ��������磬����ѧʿ����һ�α����빬���ڻ��ϵ���̫��������˾����������Ļʵ�گ�������³��ģ������˻��ϵ���λگ����������
��������گ��˵������اҵ�������Ϲ���λ������Ͼ�ݣ�Ȼ���ӷ˽������������ܷ�����֮�飬ʵʵ���������ġ���һ����������Ծÿ����칤�˴������Ծ�Υ�������̫�Ӽ��ʵ�λ����̫�ϻʣ������칬������˾�����в���������
���������������գ�����̫�ϻʵ�˳����ʽ�����ֻ�����߸��µĻʵ۱��������ڲ����ϣ��ڹ����ǵĴ�ӵ��Ǩ�����칬�����칬λ�ڳ����������DZ��������ڻʵ����ã����ڴ��������ʳ��е�̫����֮�ϣ��ֳ����ڡ�˳�ڵ�������Ȼ�ѳ��ر�����������̧�����еĻ������¥ʱ���ƺ�������Щʲô��������δ��ȫʧЧ�����Ǹ��������Լ������������ص��Ⱥ���������˳��ͻȻ�����䶯�����壬�������һ��ģ����������������Ѿ�̫���ˡ��м�λ���е�������������һ�У�ʹ��ص�����ͷ����������
�����������죬̫�ϻ�����ھ����̫�����ڱ��¾��ռ�λ������Ԫ�����ꡱ���������¡���������
����������δ�����գ��������켴����������Ϊ����˾����������Ϊ����˾�������䷢Dz�����ݺ��������طֱ�ྩ��һǧ�İ���ʮ��Ͷ�ǧ�߰���ʮ�����������
�����������¾��գ�̫����ʽ���ʵ�λ����ʷ�ϳ�֮Ϊ�����ڡ�����Ϊ��������δ������̫�ϻ��������칬��̫�������ǰ�Ԫ�λ����ʾ�Զ�λ�Ȼʵ۵ij羴����������
������������ʮ���գ��µ�گ������о�˾����̩Ϊ���ݴ�ʷ��˾�����к���Ϊ���ݴ�ʷ����Ա��������ԪΪ���ݴ�ʷ������Ա����������Ϊ���ݴ�ʷ����������
��������������´��������Ŀ�������û����ȥ���ĵ۹��Ĺ�͢�о���������ʲô�¡������鷢����̫��̫�����ˣ������в��ٴ��������˾����⡣��������
��������������Ѯ��һ�죬��һ�����ĵشӾ��������������������¤�Ҿ���ʹ���ѣ��Գ���ɽҰ��ʿ��������������һ�����춯�صĴ�����档��������
��������������˳����λ��̫�ϻʲ��ã����Ѻ����У�����ʿ�������������������
��������������Ӿ��ж�����ר��ʹ����������������������
������������һ�𣬺ȵ�����ɽ����������ԣ��˻�����������������
����������������̫����گ������������
������������گ���ڣ�����������
�����������³����Σ�̫��ֻʹ�����Ͷ��ѡ�����������
��������������νб�ʹ���ţ�����������
����������������Ȼ���ԣ�������������ʵ��̫���²����ѣ����������ı��Թ�������ӵ����Ȩ�������ҵ��ϵ��һ����̫����֪ʹ������Т�£�������˳֮�����ʽ�������Σ������ʹ����گ��ʹ�������з���֮�¡�����������
�������������������Ǿ�����֣����������Լ�������ƽ����˵����Ȼ��������Σ�����������
����������ʹ������ƹ�����������¶��ɫ����������
����������������Ѿ����Բ��������֣�ֻ�������������Ļ��˼����֡���������
�������������Ѹо������ˣ��������͵�һ������ˮ���ܶ��£��������������ǵ�ʧ��һ�ּ�ֱ���DZ��ܵķ�Ӧ��ʹ��һ�ļ���������ͽ������������˵�����ң��������£�����ʱ���м��������ֳ��������������������
���������������������ѣ����Ҫ������������㸲�������ǧ�����ˣ�����������
��������������һɲ�Ǽ䣬������Ȩ����ˣ���ʵҲ�������ã����ɵ������Աȱ���һĿ��Ȼ�����Ѳ��Ǹ�ɵ�ϡ���������
�������������ң��������̣���������ָʹ֮�ˣ�����������
������������֪������û�гɹ���һ�ֱ����ӿ����ͷ�����͵������˰�ס���ı�ʿ������˵���������ö��̣�����ij�����������ˣ����ھͿ��Ը����㣬�ҵ�ͬ־���࣬Լ�����Ǩ��ʱ����������̫��ּ֮�������֪����Ҳû���ã�����������
�����������Ѵ������ϼӿ��ܣ���������ҹ���䱨�ų�����������������ɫ�����ˡ���������
��������δ�����죬������Ѻ�����ǣ������ִ����Ѳ��������ʮ�������ɷ��ӣ�����ȫ����ɱ����������
��������ʮ�³��������������е��ڻʵ���̴�ͳ�����������������伣�����ͻȻ������ȥ�����µ۷ϳ����ա���������
��������ʮ���գ���ǰ�ᡰ����Т�Ļʵۡ��ڳ��꣬���š����ڡ�����������
�������������Դ���һƬ����֮�У��������»�Ȼ������������Щ���Ų�������Ĭ����ij�͢�س���������õ�ʧ�����Ƿ׳��棬���ʤ��������˭Ҳ˵��������ʤ���Ƿ����������Լ���һ�еIJ�����Թ���������Ҫ��й�������ϵı仯���������Ի��ᣬ����Ⱥ�Է��ڣ������ָ�������ڱ����������������Ա���ϣ����ֹ�������˵�ͬ��Э���������ڴ�ʱ�˿����е��ж����Ե�����ô�ĺ����������������ƺ���Щ����������һЩ���¡���������
��������Τִ��ֻ�г�Ĭ��Ԭ�̺����������Ż����ѱ�ί��Ϊ���࣬���������µ���ʱ��û�а�����λ��͢��ǰ��һ��һ����������������ÿ����ڣ����������ð칫����ȥ��Ӣ��͢�ԣ�����������Ϊ�Լ������������ĵķ��������ܰ����ȹ��ѹأ���������Ҳ������Dz����ܵģ����صijͷ�Ҳ��ֻ��ʱ�����⡣Τִ��ÿ�춼�ڼ��ȵ����а�����������������ָ��ʹ�ѱ���˴���������ɫ������ΩΩŵŵ������������ɫ���ͻ̼�ʧ̬����ȫʧȥ�˹��Ҵ�Ӧ�����ȡ��������������������ӣ�����ҪΪ�����ѵ���Ҳ�е������⡣��������
����������һ�첻�ɱ����������ʮһ�³��ߣ�Τִ��������Ϊ����˾������������
��������ʮ���գ���Ϊ������Ϊ��������Ա����̫�ᣬ�µ��ٱẫ̩Ϊ���˾��������Ϊ����˾����������Ϊ����˾�����ֱ������������Ϊ̨��˾�������ݴ�ʷ��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