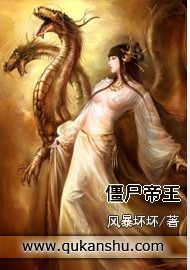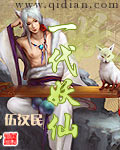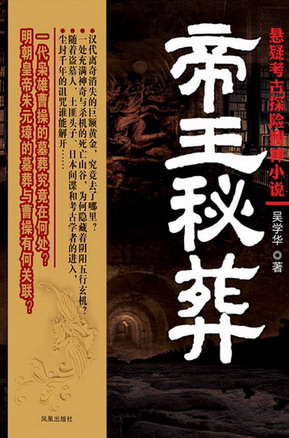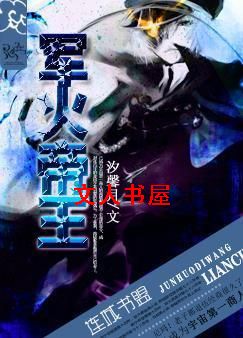一代帝王刘义隆-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人合成了一股绳。这样,殷景仁和刘湛的位置倒置了。
司徒义康原本对殷景仁并无成见,但随着刘湛一次次颇似有理的进言——毕竟人的耳朵是软的,他渐渐觉得殷的权力过大也并非什么好事。殷和自己多少还是有距离的。在自己极力主张对谢灵运处以极刑的时候,殷就和皇上站在一起;颜延之以诗来蛊惑人心,他又以诗人已年过半百为由反对让颜出外任——年过半百出外任的又何止一个两个。再说,从处理政事的角度看,刘湛也并不比殷差;从谋略角度看,刘湛还有过人之处。
当殷景仁的主张被司徒一次次地以“不宜”为由加以拒绝的时候,殷景仁感觉到了他们二人合成一股绳后实在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不仅如此,他也逐渐感觉到了过去自己对刘湛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皇上病重期间,他曾无奈地对身边人说:“引了刘入,入便咬人!”这时候,他就有了悔不当初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湛和殷景仁的关系已经渐渐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紧相追随刘湛的刘斌、刘敬文等人为了遵循主子的意旨甚至私下相互约束: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踏入殷府!但事隔不久,司徒府主簿刘敬文的父亲刘成却未能领悟其旨,他独自驾着牛车前往殷府向兼任吏部尚书的殷景仁求任吴郡太守这一肥缺。那天傍晚,当刘敬文刚到家门口听说此事后,也来不及走进家门,就急忙跑回领军府向主子谢罪:
“老父昏悖,竟然到殷铁府求郡。这等事实在是由敬文浅暗,上负府公养育之恩,合门惭惧,无地自容!”
刘湛闻知此事,虽然心中不免恼怒,但看到刘敬文诚惶诚恐,能对自己忠心如此,很快就化怒为喜:有此诸人,何事不办!于是他转而宽慰刘敬文,要他回家后不要难为了老父,或许事出有因也未可知。
领军府的人不再到殷府上来,殷府的人也很快觉察到了。作为回报,殷府的人也都不再前往领军府。后来扩而广之,不属于两府的官员,喜欢登殷府的人,领军府对他们冷眼相看;反之,喜欢去领军府的人,在殷府也不受欢迎。
随着自己的主张和建议一次次地被否定,尤其是知道了司徒称诏召檀道济入京这事后,殷景仁似乎已经嗅出了京都建康周围空气中有股不祥的异味,只是他还不能确定这异味究竟是一股什么气味。虽然他还不能确定将会生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肯定会生什么,这似乎已变得不可逆转。
皇上的病况有了好转,今天还能到东府城去走一走。这下好了,也许前些日子的担忧只是多余的,毕竟,司徒和皇上是有着手足情的亲兄弟,他人都是外人,自己也是。但现在皇上既然身体已有所好转,如果将来事态真的会向不可知的方向展且不可逆转,那么自己何不在这个时候全身引退?
皇上从东府城回来的第二天,殷景仁就把称病求退的表疏放在了皇上的案头。
殷景仁有病?什么病至于要上表归田?他的表疏大大出乎刘义隆之所料。数年来,他一直深受皇上的信任,甚至可以说,皇上对他都有些依赖了:无论大事小事,有了殷景仁,皇上就觉得可以放心了。现在怎么就突然求退?司徒和刘湛也都说在自己病重期间殷景仁有诸多不作为,莫非他的求退与此有关?
但无论如何,殷景仁是股肱之臣,失去了他的朝政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的表疏虽上,但没有得到皇上的许可。
其后数日,殷景仁表疏屡上,都没有被接受。
就在刘义隆看着殷景仁求退的表疏愁闷不解的时候,中书舍人通报:司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檀道济求见。
“檀将军?”刘义隆听报一惊,“檀将军何故入京?”
待檀道济进入了太极殿,身体仍很虚弱的刘义隆一见他就硬撑着要从病榻上坐起来;檀道济和侍臣连忙上前把皇上扶起来。刘义隆连咳了几声,这才带着气喘问:
“将军何时入京?何故入京?”
未等檀道济回答,略显惊慌的刘湛从司徒旁向前一步,抢先回答:
“将军特意入京问疾,是暂时入京。现在就要离开了。”
听罢此言,僵愣在一旁的司徒这才把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放了下来。但刘义隆显然流露出了对刘湛多言的不满,于是就又对檀道济说:
“使将军镇守寻阳,名号征南大将军,实托南部江山,以备国家非常之事。将军是自来京,还是有人召将军入京?”
檀道济看一眼侍立于侧的司徒和刘湛,也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只得答道:
“臣离京数载,知陛下龙体欠安,思慕得很……牵挂得很。臣拜见了陛下就将离京返镇。”
拜见了皇上,檀道济并没有当即离京返镇。出了太极殿,刘湛以受司徒之托为名要他留下来有要事相商,让他暂时在京都的檀府里等候着司徒的吩咐。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司徒也并没有约见他,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这样他就在府中和留任京都的诸子以及孙辈们共享天伦之乐。
第六十一章 刺客盯上了大臣殷景仁
也许是刘湛等人的安排天衣无缝,他们对檀道济将要作出的处置没有在朝廷文武百官中引起一丝半点的猜测,甚至连任职宫中的檀道济的长子、给事黄门侍郎檀植和檀道济的次子、任职于东府城的司徒从事中郎檀粲也未能有半点觉察,虽然他们也都感觉到朝廷近期或有变故,因为领军将军刘湛对司徒的紧相追随以及中书令、护军将军殷景仁的屡次上书求退,都让他们觉得事态的不同寻常。。
这时皇上虽然仍很虚弱,但皇上清醒着,这样檀道济的事就被暂时搁置了起来。因此朝内朝外,看上去仍是一片风平浪静。
在这一片风平浪静的外衣下,刘湛等人却并没有停止他们前进的步伐。
为了进一步排除路障,元嘉十二年底,刘湛与刘斌等人密谋,准备趁现在皇上心力不济的间隙,在殷景仁来往于台城的路上,派遣刺客数人像拦路打劫那样刺死殷景仁。此事若能成,事后皇上即使知道了,一方面皇上本人心力虚损无法过问,另一方面,有司徒从中周旋——刺杀殷的事,皇上一定会把它交给司徒来处理——一旦由司徒来处理此事,那么一切都将大事化下小事化了。即使不让司徒来处理,此事多少会牵涉到司徒府,那时,皇上也一定不会伤及与兄弟之间的至亲之爱。那样的话,则大功告成。
接下来的事就是寻找几个能干的刺客了。寻找刺客这个任务,按照刘湛的吩咐,由刘斌亲自去执行。
不几天工夫,刘斌在京郊建康县找到了第一个刺客。当这个刺客在殷景仁来去的必经之路边蹲守察看的时候,他犹豫了,胆怯了:这样的仪仗队,要多少人才可以来对付?要像张良当年在博浪沙用大力刺客去锤杀秦始皇那样吗?自己不是那样的大力刺客,更何况是在京都熙来攘往的大白天!再说,张良当年也没有成功。不但具体的操作过程难度太大,换一个角度看,自己要去刺杀的人是皇上身边的得力大臣,此事如果不成,追究起来,岂不是要招来灭门之祸!自己怎能为一个不甚相知的刘斌而去以一家百口作赌注?但转而一想,这样的密事,刘斌托人找到自己,可以掂量出其中的分量;行刺之事固然不可贸然行事,但刘斌为人心狠手辣,同样不能得罪。于是在刘斌的再三催促下,那人在第六次踩点观察后,从此失去了行踪。
这件事让刘斌窝了一肚子火,但又不好随意作,只能再找其次。
不几天,他又通过手下找到了一个正在服苦役的刑徒。那刑徒正苦于刑期的漫长,一听有人要重用他,巴不得就此能脱离了苦海,于是满口答应了:冒死一赌,或可换来荣华富贵也未可知!那刑徒原本就是个酒色之徒,当初就是因为酗酒闹事砸死了人才坐了大牢,如今从众刑徒中走出来,依然不改他的英雄本色,只顾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全然不顾为什么有人要保他出来。几天之后,有人催促他了,他这才打着酒嗝去殷景仁的必经之路旁看了一两回。像所有的酒鬼一样,他的那张嘴往往不受他本人的控制:三碗五碗酒下肚之后,他甚至能和酒店里的吃客聊起他的辉煌史,甚至能把他被人保举出来的原由和盘托出。听众听了都半信半疑,有人以为他在说胡话,也有人把他的话就此传了出去,尤其是他说到的怎样对付殷的仪仗队的话更是让人震惊而好奇,也因此这个内容被传的更远更广。
这话传到了刘湛的耳中,刘湛也感到震惊且恼怒了,但他只能把刘斌大骂一通别无它法;刘斌被骂的结果,是那个酒鬼从此也在京都消失了。
这话很快也传到了皇上的耳中——皇上是从潘美人的口中得知的,皇上也震惊了。皇上震惊的结果,是他意外地恩准了殷景仁的表疏;当然,这一恩准只是部分意义上的恩准:在家静养,不得解职;同时诏令以殷家为护军府,不久又下诏使黄门侍郎每日到殷府去探视殷景仁。
这时候刘义隆似乎才看出了殷景仁求退的隐衷,而风闻在皇城里竟然会有刺客想谋杀朝廷大臣之事,他就生出了些不祥的预感。
过了几天,刘义隆又作出了进一步的决定来确保殷景仁的安全:把殷家迁到西掖门外晋代鄱阳公主的豪宅,并以此豪宅为护军府。此宅原是晋帝因娇惯鄱阳公主而特意建造的,它离宫中近,这样来往方便。现在既作了殷景仁的护军府,加之台城原本就警卫森严,这样纵有再大的本领,要想突破一重重关卡,那无异于徒手登天。
刺客之计虽告失败,但它毕竟让殷景仁离开了皇上,这多多少少也遂了刘湛的一些心愿。
第六十二章 一代名将檀道济惨遭杀害
宫内的事情该告一段落了,而宫外最让刘湛担忧的,就是手握重兵的司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檀道济了。。
到了元嘉十三年初春,因偶感风寒,刘义隆再一次昏厥过去,竟至于三日不醒。见此情状,刘湛就建议司徒不如打走钱塘御医陈一旬,让他收拾行囊回他的钱塘老家去,因为这一次皇上的病情似乎不同寻常,与其捱着时日,倒不如听之任之。司徒义康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在司徒看来,皇上虽再一次昏厥不醒,但御医陈一旬的医术是不容置疑的,将来自己也许还会用得着他。当然,司徒没能悟出刘湛的良苦用心,刘湛的本心是绝不在于宫中会多一个或少一个钱塘御医的。
皇上昏厥的消息被封锁着。
檀道济在京城已经逗留了数十个日子。北虏再无什么动静,皇上的身体又日渐康复,檀道济呆在府上无所事事,就有了一种虚度的感觉,他想回寻阳去了。他想再一次入宫和皇上话别,无奈司徒一方面让他在府上静养些时日,另一方面又告诉皇上他已经回了寻阳。这让他想入宫去和皇上话别也没有了可能。
就在皇上连续昏厥的第三天的傍晚时分,檀道济的大队人马已经把行装全都搬运到了一条条船上,檀道济也已经站在了华贵的平乘船头。他们就要离京了,岸上是来为他送行的他的儿子和朝廷的一些文武官员。他们或抱拳或摆手,不停地向他致意。
就在这个时候,船头、岸上的人们都一致掉转方向看着一彪人马飞驰而来,那领头的正是刘斌。刘斌快靠近檀道济那只平乘船所在的岸边,向檀道济说明了来意:皇上从上午起已经昏厥了好几个时辰,到现在仍不见好转,为防不测,司徒让檀将军入宫。
一听说皇上又昏厥过去了,一向对皇上忠心耿耿的檀将军立即怀着沉痛的心情离船回到了岸边,然后坐上车随刘斌向宫中驰去。
但是,檀道济的车子没有进入宫中。走不多远,几个五大三粗的武士就把他捆绑起来,然后押送到了廷尉。
刘斌令狱卒快关押并锁好了檀道济,自己却站立在暗处,他甚至不敢看一眼檀道济。一旦锁好了狱门,刘斌亲自把钥匙装在身上,然后又从口袋外面捏了捏,生怕出了什么意外,这才快步离开了监牢。
在他的背后,回荡着檀道济令人恐惧的吼声:
“我要见皇上——,我要见皇上——”
这一回,千万不要再有什么意外出现,不论皇上能不能再醒过来,司徒义康和刘湛都一致认为应该快刀斩乱麻,不要再节外生枝。因此,被莫名其妙地投入狱中的檀道济还未来得及吃一点苦头,当然也还未有一点机会向皇上声辩,甚至就在他的吼声还没有完全散尽的时候,一份由刘湛代拟的诏书就被刘斌亲自送达廷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