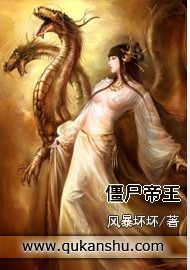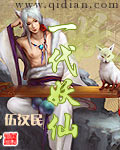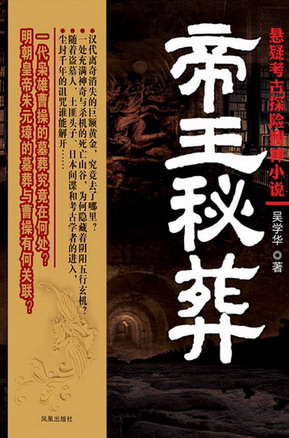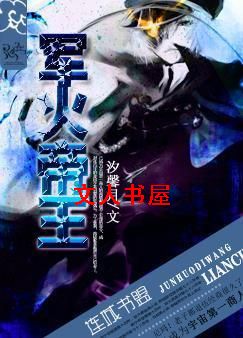一代帝王刘义隆-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若真如此,甚佳。湛为人多猜忌,不可令其万一觉察。你年已长,应渐谙世事;况且群情瞩望,不再以幼弱视你,你何故常如十岁时,动辄上表咨问?但你之所专,常是小事,湛之疑忌,兼或由此而生?”
江夏王义恭与刘湛不睦的事情还没完了,皇上的堂兄、尚书左仆射临川王刘义庆又呈上表疏请求出京外任,原因是太白星犯右执法,星象家占星的结果是:执法者死。
在星相家眼中,天上南蕃中二星之间被称作端门,其东叫左执法,是朝廷廷尉之象;其西叫右执法,是御史大夫之象。执法,指的就是负责举刺凶奸的执政者。尚书仆射是尚书令的副手,尚书令的职位空缺,尚书左仆射就行使尚书令的职权。这时,临川王正担任左仆射这个职务。自古以来,人们历来重视星象的变化与人世吉凶的关系,此前二年,王弘坚辞要职以让给彭城王义康,虽也因他的心中有居高之忧,但也确是因天下大旱,而星相家认为这是因朝廷用人不当,是“寇窃非据,谪见于天”所引起的。
见了临川王的表疏,刘义隆就下诏召见了他。
临川王是刘义隆所尊敬的兄长,他原来是先帝中弟长沙王刘道怜的次子,因先帝少弟临川王刘道规膝下无子,于是就把他过继给临川王作继嗣,后来袭封临川王爵位。起初,先帝曾把刘义隆过继给临川王作继嗣,后来先帝封宋王,刘义隆还本,而“礼无二继”,于是以长沙王次子刘义庆作继嗣。也因有了这层关系,刘义隆就和刘义庆的感情就更近了一层;当然,他们的感情亲近,也与刘义庆的为人值得尊敬有关。
在太极西堂,刘义隆以家人礼款待刘义庆,并以“兄”称呼他——刘义庆比刘义隆年长四岁。在陈说了观天象以为太白星犯右执法,是执法者死的征兆后,刘义庆恳请解除自己的尚书左仆射这一职务,希望出京外任。
刘义隆向他的坐席挪了挪,说:
“天象渺茫,难以明了。星相家认为太白星犯右执法,执法者死,但诸家所占,各有异同。太白星犯右执法,有人占为‘有边兵’,有人占为‘将军死,近臣去’,有人占为‘天下饥,仓粟少’,现在又有人占为‘执法者死’。观察天象来推断人世吉凶,这往往在可信可不信之间。太白星犯右执法,占星结果既如此,但看看从前,也应无所忧惧:三年前,以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郑鲜之担任右仆射,过了一年,郑仆射年六十因病而亡,并无星象互犯之事;郑仆射亡后,左执法曾有变化,按照占星者所言,该由王光禄当之,但王光禄年过七旬,至今平安。日蚀三朝,天下之大忌,晋孝武帝初年也曾有此凶兆,但最终也平安。天道在于辅仁福善,仁善之事多行,就不必横生忧惧之心。”
刘义庆低着头,不一言。
“还拿晋孝武帝来说吧,”刘义隆进一步劝导他,“太元末年,东方长星现,太史令奏道:‘长星现,国将亡’,孝武心中恶之。到了夜晚,他在华林园与侍臣宴饮时,举杯对着长星说:‘长星长星,劝你一杯酒,自古以来何时有万岁天子!’晋孝武,不过只是一个庸主,但他对天象就有明见。在这一点上,我倒挺佩服他。”长星,类似彗星,有长形光芒,古人认为长星现是不祥之兆。
刘义庆抬起头,若有所动。刘义隆接着说:
“兄与后军,各受朝廷内外之任。《诗经》上说:‘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分封宗室是为了护卫皇家,这一层意思,兄是比我更清楚的。现在兄见不可知之天象,就以为……假如天必降灾,那么离京千里怎么就能避了灾难了呢?假如留任京都就一定有不测之事,离此外任就必保平安,那么我又何敢违抗上天呢!”后军,即刘义庆的亲兄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
送刘义庆出了太极殿后,刘义隆回到卧榻上,手指轻敲雕饰的扶手,他又想起了长沙王义欣来。
第四十六章 皇上吊唁要臣王昙首
永初三年五月先帝驾崩,六月长沙王道怜薨逝,义欣以长子身份袭封长沙王爵位。刘义隆即位后,义欣由征虏将军、青州刺史进号后将军,加散骑常侍,元嘉三年兼任南兖州刺史;七年到彦之率众北伐,刘义隆因他在宗室兄弟排行中年龄最大职位最高又最有威望,就让他总统群帅进驻彭城作为众军声援,那也是“宗子维城”之意。到彦之败退,北方侵扰,义欣的将佐们担心魏虏大军来犯,劝他弃彭城回京,义欣坚守不动,这深得刘义隆的赞许。为表彰他,刘义隆特地提升他:使持节、监豫州等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担任后将军如故,镇守寿阳。而让他出镇寿阳,既是考虑到寿阳是南北对峙中的军事重镇,又考虑到近年来豫州荒毁、百姓贫困、寿阳城郭颓败,刘义隆希望这位兄长受命于艰难之中,能凭个人才力治好这个州,从而使寿阳成为国家抗击北虏的一道重要屏障。
就在刘义庆的去留还没有完全定夺的时候,侍中、太子詹事王昙病亡。
要臣去世,皇帝往往要亲临吊唁。刘义隆乘法驾亲自赶赴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临吊。——皇帝出行常常会乘不同的车驾,仪仗侍卫的繁简各不同:小驾,多在祭祀宗庙或行凶礼时乘坐,乘四望车;法驾,皇帝出行时有侍从车三十六辆,分左中右三列行进,皇帝乘金根车,御六马;大驾,由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驾驭,后跟侍从车八十一辆,备千乘万骑,是仪仗侍从最繁盛的一种。
王昙的长兄、卫将军扬州刺史王弘以王家主人的身份恭敬地迎候在王氏府第的大门外。下了车,看见了王弘羸弱的身躯,刘义隆就悲不自胜。从东阶登上灵堂,刘义隆对着王昙的遗体忘情地哭着,泪水滂沱;王弘立即行哭拜礼,下跪叩头,接着又站起来哭诵。中书舍人依礼先扶王弘走出灵堂,王弘恭候在门外,等着皇上出来。
刘义隆出来后流着泪含混不清地对着王弘安慰一番,又叮嘱他多保重,然后乘法驾离开了王家。
离开乌衣巷,过了朱雀航,仍处在悲痛之中的刘义隆回想着王昙随自己从彭城到江陵、再由江陵到京都这么多年来忠心耿耿的一件件往事,又想起先帝特意安排他辅佐自己并告诫自己说他有宰相才,遇事应多咨访他;想到这里,坐在车驾里的刘义隆竟然又溢出了泪水。直待陪乘的侍中殷景仁及中书舍人周纠说了些宽慰皇上的话,刘义隆才止了悲痛。沉默了片刻,刘义隆对他们说:
“王侍中未尽其才,是朕的责任。”
周纠接着感慨说:
“王家将衰,贤者先殒!”
“何止是王家,”刘义隆茫然地说,“失去了他,正是皇家的衰败!”
刘义隆说出这样颇有些不祥的话,并非悲中妄言,他正道出了王昙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回宫的夜晚,刘义隆就留下殷景仁商讨王昙去世后的补缺事宜。近几年,尚书左仆射郑鲜之、中护军王华、左光禄大夫范泰与领军将军赵伦之等人相继去世,朝中要挑选出合适的人选来补王昙去后的空缺,这还真让刘义隆颇费踌躇。在相继否定了几个人选后,殷景仁建议征刘湛回京。
此时在江陵的江夏王义恭表面上虽接受了皇上的劝诫,但心中对刘湛抑制自己仍很不平。事既如此,而朝中得力的大臣又零落相继,那还不如征调刘湛回京,这样既可止息他与江夏王之间的矛盾,又可补上王昙去后所留下的非常之缺。
殷景仁的建议再次让刘义隆颇费踌躇:这样做,补缺事宜虽然解决了,但荆州这么大的地盘,留下一个年轻的江夏王又该怎么办呢?刘义隆举棋不定。
次日,殷景仁再次申说利害,同时也解除了皇上的后顾之忧:让江夏王任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改任临川王义庆为荆州刺史,以遂他求外任之愿。
刘义隆很赞赏殷景仁的建议,因为这一下子就为他解决了两个难题,也让他觉得殷景仁更不可缺少。
刘湛这才欣喜地踏上了回京的路程,接替王昙留下的职位担任太子詹事——太子詹事是太子东宫的要员,但此时太子年龄还小,并没有出居东宫,所以太子詹事这样一个三品要员主要还是协理皇上处理朝廷事务。刘义隆的意思,也是要刘湛积累一些经验,以便日后能更好地辅弼太子处理好国家大事。
刘湛入京后,除了担任太子詹事,皇上又加他为给事中——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应对,参与政事。他从此就和殷景仁一样成了皇上的股肱之臣。
也是从这时起,刘湛踌躇满志。
第四十七章 狂放的大诗人又惹事端
并不是所有的朝臣都会有得意的感觉。。
自从皇上赐假让谢灵运东归会稽养病以来——谢灵运原也没病,他就夜以继日地宴集宾朋游玩娱乐,借以排解心中的郁闷。他与宾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参与其中的就有他的“四友”:东海人何长瑜、颍川人荀雍、泰山人羊璇之和他的族弟谢惠连。他在东部种种出格的行为,又被御史中丞所奏,御史中丞认为他所作所为缺乏朝廷大臣的风范。刘义隆看着奏折,不得已,免了他的官职。免官后的谢灵运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觉得无官一身轻,就在会稽一带恣意游玩。
因为继承了父祖所留传下来的十分丰厚的家业,谢灵运家中的奴仆佣工有数千人,门生故旧也有数百,于是他就在会稽开山挖湖,劳役不止。虽然谢惠连等人后来回京做官去了,但隐士王弘之以及追随他的何长瑜等人仍是他极合宜的游玩唱和的伙伴。谢灵运在他们的伴随下,常常带着数十百人爬山涉岭,把东部方圆数百里的奇山异水都一一游遍;他们所行走的路途又必定选择奇径险道,不论山回路转,层嶂千重,不能到达不肯罢休。
为了爬山,谢灵运还挥了他的聪明才智,继十年前在永嘉太守任上明了曲柄笠之后,他又明了一种便于爬山的木屐:在它的前后安装上齿儿,上山时取下它的前齿,下山时则取下它的后齿。这种被时人称作谢公屐的木屐,让人在上山下山时倍感轻松便捷。
游罢始宁(今浙江上虞),谢灵运又率领他的门生故旧十多人从始宁南山出直趋临海(辖今浙江临海、天台、丽水等县),使他的家中童仆数百人随后,遇到山路难行他就让数百童仆伐木开道。
他在山中如此兴师动众,不久就惊动了当地官府。临海太守王秀听属下禀报说山中有千百人砍山开道不知何为,极为惊恐,他那根敏感的神经让他马上想起二十多年前也是从东部起事的造反头目孙恩和卢循;他以为山贼临郡,急忙兵自卫。后来待细细打听,知道是贵人谢灵运,他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待王秀见了谢灵运,谢灵运只稍作问候,并不行礼,并邀请他一道游玩——谢灵运虽是被免了官的朝廷大臣,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毕竟不是普通的吏民,所以也就不太把被吏民视作“府君”“邦君”的太守大人当作回事。那王秀也不太计较,天下何人不识谢康乐啊?但他既无游玩的雅兴,也无谢灵运这样的胆子,只能谢绝。
临别,谢灵运作诗赠王秀,其中写道:“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邦君”指王秀,谢灵运以“旅客”自称。诗中的一“难”一“易”,尽写出他以游玩山水为乐不关俗务的得意之情。
从临海到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谢灵运的山泽之游方兴未艾,但这时的会稽太守再不是他当年从永嘉回始宁时的那位太守了,那时的太守是他的本家叔父谢方明——谢惠连的父亲。如今的太守甚至也不是临海那位不和他计较的太守王秀了。现任会稽太守是一位精诚信佛的人,他的名字叫孟顗。
谢灵运也不管如今的府君是哪一位,依然遨游如故。在他看来,虽说自己只是一个白衣诗人,但毕竟曾是一位皇帝身边的三品大员,“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使不论这一点,单凭他陈郡谢氏百年来的丰功伟绩、名士风流,单凭他驰名天下的“谢康乐”几个字,他是无论如何——即使强打起精神来——也无法把孟某这样一个官阶五品的“俗吏”放在眼里的。已经知晓了孟顗虔诚信佛,这也不能改变了谢灵运对他的看法。
当年谢玄因子孙难得——儿子谢瑍生来就是个弱智,孙子谢灵运年幼时却聪明异常,谢玄当然不清楚还有隔代遗传一说,就曾感慨说:“我这样的人竟然只生了个这样的儿子,而这样的儿子竟然会生了个少见的天才!”因此就对他寄予厚望,于是送他到钱塘人杜明师处寄养,并为他取名叫“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