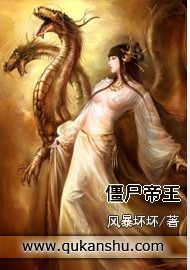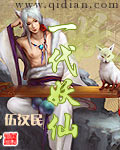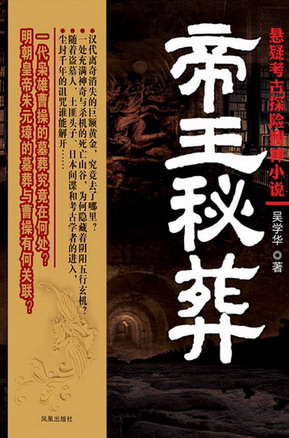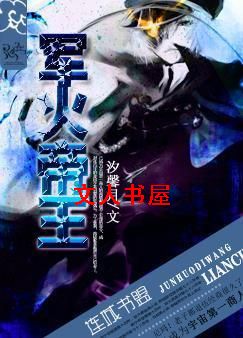一代帝王刘义隆-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则失臣,臣不密则****’。下属或相互诋毁,你切勿轻信,每遇此事,当细细察之。
“名器应深加护惜,不可轻易假人。你对左右,或授官,或赏赐,尤应斟酌;我对左右虽然少恩,但如闻外议,不以为非。
“以贵凌人人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等事易明了。
“声乐嬉游,不可过度;赌博酗酒,千万勿为。供用养身,都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应服用。你之嫔妃左右,已有数人,既始至江陵,不可匆匆再有所纳娶。
“又,你应多多引见僚佐。主臣自应相见,相见不多则彼此不亲,彼此不亲则无因得尽人力,人力
不尽,则无以尽知众事。广泛引接下属,既有益你之见闻,对言事者,也增其声望。”
信中提及的袁太妃,是江夏王的生母。
这是刘义隆即位以来第一次写这样一封长信。过去写过,那是在远离先帝镇守江陵时写的,信的内容是详尽地向先帝禀报在江陵的方方面面以及自己的一些想法。现在不同了,他是帝,他更像一个长辈。他实在是因为弟弟的出镇让他放心不下,所以他才在信中反复叮咛,告诫再三,大事小事,林林总总,写了一纸又一纸。拟了草稿后,他又重新用仿王羲之的隶体认认真真地抄了一遍,直到夜半鸡鸣。
平心而论,刘义隆在信中对弟弟的告诫,小至声乐嬉戏、接人待物,大至审案授官、处理政务,甚至有对自己若遇到不测的后事安排,可谓周全备至。由此也可以看出,元嘉年间社会生产得以展,国家实力得以提高,人民生活富足安定——史臣赞美其为“元嘉之治”,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次日,刘义隆的大驾亲自出城为江夏王义恭送行。
到秦淮河边,在祭拜路神的祖道仪式之后,刘义隆又特意把刘湛邀至玉辇中反复叮嘱,刘湛也一一点头应承。这时,刘湛已被拜为南蛮校尉,兼抚军长史,行府州事——晋宋之际,每当幼王临藩,军府和州里的事务都由辅佐他的大臣全权处理;刘义隆担心的,正是义恭已经十七岁了——他已经不是幼王了,他可能会自己作主,这样就很难处理好主相的关系。
第三十一章 谢灵运劝帝北伐
谢灵运是早已不再安坐在秘阁中翻翻故纸堆动动笔墨撰写《晋书》了,尽管要他写的《晋书》已经粗立了条目;在伴君拜陵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侍中了。。侍中是一个要臣,但他这个侍中却不是要臣,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陪侍。皇帝只是喜欢他的“二宝”而已,自己会成为一个弄臣吗?他再次郁闷着。
在京口,他看到了刘家挂在土墙上的农具,他想起了自己祖上的丰功伟绩;他知道皇上仅仅停留在欣赏赞叹他的“二宝”这一层面上,所以只和他谈论诗文不和他谈论国事。皇上见了他的应诏诗——那里也有他的郁闷,但皇上却装做视而不见对他置之不理。这都让他的心中久久不能平。
从京口回京以后,谢灵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不仅不再去撰写《晋书》,而且轮到他入宫值日,他也不去,甚至连朝会也不参加了。有时候,他驱使着数百个童仆在自家占地数十亩的花园里,挖池塘筑篱笆,栽竹子植堇花,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候,他又和族侄谢惠连等人一道,带着童仆出城游玩,远至二百多里,十多天不回京。
他听说江北也有山水佳处,钟离郡(在今安徽凤阳一带)有一山洞,深不可测,奇妙无比,于是他就和谢惠连等人带着行装出了。
他们先是雇了一条能容纳数十人的大船,渡过长江,然后一路北上,直奔钟离。到了钟离,但他们并没有找到那个传说中的山洞。正在大家沮丧的时候,谢灵运却意气风地说:
“当年王徽之居山阴(在今浙江绍兴)时,见雪中景,突然想起隐士戴逵,当即命驾。经过一宿的奔波,天亮时到了戴逵的门前,他却吩咐随从掉转车头返回山阴。随从不解,他说:‘我本乘兴而来,如今兴尽而归,有何不可?’如今也是一样。何况我等兴味未减!不在于是否找到了山洞看到了山洞,而在于离开了局促的建康,离开了憋人的宫廷!这还不足以令人感到惬意吗?”
众人见他有这样的兴致,也都舒心地笑了。
将离开钟离的时候,谢灵运又想继续北上,他想去看看久闻其名的圣地泰山,尽管那里边临魏人。但刚走了一天,因为微染小恙,他才不得不南归。
在外出游玩期间,谢灵运既不上表禀告,又不按例请假,全然是一个逍遥自在的诗人了。这时候,负责纠察朝廷官员的御史中丞开始履行其职责了:
一份弹劾谢灵运身为朝廷大臣竟然目无纲纪的奏章放在了刘义隆的御案上。
刘义隆不想伤害大臣,尤其是诗人谢灵运,于是他叫来中书舍人秋当,吩咐他去找谢灵运。
在谢灵运回京的次日,中书舍人秋当就去登门拜访了。他婉转地转告了皇上的意旨,希望诗人能主动提出辞呈,这样面子上也好看些。于是谢灵运上表,陈说自己疾病缠身,请求辞去所任职务。虽然这只是托词,但这也是君臣都可以接受的。
在接到谢灵运的上表后,刘义隆想想即位数年来对待谢灵运的前前后后,又深深地理解了他的所作所为。他并未免去谢灵运的官职,而是赐假二百日让他东归会稽郡始宁(故治在今浙江上虞附近)以了却其游乐的心愿。
始宁,有谢灵运的父祖置办的大批田产及豪宅,他的父祖也都安葬在那里。自晋氏江左以来,那些南渡的中原望族为了避免和当地富家大族在产业上生矛盾,就远远地离开京都,到江浙一带购置产业,也因此,江浙一带往往有朝廷官员大片的田产和别业(即别墅)。此时,朝廷还依照晋时官员休假制度:朝臣每月休假五日,一年之中有六十日假期,若遇家中有急事,可以合并请假六十日,后来又增至百日;若家住千里之外且道路难行,也可合并请两年假,合计二百日。刘义隆赐假二百日,当然是对谢灵运开的特例:在他看来,既不免谢的职,且赐其长假,这多多少少也算减了自己心中的一些缺憾。
临行,谢灵运求见皇上。并未像其他朝臣那样在求见的表疏呈上后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刘义隆很快就在太极殿接见了他。
问过谢灵运远游了些什么地方见了些什么奇景之后,刘义隆就问他为何求见。谢灵运听了,接过话头:
“在京口北固山,陛下远眺江北,沉默良久,给臣留下了深刻印象。”
“远眺?”刘义隆重复了一遍。
“从北固山北望,除了能见江北的一些朦胧之物,并无可让陛下长久凝神而望者,有的只是……”
“是什么?”
“陛下所眺望的,是那看不见的地方。”
刘义隆的心中咯噔一声。在这一点上,倒是谢灵运能了解自己。是谢常陪侍在左右故能明了己心,还是因为谢的悟性高,不只是有诗才而已?
“卿以为是何地呢?”
“是司州,是黄河以南的大片失地。这是陛下所魂牵梦饶的!”司州原治所在洛阳,后来被北魏占领。
刘义隆无言地看着他。
“五胡乱华,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中原地区,一直沦没在魏虏的铁骑下。先皇聪明神武,哀济群生,灭了姚泓以后,准备踏平北方,统一天下,使久困之民归于正化,但最终事与愿违,天下之人,只能仰德抱悲。少帝景平初年,先帝陵土未干,魏虏乘丧南犯,侵占我黄河以南大片土地,有识之士,谁不扼腕!但是景平时当政者徐、傅等人,所任并非其才,大敌当前,却只顾纷扰京都,无暇顾及先皇托付,终致孤城沦陷,徐、傅等却不肯救助,致使忠烈之士,囚于荒漠,长河三千,反落寇手!河南之地,一战沦亡,此国耻宜雪,朝野同心!而河南自落入敌手,百姓备受蹂躏,征调赋税,没有终了;若征求不得,魏虏则滥杀百姓,河南之民,家破人亡。这也是仁者所切齿痛心的!”
谢灵运说得很激动,刘义隆专注地听着,在谢稍停时,就问谢:
“对此,卿有何高见呢?”
“愚臣以为,今贼魏拓跋焘又出兵西征夏。频繁征战,使魏虏师老于外,国内空虚,此时北伐,机不可失。若失此北伐良机,大宋将与魏相持下去;而魏虏屡经征战,势力范围将扩大,力量将得以增强。等到那时,大宋即使兵多食众,再想取魏,则非易事。”
刘义隆点头赞许。谢灵运又接着说:
“历观前朝,强国都以兼并弱小者为根本,古今圣贤,无不如此。古人有这样的话:‘既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过去曹魏虽强,但平定荆、冀二州,都是乘袁绍、刘表弱小;晋氏虽盛,但开拓吴、蜀之地,也乘葛、6衰落。这都是前世成事,今见于史册的。当年先帝平定姚泓之时,长驱滑台,席卷下城,魏虏失气丧魄,指日就尽,天下之人都以为魏虏当随姚氏而灭。可惜王镇恶、沈田子、王修诸将相互残杀,加以长安违律,潼关失守,这样使魏虏得以延缓岁月,时至今日,十多年了。如今魏虏攻夏,大宋两取其困,其势必如卞庄刺虎,一举两得!中原百姓期盼皇恩,如饥似渴,翘南望,时日已久。至于今日国家府藏,的确并不丰足,但是凡举大事,不必坐等国富兵强,贵在天时。现在兵器充满,兵力粗足,粮食无忧,和先帝时相比,条件更好。群臣中有人认为北伐之举得不偿失,这是不能成立的:中原人口,百万有余,田赋之沃,著自《贡》典,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强富之实,昭然可知。得中原,国力将大增。为国家长久计,怎能计较一战之费呢!”
“先帝远征姚泓,收复长安,但随即长安不能守;朕若兴兵伐河北,河北可守吗?”
时人所说的河南河北,都是以中原地区的黄河为界:黄河南即河南,黄河北即河北。
“鉴于长安之败,陛下自然会担心河北难守。但依臣看来,长安与河北形势不同:关西百姓杂居,种族不一,加之远戍之军,处于新旧交替之际;而河北则不同:河北之民都是汉家旧户,几乎无杂人,况且那里地理形势连山阻隔,又有三关之险,守军若游骑长驱,则沙漠风靡;若驻军守塞,则安如山固!”
“卿以为,伐河北有必胜的把握吗?”
“晋武帝,不过一中等之主罢了,但恰逢吴后主孙皓暴虐荒乱,天授其福,加之谋臣献策,武将扬威,故能建功当年,天下一统。而今陛下聪明圣哲,天下归仁,文德与武功并振,霜威与素风俱举,加之宰辅贤明,诸王出众,州郡齐心,虎臣满朝,而天威远命,何敌不灭!魏虏拓跋氏,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臣见识肤浅,愿陛下早定大计。臣行将东归,但心中盼太平之道,期泰山之封。臣早已想和陛下陈说愚见,但担心所言荒谬,有污圣听;今蒙陛下赐假,臣将暂离京都,而抱此愚志,如骨鲠在喉,今日得以一吐为快,再无缺憾!”
谢灵运所言,有些是他人所曾说过的,有些是刘义隆所反复琢磨的,而有些新观点却给了刘义隆以很大启示,这也让刘义隆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正因为如此,刘义隆犯难了:去说服众人,让谢留下来?若留下来,又让他做什么?
等等再说吧。刘义隆沉思良久。
随后,刘义隆亲自把他送出太极殿。
走出宫殿的谢灵运,见皇上并没有因为自己今天的一席话而流露出什么挽留的意思,心中一片怅然。
第三十二章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谢灵运的《晋书》虽然没有写成,但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却在他费时三年之后终于完成。元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裴松之携带着《三国志注》及前一天写就的《上三国志注表》,晋见太极殿。
刘义隆在延请年近六旬的老臣入座后,就先看他的《上三国志注表》。
表疏上说,陈寿的《三国志》是不可多得的嘉史,但是不足在于疏略,记事时有脱漏。臣奉旨作注,上搜旧闻,旁采遗事:凡是陈寿所不载,事件却应该存录的,就无不尽取以补其缺;若同说一事却前后矛盾,如今又不能判断的,就一并抄录以备异闻;至于纰缪显然,言不合理的,就随后加以矫正;记事当否及陈寿之小失,臣都按愚意加以论辩。
刘义隆看罢上表,就随手拿起一卷。陈寿的《三国志》,刘义隆是熟记于心的,他要看看裴松之是如何随后加以矫正并加以论辩的。他翻看到《吴书》中记孙权之子孙奋被后主孙皓诛杀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