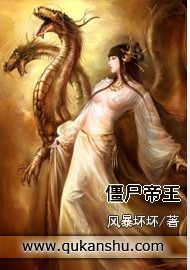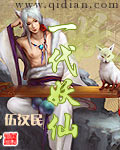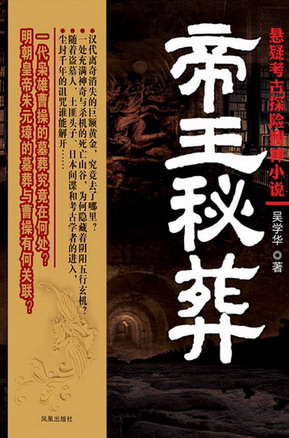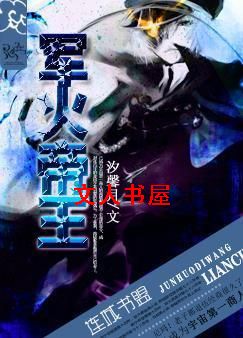һ����������¡-��1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ƽ�������ˣ�ͨ�λ����������������������ʶ������
��������������ɰ���ز���ؼ泣��һ�������𣬰��ÿ����
����������������������̾�����£�
������������ʫ���⡰�걯����֮�����µۺ�ʫ��˫˫���������������ˡ�
��������ʫ�˴����ι�����;���°��������ӡ���ָ®�������棩�����Ƶ�®�����������Ĺ�¡��������֮�������У�д����ʫ���Ե��������Լ�������ĵ��¡�����ʫ�����У���������Զ��®�������ǵ��£��ǡ����ӡ�����������ʲô�����ˡ���������������֮���������������Ҳֻ�ܡ�����ͽ���ˡ����ڰ�̾����֮�࣬����ȻҲ�����������¶��Լ�����ʶ����������ֹһ�ζ��Լ�˵���ս�ί�����Ρ�������������δ����������ȥ�������ܲ����ˡ����ࡱ�����ᡱ�أ�
��������д������ʫ����һֱ���������¶�����죬���������ĵ�һ�����ߡ�
���������˴ν�������ֻ��һ�鲼��ʫ�ˣ������ص���������µġ������ž��ӡ���������ʱ���Ѿ���ȥ�������Ͻ�������گ���һ�������ŵ�Ӫ������ĸ�ŷ��˼�������®������ĸ������л�����ؾ�������������Ұ�ͷŵ�һ���ź������ڸ��ǡ��˿���֮ʱ�����л�Ҫ˵����ʫ��ֻ����Ҫ˵��һ�����ӡ�
����������Ȼ����ֻ��һ�����ӣ����������Ѿ��ڱ��µ����������˾���������⣬Ҳ����ʫ����û���뵽�ġ�
�����������������������念��ϲ�����ӡ�
�������������Ǿ��ݴ�ʷл�ij�Ů�������ȵ�����ʱ����ȷ���ġ�Ϊ�˳�Ů�Ļ��£�Զ�ڽ����л���ص��÷��˲��Ϻͳ���л���ݻؾ������˻��£����еģ�����л�Ķ�Ů�������������������ϵ��õܡ���Ұ�����������Ҳ���ȵ���ǰ�İ��š�
���������ʼҺ�����л������������ν����赺ϣ�ʱ�˶���ô��Ϊ��
���������ĵܵĻ�����Ϊ�ֳ�������¡����ȻҪ�μӵġ��ȵ�������ϣ����ݴ��������ĸ��ڻ�����ʱ������¡ȴһ�Բ�������Ҳ������һ��ϲ�����ɫ��
���������������µ۵Ļ��������ˡ�
�����������˻��������¡����齱��������漴˳�������ڱ����ϡ����տ����Ļ��ӣ��ʺ�Ԭ���û��ȥ�μӻ������ܸо������ϵ��������������������йػ�����¡�
�����������»�ӳ������Ӱٳˡ����ڿ����������ˡ�������¡�������˵��
���������������������𣿡�Ԭ��������ǰ���Լ������ϻ����������ǻʼҵ��ų�����
�������������ӵúܡ�������¡���Ŵ���ľ�̵��λ������������ţ������������ȵ��ն�����������������һŮ��������
���������������һ�䣬��������С���������Ԭ��ͣ����ͷ�Ļ�ƣ��ʣ�
��������������˵ʲô����
������������¡һͦ������������Իʺ�˵ʲô���һ㶣��ֻ����ص���ȥ���ʺ������еĶ�����Ҳ�������ϵ����ߡ�
��������������������һŮ������ԭ��ǰ���ֹ�˵�Ļ�����������֮��ʱ���ɶ���˾��ӱ�ͳ�ɳ��˾��V�ֵܸ�ӵ����ͼ���������ֹ��Ů���ɶ�������ɳ���������Ҳ�˵���ɼ��ֹ㣬���������������ֹ�������������������������ӻ�һ��Ů���أ�������˵���䲻���Ѽ�Ů���ɶ��������Լ���������ͬ�ģ��һ�����������أ�����ô��ɵ��Ϊ��һ��Ů��ȴ�õ�����ɱ���ҵ�������Ӱ���
���������ڽ���������ʱ����Ϊ��Ҫ˵�������Ļ��أ�
���������ʺ���˫�ַ�����ϸߴ��������Ȼ��ָ��ָҡ���еĻ��ӣ�
�������������½�����ô���˶����ˣ���
������������ÿ�����������Ҫ����Ūһ����ӵġ���������ֻ�dz�ҡ����˿������ڻʺ���ô�ʣ���������ɵ�˵��
��������������������������DZ�һ���ֵܣ���ô���Ͳ����ж����ˣ�Ҳ�����С�����
���������ʺ����������������ģ�ֹ������˵��ȥ��������γ��˲���֮�ԣ������Ѿ���ȥ������һ�ж����ڰ��������մ�������������ô������Щ�쳣���У�����ʲô��������Ҫ��ʲô���𣿻ʺ���һͷ��ˮ��
��������С������ҡ���п�������С������˱��ӣ����������������߽�����
�������������ϻ���û�ж�ŪС���ӵ���˼��ֻ�ǿ��˿���Ȼ��������������ȥ��
��ʮ���¡�����ֻ�����۷���
���������뿪�˻ʺ�Ļ�����µ۾ͷԸ�������ȥ�����������Ͼ����������ʱ������ͨ���ߵ��촬����һ����
������������������˵������⣬�µ�����¡���صذ����ں�����Ӹ����ڵ��������Ҳ�ٵ������������ݵĽ�����С�
��������һ·�ϣ�������̸�����ʸ����ȵ۱���ʱл����������������������ġ����������
���������������Ȼ�������֮�ܣ���֪���������������һƳ���£������桱һ�����Լ���Ը�ڱ�����ǰ�ἰ�ģ����ȵ۽��پٱ�����ʱ����л����ʿ��ƣ���������Ϊ��Ȱ�ɣ���δ�����ɡ������֣��֮���ϱ�����
�����������¼���������˵�����ʣ�
����������֣���������ʲô�أ���
����������֣���Ϊ���������������ȵ��������֣�һ����ȫ���������ء�����������¼������أ�����һʱ���Թ��£������������ı������;�һ������ʱ�ã����ʹ�����Ϊ�������ɡ����Һ���������һʱ���⣬���Բ��ҳ��ƹ��£���������أ�һ������Ϊ����η�����������ҷ�����Dz���Ȼ���ٻ�ʦ��������ô��������֮�ģ���������������Ҵ��Զ���������ࣺ��������˾����֮����������ͤ������ұͤ����������ͨ����ɽ��ɽ�´�����Ⱥ��͵Ϯ���DZ������룻ȥ�걱����������Ϊ��������ơ�ǰ��֮������֮�����ֽ����ݴ�ˮ����ʳȱ�������⣨ָ������ˡ������һ˵ָ������ˡ�������Ⱥ�����ݿ��أ��������������������IJ������������ȵۣ���������ٳ���������dz֮ı������֮�ڣ��Ʊ�Σ���������������ı��ٳɺӡ���֮������Ӧ�뱱²��ã���²������ϰ������ϰ���á����������ң���������ƽ�ǣ�����������ū��κ����ܳ�ڣ�����ɥʦ��ͷ�������ǵ�����֮����һ�����𡣡�
������������������ƽ�ǡ����£��ֱ���ָ�����ū��Χ��ƽ�ǣ�������ƽ�����˼Ʋŵ�������������������ū������������Ҫ����������������裻�ܲٳ��֮ս����ܶ��飻���±���������ͷ����۽������ˡ�
��������������һ����������¡�������ƺ�����֣��֮�����ȵۣ������Ǹ��������Լ���
�����������˱������ϵ��촬��������¡���߱߿���Ȼ������һ�Ҽ����깤��ս������վ�ڼװ��Ϻ����Ĺ�Ա��̸���������ʼ���������һ��ս������Ҫ�IJ��Ϻ�ʱ�䣬�Լ����������ܽ�����������ȵȡ�
���������������¡�ֺ��̴�һ�������һ���Ѿ�������˵�ս����������ĺ�������߮��Ѳ����һ���������������į�ĺ��棬����¡ͻȻ����һ��β��Ѽ�į�ĺ�����һ��ˮ���IJ���������������������ͷ�����Ķ��߷·��Ѿ�������ˮ���Dz���ʱ����˷����ź���ɱ����
���������µ۽��������ټ��ij��佫��ͬʱ��گ����ʡ������Dzɢ�������ﵱȥ��Զ�ڽ���ľ��ݴ�ʷл��Զ��������Ӻ�ݴ�ʷ������ѯ������������Ӳ��˱������촬�������ƺ�������Ұ��һ����Ҫ��Ϣ��
��������Ҫ���˶�ã��µ۽���ٱ�����
���������µ�Ҫ��ٱ��������ո�����ǰʧȥ�ĺ�������ҰΪ�����۷ס�
����������������֪���н���Dzʹ�߸�������ѯ��������Ϣ�����ݴ�ʷл��д��һ���š������У�������л�ޡ������ӡ��壬����δ������Ұ֮�ǣ��Ǿ��߶ࡱ����˵����������������豱�����۽�Dzɢ�������ﵱǰ���ɷá���
��������Ҫ���˼��գ�ʹ�ߵ��ˣ�л����֪�����𣿸����αض��һ�٣�
��������ԭ����������������ʢ��л���ڴ�گʱ���Բ������������ա����Ͼ����µ��Ѿ�ʮ�����ˣ����������������£����Իᰲ�ţ����Զ�л�����أ����������ʼң����Ե۲�����ǧ���ɷá�
�������������б�ҪΪл�Ĵ�گ������
���������ǵģ����б�Ҫ��ô���ģ�Ҳ�б�Ҫ�ɳ�һ����ʹ���������ʱ���Ƿdz�ʱ�ڣ��Ƿdz�ʱ�ڣ��Ͳ�Ҫ��ʲô���ӡ��Ͼ���������һ��������˩�ŵ����ơ�
��������л��Ϊ�ˣ�������ʢ�����ξ��ݣ�����մմ��ϲ�����У���ȥ���常��»���л壴��У��常�������꣬���𣺡���ʮ�壡���常�������β�ס������֮ɫ��Ц��˵���������ɶ�ʮ�����α���������������ȣ��Ѿ����ˣ���л�����ˣ�������ɫ�������ɼ�ǰ�������ۣ����ڶ�ʮ����ʱ����Ϊ�����ɽ������ݴ�ʷ��
��������������µ���ס��̫���л���ĵ۸��������ξ��ݣ����в��������ֵ������ھ�����������������µ۲�û���������������д�Ȩ���������졢�����С��ȵ����쾫���ɽ�����ͤ���������봬�е�л����ʯͷ�ǣ�����ض�����˵���������յ������ˣ�����˵���������վ���˵��������ɽͷ��͢ξ������͢ξ��ɽͷ��������ͬ�У���͢ξ��ָ��������ɽͷ�Ͽ���͢ξ������û��ʲô���ǵģ�Ҫ�Ƿ�����������͢ξ��������ң��ɽͷ���ǿ��Ǽ�����£�
�����������˽��꣬��ʱ���µ�ί���������ؽ��꣬л���Ľ����ܻ����ͺ����������Ϊ�����ؾ��ͱ�ʱ��л����������˵������Ů������ʼҡ�������Ů������֮�����ã����������ˣ���֪������������Ҳ�ǽ������壬����������ƽӹ���ӣ������Ժյ�л�����а�Ů����Ů�����ֻῴ�����أ�
��������ֱ��Ԫ�����꣨��Ԫ426�꣩���£�������˵���µ۵�ʹ���ﵱһֱû�е�����л��ȴ�������ڹ����λ������ɵĵܵ�л�ݵ���ʹ����ʹ����������һ�����˾��ֵ���Ϣ����͢���հ����쳣���ƺ���ͬ�ڱ�����
���������������������м٣������ĵܵ��־�����Ϊ���֮�ˣ�������һ������ģ��ֻ��Ǽٵģ���һ�أ��ֵ�Զ�ڽ����л��ң��֪��ǧ��֮��ij��е�ʵ���ˡ�
���������ڽ�������£��ٸ������ã��ڣ��ǻ�������л���ڵ������������������Ѯ������ξ��γ��졣
���������γ����������л�ͰѸ�����˽�ŵݸ�������
�����������ξ�������ι�д���ţ���л����������Ϳ�ʼ�ʣ��ֲ������ش�ͽ���˵�����Ǹ����ø������ˣ����ǵ����Һö��£���
���������γ��쿴�ϣ���Ĭ���ã�Ȼ��������˵��
����������������Ϊ����ʹ�ﵱ�������𣿡���ʹ����͢ʹ�ߡ�
�����������ﵱ�����������Ǹ�����£����ճ̿����ﵱӦ�õ��ˣ�����·���������鷳��������Ҳδ��֪����
�������������dz��ԡ�˲Ϣ��䡯������֮�£��븵��Dzʹ����ʱ�����Ѳ�ͬ����
�������������кβ�ͬ�أ���
����������������ţ���˵̨����ν�������������������ơ���ʹ�ﵱ��������֮������
��������Ҳ���Dz�Ը������˵�Ǻ���֤ʵ�Ǹ����µIJ²⣬ֱ����ʱ��л���ó��ܵ������������ܼ����γ��쿴���ܼ����ֿ���л�ޣ�һ�Բ���
�����������졢����Ȼ�ƹܳ���������δ�����һ�㼣�ܵ���ν�������쳣�������Ǻ��⣿������۷ף��������·;ңԶ������;˵�Զﴫ���л���������ţ�����������������������Ҳ����Щ���ҿ�ο�ijɷ֡�
�����������ˣ�л�����кγ���Ԥ�Ȳ���ô�گ����ֻ˵���������㣬����Ӧ�õȴ����ꡣ
������������գ�л����Ȼû�е�����ʹ�ﵱ��������ȴ�����ѳ�����Ϊ������ʷ�����������̵��ݵ���ʹ���б��ξ��փף�
������������͢�����֣������Ѷ�����
����������ĵ����齫��Ϊ��ʵ��
���������졢�����˾�����Ϊ��̴�����������л�����������
��ʮ���¡�����¡���ֹ�����
��������Ԫ����������ʮ���գ����������������ݴ�ʷ̴����Ӧگ�뾩��
�����������գ���گ��˾ͽ����֮����������빬��
�����������������Ϊ��Ҫ���ֱ���֮�£��ͼݳ������г�ȥ����·�ϣ���������ֵ���ڵĻ�������л�����ĸ����۶��������˵��˸�����ǰ�����ͱ���
���������������ˣ���
���������������ˣ��������ţ������ߵ���گ��ǰ����ɩ�Ӳ���Ϊ�ɣ��봫گʹ�Ժ�Ȼ��ת���ظ������˴Ӻ��ż�������֮���Լ��˳��Ƶ�������ţ����˳��žͻ��Ͽ����������ָ���Ĺ�ض�ȥ��
��������������ɩ��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