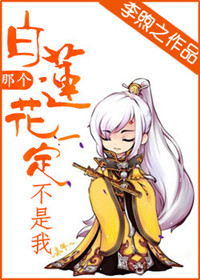颜如莲花开落-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却听门外一声极熟悉的轻咳,忙抬眼去看,只见祖荫背着淡薄的日影站在玻璃窗外,眉目不甚清楚,脸色略有些憔悴。门外细雨初过,草木枝叶如笼湿烟,只映得他眉目清秀如竹,含笑与她隔窗相望。清流无声一笑,蹬蹬地出门走了。他亦微笑着掀帘而入,却并不言语,只深深地看着她。
她被瞧得心里发虚,侧过脸去眼睛往下一溜,忽然看到桌上还摆着刚写过字的纸,伸手欲收起,却鬼使神差般从砚盒边拿起笔来,直直往纸上落下。忽然醒悟过来,红着脸笑道:“我的天!”话未说毕,只觉得腕上一紧,祖荫从背后伸手来握着她的右手,替她将手腕稳住,一笔一画地写下去。白绵纸质地细密,笔尖从纸上划过,是如春蚕食桑叶的沙沙声。她随他手腕轻转,轻声问道:“这写的是什么?我都不熟悉……”他并不答话,只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一行一行地写满整张纸,才悄然放下笔,含着笑意道:“没关系,这些字你现在不认得,以后慢慢就认得了。清流的字太潦草,开始不能跟她学,明儿我去找卫夫人的帖子给你照着临。”他的眼里尽是静静的喜悦,笑了一声道:“樱儿,真是对不起你,一下子走了这么久。不过忙了大半月,终于把纱厂买下来了。巧得很,纱厂生产的布就叫雪鹰牌棉布,可见与你有缘。”她的脸如煮熟的虾子,一点一点地红了,微笑道:“你明儿把它改了吧,听着……怪别扭的。”他却极正经的模样,伸手将她箍到怀里摇头道:“这可算是名牌,以前获过针织大奖的,怎么能随便改?”她羞得拿手蒙上脸去,顿足道:“那怎么办?传出去会被别人笑死的。”他强将她的两只手拿开,很慢很慢地微笑了,轻声说:“到了纱厂里,大家一提‘雪鹰’,我就觉得像在唤你,越听越觉得牵肠挂肚,赶紧把事情谈妥了就往回赶。你还不该念着它的好?”他的声音那样沉静,是让人什么都不愿再想的安稳,“樱儿,咱们回放生桥。”放生桥处的房子空置半月,无人照管。院门一开,树上栖的几只雀儿乍然惊起,拍着翅膀唧唧地飞到半空里去了。半月前初来,一树玉兰半开半合,清露滋润。倏忽花期匆匆过了,花瓣落了一地,萎黄不堪,有几瓣恰恰落在金鱼池中,半浮半沉间被沤得烂黑。空气中甜郁郁的腐败之气,比发酵的酒还要浓烈。进宝见他眉头微蹙,忙笑道:“我去大掌柜家瞧瞧,若有合适的丫环,马上就带过来。这院子空了这么久,一个人哪里打扫得过来?”说罢不待他答应,一溜烟竟走了。祖荫一句话刚要出口,见进宝早已无影无踪,摇头苦笑道:“这猴子就知道偷懒。”携手扶着她小心翼翼地走过花径,与她一起到堂屋坐下,才皱眉道,“我听树之说,你这半月像是着了魔,心心念念地就想着画画写字,恨不得连睡觉都省了,晚上要丫头催好几遍才肯躺下休息,可都是真的?”他脸上佯装怒意,眼中却满是怜惜之色。雪樱啊了一声,扑哧便笑了,见他面沉如水,忙拿眼四下里乱看,见门上贴着一张红纸,上头木刻墨印着几个字,急忙指着那纸道:“你瞧,那张红纸上写的四个字,是不是风雨国民?”他本来绷着脸,到底忍不住,微笑着摇头道:“明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字,被你一念,就少一半去了。”脸上浮起一抹赞许之色,“不过,才半个多月,你就能熟悉四个字,真是聪明。”她将脸一扬,轻声笑道:“我刚才着急没看清楚,最后一个是平安的安。若再加上它,就一共认得五个字了。对了,清流姐还在画室里专门给我立了个画架,她说画画如练功,一日也不可懈怠,以后我要天天去张家练习。”祖荫不禁气结,拧着眉头半晌道:“真是岂有此理。”却忍不住微笑,“看来我也得努力些,不然连自家媳妇也看不住。明儿请树之过来瞧瞧,咱们哪间房子适合作画室,就依着他家的规格,建个一模一样的。”她大喜过望,脸上笑意盈盈,几乎说不出话。祖荫亦是心满足足,抬手缓缓抚摩她乌黑的发髻,忽然低声问道:“樱儿,上次走得匆忙,也没听你把话说完。那天……你娘到底说了什么?”她像是被毒蛇一口咬中,笑脸瞬间凝固在脸上,下意识地往后缩去。
八仙椅既深又阔,她整个身子都几乎蜷进椅中,一双眼睛如鸽子般温驯纯洁,含着一丝凄楚,摇头不语。祖荫伸手按在她的肩膀上,只觉得她浑身瑟瑟发抖,心下极是不忍,咽了口气慢慢道:“樱儿,那日你说,你只有我一个人了。既然如此,这世上还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他的眼中一片情深似海,让人不自禁沉沦。这世上还有什么秘密不能跟他说?她心中一酸,泪水几乎涌到眼中,刚张口说“我娘——”,那誓言却一字一句如焦雷般在耳边炸响——“你若日后对旁人提到自己的身世,天打五雷轰,青天白日遭逢邪祟,都要落在陈祖荫身上”。她打个冷战,将嘴抿得紧紧地,默默瞧着门上贴的红纸。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最后一个字是平安的安,万事安好,消灾得吉。她终于扭过头去避开他的目光,轻轻地说:“我娘说既然我情愿没名没分地跟着你……日后有什么苦楚,统统得自己担着。”他胸口一闷,千种复杂感情纠结一处,想解释却无从说起,终究默然踱到门边瞧着院里一地残花,低声叹道:“我何尝不知道……你不明白……”玉兰花瓣如污秽的纸巾铺在地上,一阵阵腐败之气潮水般涨落,简直让人窒息。这是一种行将死去的味道——那间几乎近月没开过窗的屋子、密不透光的窗帘、久不清洗的褥单、说话时胸腔如风箱般拉动的呼呼声、门外低低切切的啜泣——合在一起便是这种陈腐的味道。其他一切都能慢慢腐败,唯独诺言历久弥新。
院中久久无人打扫,春日潮地,万物都易生长,向阳处的小草已有二寸高矮,难收难管。祖荫心里一瞬间亦然如是,无数回忆纷至沓来,如阶角丛草,除了乱还是乱。玉兰树上新生的嫩叶却是绒绒的,叶与花一般好看。虽然花儿已尽归腐朽,眼前一切却是全新的。祖荫心里似乎也从纷乱中生出一丝期盼,颇有感慨之意:“樱儿,清流教你念书画画,你不晓得我有多兴奋。”微微一笑,像是自言自语,“起初见到他们夫妇二人,我简直惊奇得要命,世上怎么会有这样自由安闲的伴侣,能够凭着自己意愿结婚?后来往他们家去得多了,才渐渐知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他脸上鲜有一种如孩童般的纯真神色:“我原本已绝了指望,自觉人生不过如此。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只是心中的白日梦罢了。可自从碰到你,竟像美梦成真。”他的眼神一暗,叹道,“我极羡慕树之与清流,朝夕相对,再无旁人,何等美满?可我已允诺……亡师在先,不能食言……”他背向雪樱而立,一席话说得甚快,身后却毫无回音。院里的石阶亦悄然似反省,他只怕她生气,低低唤了一声“樱儿”,她仍是不言不语。他心里愈发难受,忍了又忍,缓缓转过身去,却怔在当地,良久苦笑一声,走去抚着她的脸道:“樱儿,这里对着门,当心风寒受凉。我抱你上楼睡罢。”雪樱这半月来日夜用功,本就是乏透了。方才将整个身子躲进椅子深处,说了两句话困倦上来,不知不觉便靠着椅背睡着了,此时慢慢睁开眼睛,见祖荫一脸怅然之色,自己也怪不好意思,口中忙不迭道歉。祖荫却像是乍然回神,双臂一展,已将她抱在怀中,摇头微笑道:“念书学画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不可求效太骤,欲速则不达。我看着你,你且好好睡一觉吧。”他将她抱上楼安置到床上,见她呼吸渐渐均匀,方轻轻松开手。只听后窗河里,船桨与流水回环相和时,一片溅水声,便起身走到窗边将推窗合上,静静退出房间。二楼的栏杆上挂了几瓣枯萎的玉兰,与朱栏相衬,黄扎扎地刺眼。他正欲伸手将萎瓣摘下,抬眼间却见巷口上似有人朝楼上远望,目光相对,马上就不见人影了。他心中大奇,只觉得这人有点眼熟,凝神回想,却万万想不起曾在哪里见过。院门啪啪被拍得一片响,还不等人应声,便咣当大开。进宝笑嘻嘻地领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进来,见他站在楼上,忙向上拱手道:“少爷,大掌柜家的前两天就把丫环预备好了,就等着您开口呢。我一去,嘱咐了两句便让带过来了。”又转身对那小姑娘道,“快给爷请安。”祖荫忙朝下摆手,回头看了一眼,见房门关得甚严,才点点头笑道,“也没什么安不安的。进宝也帮着忙,先把这院子打扫干净。”进宝答应一声,面上却浮起难色,想了又想,忽然扑通跪下,哭丧着脸道:“少爷,上次少奶奶遇见我……已经知道雪樱姑娘的事了。听说这半月一直在娘家……您还是赶紧回家看看吧。”祖荫怔了怔,缓缓皱眉道:“你怎么不早跟我说?”扭头看看房里,点点头道:“既然如此,你在这里瞧着,我回家看一眼就回来。”陈宅在青浦出了名的开朗畅通,门房也比别家显着敞亮。春阳和煦,照进房里暖洋洋的,深宅大院昼长人静,正是歇午觉的时辰。看门的老周喝了两壶浓茶下去,仍觉得困意浓浓,不知不觉便眼睛半阖。却好似有个不知趣的小贩摇着拨浪鼓在门房外徘徊,“登登登”的声音没完没了地响,惹人心烦。老周将眼睛睁开一条缝,斜眼一瞅,勉强瞧见一人背光站在外面,正以手叩门。他刚梦到发双倍工钱,正数钱间却被吵醒,自然不耐烦,将眼一闭道:“我家少爷出门去了,你有什么事过几日再来。”那人静了一静,脚步声便渐渐远去了。老周恍惚间忽然觉得不对,直直跳起身往外一看,又惊又悔,急急嚷道:“少爷,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灰蒙蒙的雨幕使黄昏更添了一种愁意,电车叮叮地摇着铃铛开过来,街上的行人撑着杏黄色的雨伞步履匆匆地走着。民国十二年八月初八,今天与最平常的日子本该没什么不同,但对禾生剧场来讲却非比平常——京剧名角程老板今晚将在此首演《红拂传》。他在京成名,此次赴沪首演,声势排场都十分惊人。现在离开演还有半个时辰,院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队伍等着入场。启铭钱庄的少东家齐云昊当然不用排队。小汽车刚在剧院的侧门处稳稳停住,穿着制服的门童就殷勤跑来将车门拉开,恭恭敬敬请他下车,引着往二楼的包厢去。齐云昊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身家自不必提,更兼长相俊美,连女子都要胜过,刚满双十还未曾婚配,引得一帮影星名媛如浪蝶般,整天无事也往钱庄去几趟。他又生成一种风流态度,来者不拒,今日和这个上报纸头条,明日又追捧那个明星。这一众女子,人人都离他远不远、近不近,不甘心又舍不得脱开手,纠缠不清。程老板这场首演,不知道经理替他约了谁,估计是刚红起来的沪上名媛王遥杳。听说这女子极会用手段,他不觉嘴角上翘,露出一个浅浅微笑来:若跟他用手段,倒要看看她有几分道行。上楼梯右转第五间,包厢门帘上贴张黄色纸条,上用楷书工整写着“已定 齐”。那门童将纸条撕下来,打起帘子请他进去。包厢里静静静的空无一人,小圆桌子上仿着西式摆设,铺着雪白台布,桌上搁着一枝鲜红的玫瑰花和烛台。他在心里冷笑一声:“真是不伦不类。我等着你,有多少手段尽管使出来。”女伴竟然敢比他晚来,这可十分罕见。虽说女士迟到天经地义,在他这里就要反过来,往往他是迟到那个。今日赶着看程老板的戏,好不轻易早来了几分钟,竟前所未有地被晾了场子,怎能叫他不生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剧场里坐满了人,渐渐嘈杂起来。台上的气灯刷刷齐亮,将舞台照得如同白昼,台下便先喝一声彩。敲过一巡开场锣鼓,这女子仍是不见人影,他冷冷地想:“我倒看你能忍得几时。”这出《红拂传》果然不同凡响,整整一个台子载歌载舞,端的叫人眼花缭乱。程老板扮的红拂女穿梭在一众舞姬当中,出尘脱俗。此时演她不愿再做歌姬侍宾待客,手持拂尘唱来一段二黄慢板。二黄板本就苍凉深沉,程老板的唱腔又极是清远雅致,隐约一点哀怨含而不发,台下如雷般叫起好来。云昊一心两用,双眼看台上,又分心听楼道的动静,不由焦躁起来。听楼梯恍惚有响动,却不是高跟鞋咚咚踩过来的声音,门童刻意压着低低的声音:“小姐,齐公子的包厢请这边走。”他嘴角浮起微笑:她到底来了。能忍到此时,委实不平常,起初倒将她小看了。身后的门帘动了一下,他哪里肯转过身去,只装作专心听戏的模样。此时红拂见李靖在座间,慧眼识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