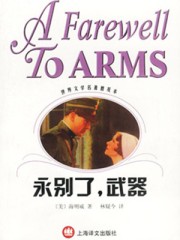别了讲坛-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养提得太高了,就回不来了,试问在职教师有一个研究生吗?
现在看来,这种争论简直无聊透顶!
所以,六月初,当叶县西湖中学的副校长郑直来教院招聘的时候,大家群情激昂,喊着豪言壮语:“不下海,不考研,不外聘,兄弟姐妹们,回城去!”尤其喊那最后三个字的热情,一点也不比当年的“看海去”和后来的“进藏去”缺少分毫。
吴雁南在杨玲的鼓励下,和同乡学友们一起回了趟县城。
每个人在心里都做过统计和摸底,叶县城关共有一中、二中、西湖中学和职业高中四所高中学校。对这七十多人,不可能满盘皆收,所以各校都要通过竞聘,择优录取。一中是省重点中学,说是只要应届本科生,即使要不到,也宁缺毋滥。其他几所学校没有一中那样的牛气,只能在省教院和其他成人学校毕业生中矮子里面选将军。语文学科,二中缺三人,西湖中学缺三人,职高缺两人。
在省城应聘屡遭打击的吴雁南,回到叶县城关,有一种随波逐流的感觉,潜藏心底的对杨玲的爱,也使他对叶县城关没有寄予太大的梦想和热情。谁料,在西湖中学的公开课评分上,他竟然高居第一!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申建文对他说:“吴雁南,你的课讲得不错,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你九月份可以来上班。”
他想笑,却笑不出声。本知道命运弄人,没想到命运竟这样捉弄自己。当他从叶县重返教院的时候,又和周明生双双接到新世纪学校录用的通知。鱼与熊掌同时涌来,怎么办?他把回乡应聘的结果告诉杨玲,杨玲说:“你回叶县吧,人的一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中国人都讲究个根,在新世纪工资再高不也还是一棵浮萍?——能进县城当然好,工作要尽力,为人也要在意,别弄得跟高加林那样,弄来弄去又弄回乡里了。”
“你看我像高加林吗?”吴雁南听了杨玲的话,既感激又觉得好笑。
“不是像,是很像,”杨玲开玩笑说,“也许我是多担心了,但谁让你的根也在农村呢?”
“我懂了,杨玲,我会时时留心处处在意的,谢谢你。”
于是在一天天的毕业临近中,在一次次的矛盾煎熬中,吴雁南彻底做出了回家的决定。他觉得自己很自私,但他只能自私。他想起自己在家乡石河中学教书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跟同村的一个年轻人为争宅基地发生了冲突。吴雁南当然站在父亲这边,那家伙便指点着他说:“高兴时我叫你一声吴老师,不高兴你什么都不是,我是没你书念得多,但这年头多念两本破书我看没什么了不起,还不一样住个破草房!阻碍国家康居工程发展的,就是你们这样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的半吊子家庭!”这些刻薄无情的话深深地烙在了吴雁南一家人的心里,他们知道那家伙的底气来源于他在上海打工挣到了一些钱。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吴雁南和他的父亲无心再争的时候,那家伙真就在吴家的老宅基上竖起了上下六间的楼房。吴雁南要来教院进修的时候,父亲说了一句话:“你花钱进修我不拦你,那是你追求上进。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希望你进修以后不要再回富农镇了,尤其不能再进石河中学!”
四
第二天早上,当吴雁南还在梦中重复那些和杨玲在一起或欢乐或忧伤的故事的时候,觉得耳孔发痒,狠劲抓了一把便醒了。睁眼一看,何书章正眯着一双小眼睛冲他坏笑呢。
“唉,你这家伙,专搅人家的好梦。”吴雁南埋怨道。
“都九点半了,还不收拾行李,真想等教院派人拿扫帚扫你出门啊?”何书章说。
这个何书章,特搞笑。可以肯定,凡是上过高中的人一见到他冬天的装束准会忍俊不禁。因为高中语文课本里有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他便是那插图漫画里人物的再现。别里科夫因“套中人”的“美誉”名满全球,你再看何书章,上教院的时候,他是全班五十人中唯一备有雨鞋的一个。天稍凉了,还下着点儿小雨,他就穿上黑色的皮夹克,竖起宽宽的毛衣领,脚上套着那双独一无二的雨鞋,打把大大的黑雨伞。他的眼睛近视得厉害,镜框是黑色宽边的,望去,镜框里面的小眼睛不过是圆圆的两个小点。他虽然不戴口罩,但有一副皮耳套,到更冷一点的时候就都焐在耳朵上。这样,教院里别里科夫的行头也就完全齐备了,大家见到他的时候都会会意一笑,心照不宣。
即便是个初中生,见到何书章,想象的空间里也会有清晰的定位。在初中英语教科书里有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教授为了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把食指伸进杯中的液体里,拿出来后舔了中指,骗得学生们都尝到了杯中的苦味。那篇课文为了直观还配了插图,教授是个矮胖、秃顶、小眼、眼镜掉在鼻尖上的短脖子老头。而何书章一米六十的身高全然又是教授的翻版,并且较之别里科夫只能在冬天的装束,他四季常在。所以大家为了避免过分的侮辱,更愿亲切地叫他“教授”。也许他不明就里,也许是太过和善,反正一听别人称他为教授,总是把滑到鼻尖的眼镜往上优雅地推一推。
他比吴雁南大几岁,在教院的两年一直睡吴雁南的下铺,家住叶县西山镇,和吴雁南是老乡,与吴雁南的关系一直很不错。他为人本分,做事细心,与人为善,富有爱心。尤其对待他的农村妻子和六岁的儿子,更是宝贝一样的想着念着,他常说在这个世界上老婆孩子就是他的全部不动资产。上次回西湖中学试教,他得的分数是继吴雁南和李爱华之后的第三名,现在的心情自然特别高兴。因为一旦能举家冲进城去,他老婆那双勤劳的双手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到时候,也就不用一家三口啃他一个了。
既然何教授说九点半了,那就真得起床了,吴雁南一边下床一边说:“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还要给儿子买点东西,你先走吧。”
“他们几个呢?”
“可能都走了。”
“他们几个的去向你都清楚吧?”
“知道一些,金成龙那个阿斗,肯定是不回去了。据说他叔叔县教育局金科长知道他在这关键年头留了校,打电话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他还敢回去?好在他本人一心要留在省城考研,这回留校了,正好有了理由,虽不怎么光彩,倒很充分的哦。”
“这我知道。”
“周明生说既然叶县城关不要他,他也不回去了。他还说他要勇逐潮流,贵族中学才是有才能的人驰骋的空间。希望他理想大于空想,以后生活能过得安稳。”何书章又说。
吴雁南想起了周明生在西湖中学应聘时倒数第一的悲惨遭遇,就觉得好笑,说:“这就叫‘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周明生又会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了。”
“周明生才不那么可怜兮兮的呢,他说‘此地爷不留,自有爷留处’,爷绝不让别人牵着鼻子乱撞。”
“他有点阿Q了。”吴雁南说话之间已收拾好了行李。
“不过,新世纪的确是省城最好的贵族学校,你能进却不进,怪可惜的。”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赵博远、彭明天、严莉莉进二中,李爱华也进西湖中学,洪长海、陈建江进职高。在这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时代,我们也都算各有所归了吧?”何书章很有些志得意满地说。
“各有所归——”吴雁南还想说点什么,电话铃响了,何书章顺手拿起听筒:“喂,你哪位,哦,弟妹啊,在,在在!”
何书章把听筒递给吴雁南,吴雁南白了他一眼,接了听筒说:“喂,杨玲。”
“你什么时候走?”杨玲问。她的家乡离省城近一些,下午回去,所以她要来送吴雁南。
“现在。”吴雁南说。
五
吴雁南迅速洗漱完毕,和何书章一人拎着一个大包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杨玲在楼门口等着,手里提着一个方便袋。在寝室外的广场上,一溜排着出租车长长的队伍,吴雁南要了一辆,打开车门,在何书章的帮助下,把包塞进去。
“雁南,吴雁南!”有人叫道。
吴雁南手扶着打开的车门,搜寻了半天,才在男生宿舍楼的一个窗口上,找到了那张长头发遮着的瘦脸。那是艺术系的寝室,喊他的是美术班毕业生叶家宝,他和吴雁南不仅是叶县老乡,还都住在富农镇。
吴雁南想了想就冲叶家宝挥了挥手说:“回去再联系!”
吴雁南和杨玲上了车,就听到后面一片声地叫喊:“一路顺风!”“心想事成!”“前程似锦!”有送吴雁南的校友,比如何书章,也有送别人的,反正是送别,后走的干脆齐声叫着,也不在意那被送的是谁了。想必,他们美丽的祝福也是为自己祈祷的吧?。
今年是千禧之年,千禧之年发生了多少大事,这些教院毕业们很少记得住,潜藏在每个人心底的,是对前程的担心和臆想。都说进修者多是乡村中学的老师,其进修目的有三:考研,换单位,找对象。但两年时光弹指一挥,上天不会一分为三地给大家做出安排:让三分之一攻读硕士,让三分之一如愿跳槽,让三分之一情有所归。实际上多数人都还是原来的样子,老是老不到哪儿去,那定在暑假的一个日子,你就是来拿了本科毕业证,你的身份也依旧是个老师。更何况人们都说:富人无须要文凭,穷人要了也没用。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几乎所有来进修的乡中园丁,经过两年的城市生活,都像吴雁南一样,被学费、生活费和一些意想不到的额外开销,弄得一贫如洗甚至负债满身了。他得感谢金成龙的五十元钱,要不然他昨天就只能对杨玲空口说祝福,今天也就无钱坐车了。
出租车穿过落泊零乱的校园,很快驶出校门,上了大街。吴雁南的目光拂过高大的建筑,拂过宽阔的马路,拂过穿梭的车流,拂过奔忙的人群,转到了杨玲的脸上。他这时才注意到,杨玲的眼睛有些红肿。
“杨玲,我真不想走了。” 吴雁南说。
“但你没有回头路了。”杨玲说,双眼迷茫地望着前方,镜片上又开始洇湿着潮气。女人的确都是泪做的。
“我们县城的西湖很美,我等你去看。”吴雁南说。
“我希望我能去到。”
“西湖盛产银鱼,去了,我请你吃。”
“我希望我能吃到。”
到了长途汽车站,吴雁南找到回叶县的车,先把行李在车上安置好,又回到杨玲面前。两个人对视了一会,没有话。
“给你。”过了一会,杨玲递过来手里的方便袋。
“什么?”吴雁南没有马上伸手去接。
“一点吃的喝的。”
“你留着吧。”
“天太热,路上用得着。”
是的,天气比昨天更加闷热了,吴雁南真渴望马上就能下一场雨,浇一浇自己焦躁不安的心。他接过袋子,望着杨玲的眼睛,杨玲的眼睛很快红了,泪水止不住地落下来,吴雁南手足无措了。
“杨玲,我会来看你的。”吴雁南说。
“嗯,一路平安。”杨玲说。
“杨玲。”吴雁南声音低沉地叫道。
“你——”杨玲的话没有说完,她实在说不下去,便转过身,捂着脸,脚步蹒跚而疾速地走了,不多久便被人海淹没。
“杨玲,我会去找你的。”吴雁南在心里一遍又一遍抽搐地叫道,视野里却早已没有了杨玲的身影。
消失了,不见了!不见了,往后的日子,还能再相逢吗?分手原来如此简单,在广阔宇宙的时空里,竟然只浓缩在这短短的一瞬。男人和女人之间,只有承诺和泪水,在这承诺和泪水背后,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无奈。
六
汽车向西行了三百多里,在省道和一条狭窄破旧的柏油路接口处,扔下吴雁南向北方的县城疾驰而去。吴雁南转上一辆中巴,在柏油路和石子路的接口处,又转上一辆小巴,小巴在石子路上便只能象蜗牛似的爬行了。到家的时候,已是黄昏,血红的太阳垂在天边。
这是三间八十年代典型的草房,夹在砖墙瓦顶的现代民居中间,分外醒目。不论吴雁南承认与否,接受与否,这里都是他的家,是他安排好工作之前白天吃饭晚上睡觉的地方。母亲坐在门前,被夕晖重重地围着,她在缝补装化肥用的塑料袋。吴雁南丢下行李,走上去叫了一声“妈”。
“南儿,你回来了?”母亲万分欣喜,双手捏了针,望着儿子微黑可爱的脸庞说。
“我回来了,妈,稻还没抽穗吧,用得着这么早吗?”
“你这孩子,书都读哪里去了,闲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凡事要做在前面,稻子一抽穗,转眼就黄了呢。”母亲笑着教育起儿子来。她一共生了四个儿女,就这么一个儿子,最小也最争气,是村子里第一个通过考学吃上皇粮的。女儿们早已出嫁,这个老儿子便是她和老伴的全部,虽然都二十八岁了,但没结婚,就还是个孩子。更何况,子女在父母的眼里一辈子也长不大啊。所以,她是打心眼里疼爱儿子,看到他心里便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