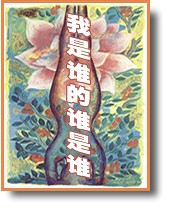谁的荷尔蒙在飞 作者:三蛮-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操!你奸淫幼女啊,你!”半响,老K第一个做出反应。
“还敢说你没搞过!”大锯跟着使劲。
“小孩,没你们想的那么下流。”
“你那时候直了吗?”该死的小茹梦总是十分关注细节。
“不记得了。反正我就是记得有的男孩往里尿尿了。”
“玩到几岁呀你?是不是一直玩到高三啊?”我严肃发问。
“没有,有一次让一个小女孩她爸回家给看见了,拎起来就是一顿揍,把我们都吓坏了,提了裤子就跑,后来就没人敢玩了。”老大意味深长的回味道。
“行啊你,还没忘提裤子!”老K不阴不冷的笑骂。
“过去小,不懂事,咱就一笔勾销了,现在跟大胸炊姐到底怎么回事?”大锯依旧不依不饶,“说!整到哪一步了?”
“是不是往里尿尿了!”小茹梦怒喝。
在大家笑得一片人仰马翻好久才喘过气,老大终于告诉了我们真相:“就是个一般老乡,关系处的不错,平时互相照应呗,我去打菜的时候能多给点,钱也能少收点,有时候她要是心情好,我就吃饭不花钱,偶尔有时还能倒找我点儿哪!”大家随即纷纷感叹老大的老谋阴险,一会儿宿舍里便渐渐的安静下来,众人趁着乐意纷纷睡去,大锯也心满意足的回了屋。
“小楼,真能憋出病吗?”半夜三更,老大突然踢床板的悄悄问我。
“能!心脏病!”
(5) ……
(5)
除了弹吉他和偶尔的上上课,我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会给杨红写封信,添油加醋的给她描绘渲染我的所作所为和情绪状态,最近又发了些什么白日梦,学校又发生什么怪闻趣事然后以“我都想你想到吐白沫子了!”结尾,并附上一张最新的日记,杨红的回信可没有我那么神采飞扬,只是流水账似的说一些学习生活,然后附上一张诉苦日记:素描课被老师骂基本功不行了;水粉不知道让谁偷用了;由于太多男生找她,同屋女孩又制造事端了,由于上了次校报,又有几个菜鸟向她示爱了,最后总是以“长得漂亮是爸妈生的,我又招谁惹谁了!”结尾杨红总是嫌我写的少了,我却总是嫌她写的不够深入,不跟我掏心窝。
没多久随着天气的变冷,我们的热情好像有所褪减,信,也是一个星期一封了。
“性博士,敢不敢和我出去跑场子去?”一天磕琴时老K突然问我。
“你不是挺能骗钱的吗,跑场能骗几个大银?”
“光搞些鸡巴推销策划有鸟意思!够胆子咱们就扛吉它去踩几个酒吧,咱们玩艺术挣钱!”
“咱这水平行吗?”
“行不行再说,我问你敢不敢?”
“你敢我就敢!”我使劲在琴上扫出一阵强力和弦。
“好!像个爷们!”
我的吉他是大一时老K教我的,这个兔崽子高中时就会了,入学那天就小试牛刀的给我们弹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当时立马就把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镇的死死的,后来,流水光阴,随着大家一起的眼界开阔和见多识广,才渐渐对老K的这几板斧不以为然起来,现在再唱起老K写的那些歌,老K自己都很是过意不去了,摘段歌词如下:“希望有一天,你来我家找我,我们手拉手,一起去跑步和游泳……”
(6)
“我们肯定比他强多了!”老K瞪着眼珠子跟酒吧老板发誓,“他就一个人,吉他和声音一个人你怎么也出不了层次,没和声的歌,怎么听都是干巴巴的。”见老板反应不大,老K继续满嘴吐沫星子的瞎诌,装腔作势的比划,活像个菜鸟歌手大赛的老不死评委。
台上表演的那哥们的琴其实我一看就知道比我俩强多了,随便唱什么歌琴都能跟着,而且还能加上“花儿”,唱得也不错,真声假声交替使用,每每遇到高音区还要貌似陶醉的盘旋上一阵才肯下来,以博取台下酒包们的掌声与喝彩。
“你们俩一起走多久了?”酒吧老板斜着眼睛问我。
“三年了!”
“都跑了那些场子啊!”
“都跑了那些场子还真不好说。”老K急忙替我解围,“反正除了你们这一片儿来的少,其它都常走。”
“行,一个晚上三百,下礼拜六晚上九点开始,你们上吧!”老板不住地点头如捣蒜,“记住,多来点英文的,经典的,我们这边白领多,好这口儿!”
“那,准了!”老K一脸的理解与不在话下。
随后,我度过了自高三后最为充实的一个礼拜。
老K和我每天和我像疯子似的扒谱子练琴,老K还专门找了些艺术系的女生教我们怎么找拍子怎么吐气发声怎么颅腔共鸣(就是唱歌时让脑袋跟着嗡嗡响),无恶不作的老K甚至都自学了一点儿老王菲的那种爱尔兰花腔,以准备留到表演时制造点高潮。
就这样一直忙到了礼拜五的晚上,我俩算了一下,算上那些不会分解只会扫弦的一共是十五首歌能从头到尾弹下来,“够了,一本磁带才十首歌都能听一晚上,咱们这都富裕了!”老K累得直嘟囔。
礼拜六早上,一个屁把自己臭醒,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连忙大喝:“老K,咱们就拿自己这两把破木棉吉他上啊?”话音未落,老K就像挨了电棍似的从床上弹起,随即如梦方醒般飞奔出校,绕着这座老城东西南北各穿梭了两遍后,于下午拎着两个大琴箱子回到宿舍,一边狼吞虎咽的喝水一边嘟囊“这俩老破逼箱子,比琴还难借!”
我俩于是赶紧开始熟悉那两把电民谣,时不时互相打气:“你弦扫得真‘暴’!牛逼!”
“不是你唱得也太牛逼了!我颅腔都跟着共鸣了!”
“歌词记不住怎么办”吃晚饭时,我胃口不佳的还是有点忐忑。
“没事,把记住的多唱几遍,实在不行就哼哼‘啦啦啦’”晚饭我俩都没有吃多少,两腿发软的拎着大琴箱子走到校门口,正好迎面碰到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师妹,“师兄,师兄,有表演哪?”
“啊!跑两个酒吧!赶赶场!”老K一个甩头突然装酷,让我也蓦地有些发飘,于是便用眼角朝斜下方冷冷的扫了她们一遍。
演出本来从晚上九点到十二点,可我和老K那天十点半就回到了宿舍,人家把我们开了,第一首歌都没让唱完,就开了!
(7)
那天那个狗屁酒吧里人声鼎沸,我和老K拎着大琴箱子上台后先花了半个小时把两个吉它音响弄出声来,在台下哄声四起的情况下我们又花了十五分钟把吉他校正音,终于开始唱时我俩已经紧张忙碌的浑身湿透几乎虚脱。这时我一个闷屁放过,又想起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俩忘练和声了,一个礼拜都忘得死死的。
“去它妈的,一起唱!一个调!”调音响调得两眼发直的老K已经变得歇斯底里,忘记了话筒已在嘴边,全场观众都听见了他的骂声“去它妈的,一起唱!一个调!”
那是首烂的不能再烂的校园民谣,练过琴的孩子几乎都会弹,平日里我俩也配合的非常流畅,可那天真的是倒了血霉,琴声一起时,观众们可能是由于听到骂声,全场一片寂静,感觉相当不错,一下我就发现了我的琴音不准,可老K并未发觉,一个劲儿的示意让我加“花儿”,我顶着头皮走了一段,实在太难听,便立马改用根弦走贝司音。
第一段吭哧瘪肚的坚持下来后,第二段一开头就出了事儿:我们俩唱的歌词总是不一样!我俩又临危变阵决定一人挺一段儿,就在一顿瞎弹滥唱快要把第一首歌对付到结束的时候,老K由于闭着眼睛过于抒情的摇头摆脑,一下把身前的麦克风撞翻了,一阵刺穿耳膜的尖鸣后几个艳舞女郎上台才把我们救下场,收拾好大琴箱子后酒吧老板走过来一句话也不说的指了指我俩,又指了指门口。
我猜那应该是“滚蛋”的意思,于是便低头羞愧的往外走,可老K依然豪情不减,勇敢地上前问了句“哎!那钱,还给吗?”
回来路上我和老K又算了一下,投入的感情不算,光钱财就损失了二百余元,到宿舍后我们又破罐子破摔地请舍友们出去喝了顿酒。
“哎呀!那家伙!别提了!咱们第一首唱的是校园民谣吧?”老K看看我,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哎呀。第一首校园民谣刚唱到一半,就有几个的观众被唱哭了。感人哪!后来为了照顾他们情绪,我俩都不敢唱慢歌了,一律改唱快歌,没想到这反应更大,唱到最后,唱的那些观众都疯了!疯了!你懂吗?”老K瞪起眼珠看大剧,张牙舞爪的比划起来“就这样!就这样!根本就不让谢幕!那观众……都哭啊!就差把我俩绑起来了,最后不得不加唱了五首,五首啊!”老K伸出五个手指,再次比划“……才让走!”
“是啊?真的假的?听着怎么这么像麦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哪,下次什么时候还去啊,带我们见识见识。”大锯说道。
“对!我还没去过酒吧哪!”茹梦也说。
“行!下次去,一定带你们!让你们感受一下!”老K回答一顿胡吃海塞。
桌面狼籍,我醉醺醺的问老K:“痛快了?”
“痛快了!”老K也喝得眼神迷离。
那天夜里我还是因兴奋过度而死活睡不着,于是在床上点起蜡烛撅着屁股给杨红写了封信,汇报一下受害经过并发了些毒誓以后一定脚踏实地的好好做人。
写完信时天已微亮,窗户边忽忽的传来阵阵凉飕飕的秋风,顺着看过去,窗户的树叶已经开始掉了不少了。
小红这懒猫肯定还在熟睡,真不知道她那边儿是不是也变凉了。
(8) ……
(8)
酒吧受挫的第二天我一脚把吉它踢到床下死角,从此潜心研究起了我的摄影术,暑假时我给小红拍了十几卷黑白乐凯,但到现在还没冲出一张照片,我于是给自己下了死命令:十天之内全冲出来!
我于是便又经历了十天非人的折磨,由于那本叫什么纽约的大厚摄影书上关于暗房讲的很少,于是我只能自己瞎摸,冲底片到还顺利,可到了洗印的时候就头皮发麻了:放大机相纸还有那么多盆盆罐罐那么多药水药方我一概不知怎么用和怎么个顺序,第一个晚上我花了半个晚上在水房把东西摆好,然后又花了半个晚上把东西收好,根本无从下手!第二个晚上大锯陪着我一起拿着相纸蘸饺子似的蘸蘸这个蘸蘸那个,还是没有出人儿,第三天晚上我宣布,谁给我在相纸上整出人儿来,我给他拍个写真集,于是大锯茹梦老大老K一干垃圾人等全部到齐,搞到半夜摔碎了一根温度计掀翻了二次显影盆后,五条汉子默声哀叹:“古人说的对!书生无用!书生无用!”
在我们收摊子的时候,大锯屋的“小不点”突然拉夜尿经过,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摆了摆,按了按,没用几下就显出了一张人影儿,看着杨红在相纸上一点点出现我激动万分的举起了“小不点”。
以后的几个夜晚“小不点”天天都在一旁静静的陪着我并教会我许多的暗房知识,然而我却多少总有些心怀愧疚。
我和“小不点”本来是同屋,开学没几天我俩就因为约等于‘一块橡皮’的屁大点儿事打了一架:我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在我床上浇了一脸盆凉水(这让当时闻讯前来劝架的大锯极为不满,骂我们是“老娘们打仗”),随后老大换来我们屋,我们这两年也就没怎么说过话,但也不能全怪我,其实这两年在学校里,他跟谁的话都不多。
小不点,人极为聪明,高中时就在省数学竞赛拿过奖,还有过天文望远镜之类的大发明,但他有时也很极端,开学时大家胡乱发言作自我介绍时,轮到他时他说:“我认为不做爱因斯坦那样的人,活着就没意思!”,同学一片哗然,把随后发言的老K也镇蒙了,差点没说:“我认为不做爱,那样人活着就没意思!”
“小不点,谁教你的这手艺?”有一天晚上在等底片晾干时,我问。
“我爸是个化学老师,小学时就教我在家做暗房洗照片了。”
“老师的孩子就是幸福!”我感叹道。
“也有不好的,比如说从来都不敢逃课什么的。”
“对了,你现在为什么,好像也不愿意去上课了?”
“咱们学校老师的水平不行!”小不点淡淡的说。
“不都摇头摆尾挺能吹的吗!”
“净是瞎吹,其实他们的数学素养和逻辑结构都比不上我们高中的老师。”
“那你的大学算是白上了!”我故意逗他的说。
“对,是白上了!连次恋爱都没谈过!”小不点冲我腼腆的笑了笑。
我蓦地一阵心酸,一股莫名的悲哀奔袭而来,那是种与生俱来的敏感而带来的悲哀,我分不清那悲哀是为了小不点还是为了我自己,那是一种我永远不明所以却又挥之不去的悲哀。
“你以前喜欢玩什么”我转移话题以掩饰情绪。
“天文方面的,观测一些星座什么的。”
“那东西不闷嘛,那么老远老远,一动不动!”
“不闷!那里是另一个时空,一个未知的时空是很有意思的!”小不点朝我难得的神气十足了一下。
“最近还观测吗?带我看看。”
“好久





![(HP同人)[HP]谁的月,谁的夜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29/2917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