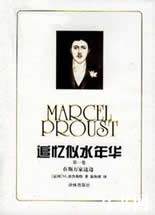追忆似水年华[美]-第4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对我的感情如何,这些感情是出自对物质利益的考虑抑或出自爱,对此我更是不甚了了。我会猛然忆起某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比如,阿尔贝蒂娜想去圣马丁,说她对这个地名感兴趣,也许无非是因为她认识那里的某个农家女。不过埃梅把淋浴场女侍告诉他的这件事通报我也无妨,因为阿尔贝蒂娜永远也不会知道他通报了我,在我对她的爱情里,我什么都想知道的需求总是被我想向她显示我什么都知道的需求所压倒;这虽然消除了我俩不同的幻觉之间的分界线,却从没有取得她更爱我的结果,倒是恰恰相反。然而自她去世以后,第二种需求和第一种需求所取得的结果合二而一了:我以同样快的速度想象出一场我希望向她通报我所了解之事的谈话和一场我想向她打听我不了解之事的谈话;即是说我看见她呆在我身边,听见她亲切地回答我,看见她的双颊又变得丰满了,眼睛也失去了狡黠的光而变得哀伤了,也就是说我还爱着她而且在孤独和绝望中我已忘记了我疯狂的忌妒之情。永远也不可能告诉她我所了解的事而且永远不可能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我刚发现的真相的基础之上(我之所以能发现恐怕只是因为她已经死了),这令人痛心的不可能之谜以它的哀伤取代了阿尔贝蒂娜的行为的更令人痛心的谜。怎么?我那么希望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已了解淋浴场的故事,这时阿尔贝蒂娜却不复存在了!我们需要思考死时,却除了生以外什么也不可能去考虑,这又是我们面临的不可能性的结果之一。阿尔贝蒂娜没了;然而对我来说,她仍旧是向我隐瞒她在巴尔贝克和一些女人幽会的人,仍旧是自以为已成功地让我对那些事一无所知的人。当我们在思考我们死后发生的事情时,我们此时的错觉不是仍然会使我们想到活着的我们自己吗?说来说去为一个去世的女人不知道我们已了解她六年前的所做所为而遗憾这是不是比我们希望一个世纪以后我们死了还受到公众好评滑稽得多呢?即使第二种假设比第一种有更多的实际依据,我这马后炮式的忌妒心引起的遗憾却仍然和那些热衷于身后荣耀的人的看法错误如出一辙。不过如果从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分离中得出的庄严的最后印象暂时取代了我对她那些错误的考虑,这印象也只能赋予这些错误以无法挽回的性质从而使它们变得更加严重。我看见自己在生活中那样不知所措就好象我独自站在无边无际的海滩上,无论我走向何方都永远不能与她相遇。
幸好我及时在我的记忆里找到了——因为在一片杂乱无章里事物总是五花八门的,这几样危险,那几样有益,其中连回忆也只能一个一个地现出清晰的轮廓—— 发现了我外祖母的一句话,有如工人发现了有助于他要做的活计的物件。在谈到淋浴场女侍告诉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一个不太可能的故事时,外祖母对我说: “这个女人恐怕得了撒谎症。”这件往事大大帮助了我。淋浴场女侍告诉埃梅的事有什么意义呢?更重要的是她当时根本什么也没有看见。谁都可能和一些女友一道去淋浴却什么坏念头都没有。那个女侍把小费说多些也许是为了吹牛。有一次我就亲耳听见弗朗索瓦丝认定我莱奥妮姨妈当着她弗朗索瓦丝的面说她“每月可以吃上 100万”那样的疯话;还有一次她说看见我莱奥妮姨妈给了欧拉莉四张1000法郎的钞票,而我认为一张折成西迭的50法郎的钞票都不大可能是真的。我就如此这般地探索下去,而且逐渐摆脱了我经过那么多周折获取到的令我痛苦万分的确切消息,因为我总是处在渴望了解而又惧怕痛苦的矛盾之中。这一来我的爱应该可以复苏了,然后随着我的爱情的复苏,与阿尔贝蒂娜离别的忧伤也紧接着复苏了,处在这忧伤的时刻我也许比前不久备受忌妒心折磨时更为不幸。可是每当我想到巴尔贝克这种忌妒心又会突然出现,原因是我仿佛突然重见了巴尔贝克饭厅的图景(在此之前这图景从来没有使我难受过,我甚至认为这是我记忆中最不使我痛心的画面之一),每天晚上,玻璃窗外总有一大群人挤在阴影里,就象挤在水族馆里明亮的玻璃隔板前似的,他们瞧着里面稀奇古怪的人们在亮光里走来走去,可是拥挤又使渔妇和平民姑娘摩肩接踵地碰撞着(我从未想到过这点)小有产者的小姐们,这些小姐对里面的豪华十分忌羡,那种在巴尔贝克还很新奇的奢侈,即使不是家境起码也是吝啬的习惯和旧的传统使她们的父母未敢效法,在这些小有产者小姐里几乎每天晚上都肯定有阿尔贝蒂娜,当时我还不认识的她恐怕已经在那里搜罗小女孩了,也许过一会便会找到一个女孩而且同她一起乘夜色去到沙滩或峭壁下某个荒废的浴场更衣室。忧伤又紧接着攫住了我,我象听见判决我流放似的听见了电梯的响声,电梯没有在我这一层停下,直开到楼上去了。我望穿秋水却永远也见不到我那唯一的客人来访了,她已经死了。尽管如此,每逢电梯停在我这一层时我的心仍然会狂跳起来,有一阵我曾想:这一切果然是梦该多好!这也许是她,她快按铃了,她回来了,弗朗索瓦丝就要来通报我:“先生恐怕一辈子也猜不出谁来了。”说她怒发冲冠不如说她胆战心惊,因为她的迷信超过了她的报复心,她害怕活的阿尔贝蒂娜也许远不如她害怕她所谓的阿尔贝蒂娜的鬼魂。我试着什么也不去想,便拿起一张报纸。然而阅读那些没有感受过真正痛苦的人写的文章简直让我受不了。一个人在谈到一首不值一提的歌子时说:“真是催人泪下”,可是如果阿尔贝蒂娜还活在人世我倒会兴高采烈地听这首歌子。另一个人,还是个大作家呢,在下火车时受到欢呼便宣称这样的表示是“令人难忘的”,换了我,倘若我此刻也看见这种表示,我恐怕一刻也不会想到是“令人难忘的”。第三个人保证说,如果政局不那么糟糕,巴黎的生活会“美妙无比”,然而我完全清楚,即使没有政治这儿的生活也只能使我感到难于忍受,如果我找回了阿尔贝蒂娜,即使政局糟糕,生活于我也是美滋滋的。狩猎专栏的编辑说(时值五月):“这段时间对真正的猎人来说实在令人头疼,说得更确切些,真是灾难性的,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可猎。”
“展览”栏的编辑宣称:“这样组织展览会使人感到万分扫兴,令人愁煞苦煞……”如果说由于我自己感觉敏锐,那些从未经历真正幸福或不幸的人说的话便显得既虚假又苍白无力,与此相反,那些最无关紧要的一行一行,无论多么风马牛不相及,只要能和诺曼第或尼斯挂上钩,只要能和温泉浴场或伯尔玛,和德·盖尔芒特公主或爱情,或失踪,或不忠实这些概念沾上边,都会在我来不及转过头去的瞬间突然使阿尔贝蒂娜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于是我又会潸然泪下。而且我通常是无法去阅读这些报纸的,因为翻开报纸这个简单的动作本身就会使我同时想起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我的类似的动作,而且想起她已离开人世;我根本没有力量把这份报级全部翻完便又把它扔下了。每一个印象都会引起同样的然而又是伤痕累累的印象,因为阿尔贝蒂娜已经从这些印象里消失了,因此我永远没有勇气坚持度过这些支离破碎的令我伤心的分分秒秒。甚至在她的身影逐渐停止出现在我的脑际却又强有力地萦绕在我的心间时,如果我需要象她在世时一样走进她的房间里去点灯,去坐在自动牌钢琴前面,我也会突然心酸难忍。她仿佛分成了若干小小的家神,久久停留在蜡烛的火焰里、门的执手上、椅背上以及别的更无形的领域,这就象我在不眠之夜的感觉,或我喜欢的女人初次来访时引起的躁动不安。尽管如此,我在一天里过目的或尚能忆起的寥寥几句读过的话仍然常常引起我强烈的忌妒。这寥寥几句勿须对我提供女人伤风败俗的充分论据,只要重新唤起与阿尔贝蒂娜的生活密切相联的我旧有的印象便能达到目的。阿尔贝蒂娜的过失一旦移运到某些早已遗忘的时刻,由于我回顾她还活着的时刻的习惯并没有衰退,她的过失便增添了某种更贴近、更揪心、更残酷的意味。于是我再一次问自己那海滨浴场女侍揭露的事是否真会是假的。要想知道实情,最好打发埃梅去一趟尼斯,让她去邦当夫人的别墅附近住上几天。倘若阿尔贝蒂娜热衷于女色,倘若她离开我是因为不愿意更长久地被剥夺这种乐趣,她一旦得到自由,便一定会立即去那里设法重演故伎而且会取得成功,假如她不认为去她熟悉的那个地方比在我家更方便,她肯定不会选择那里去躲避起来。阿尔贝蒂娜之死使我忧虑的心境改变如此之微小这无疑是不足为怪的。一个人在他的情妇健在时,构成他所谓的爱情的相思大多来源于她不在身边的时刻。因此人们老习惯于以不在身边的人作为遐想的对象,尽管这个人只有几小时不在,这不在场的人在这几小时里也只属于回忆。由此可见死亡并不会使事物有什么大的改变。埃梅一回来,我就请他动身去了尼斯,这一来不仅根据我的思想活动、我的悲哀、我因联想到某个远而又远的人的名字而产生的躁动不安,而且根据我全部的行动,我进行的调查,我为了解阿尔贝蒂娜的行动而花费的钱财,我可以说这一年里我的整个生活都充溢着爱,充溢着我和她之间实际存在的恋情。而这一切活动的对象却是一个死人。人们有时说,倘若某个人是一位艺术家而且往作品里注入了一部分自己,这个人身上的某些东西便可以在他死后犹存。从一种生物体内抽取出来又嫁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部的东西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尽管被抽取生物的母体业已死亡,这也许出于同一个道理。
埃梅去尼斯住在邦当夫人的别墅附近;他认识了一个女仆和一个阿尔贝蒂娜常去租一整天汽车的汽车租赁人。这些人什么也不曾注意。在第二封信里,埃梅告诉我他已从一个城里的洗衣女那里打听到在她给阿尔贝蒂娜送衣服时阿尔贝蒂娜捏她手臂的方式很特别。“不过,”信上说,“这位小姐并没有对她做别的事。”我把埃梅的旅费寄去,这笔钱也算付了他的信引起的痛苦的费用,与此同时我却在竭尽努力医治我的苦恼,我对自己说那个动作不过是一种亲热的表示,并不能证明有什么邪恶的欲念,这时我又收到埃梅的一封电报:“打听到最值得注意的情况。给先生弄到大量消息。信即到。”第二天我果然收到了一封信,光看信封我就簌簌地颤抖起来;我认出那是埃梅的信,因为每个人,甚至地位最卑微的人都管辖着一些熟悉的小生物,它们是活生生的但又仿佛发僵地躺在纸上,那就是每个人特有的字体。
“起初那小洗衣女什么也不愿对我说,她保证说
阿尔贝蒂娜小姐除了捏她的手臂没干过别的。为了
让她说出来我带她去吃晚饭,请她喝了酒。于是她
对我讲了阿尔贝蒂娜小姐去洗海水澡时常在海边碰
见她的事;阿尔贝蒂娜小姐习惯一大早起床就去洗
澡,而且照惯例总在海边的一个去处把她找到,那
里树木茂密谁也瞧不见谁,再说在这样的时刻谁也
不会去看谁。后来洗衣姑娘把她的女朋友们也带到
那里去洗澡,后来,那里天气已经变得很热了,甚至在树荫下太阳也很烤人,她们便去草丛里互相擦
干身子,互相抚摸,挑逗,玩耍。洗衣小姑娘承认
她很喜欢和她的年轻女友们逗乐,她见阿尔贝蒂娜
小姐贴着她的身体搓揉时还穿着浴衣便要她把浴衣
脱了,洗衣女便用舌头沿着她的脖子和手臂舔呀舔,她甚至舔了阿尔贝蒂娜小姐伸过去的脚掌。洗衣女
也把衣服脱了,她们还在水里追逐嬉戏;这天晚上
她就对我讲了这些。不过为了忠实执行您的命令,为了不惜一切使您高兴,我还把小洗衣女带回去和我
睡了觉。她问我想不想让她再做一遍阿尔贝蒂娜小
姐脱了浴衣后她做过的事。她还对我说:‘您真该看看她怎样地动来动去,这位千金小姐,她对我说:
(啊!您简直让我快活疯了!)她浑身酥软,禁不住啃起我来。’我还看见了这洗衣姑娘手臂上的痕迹。
我也能体会阿尔贝蒂娜小姐的快活,因为这小家伙
实在太乖巧了。”
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告诉我她对凡德伊小姐的友情时我确曾苦恼不堪。然而那时还有阿尔贝蒂娜在我跟前安慰我。后来由于我过于渴求了解阿尔贝蒂娜的行为,我达到了让她离开我家的目的,当弗朗索瓦丝通报我她已离去而只剩下我自己独处时,我却经受了更剧烈的痛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