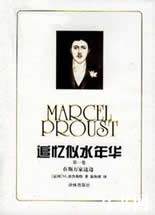我的似水年华-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见面,他就笑得什么似的,我说,叶校长也有却场的时候啊,哈哈,好你一个小叶啊,今天什么场合啊,你没看见台上台下都坐了些什么人啦,今天到场的可都是领导,专家和学者,你怎么倒象个蹩脚的乡下小耍猴的,干吗呀,没精打睬地?平时看你优雅得爱死个人了,今天怎么了,怎么那么狼狈啊,象害了大病,不会真病了吧,他一连串地笑着我,关切地问着。
我知道我今天这场戏可能真没有演好,但我也没有觉得怎么不得了,不就一个典型发言吗,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所以,对这事我倒没有放在心上,我是有别的目的,到这里来。
嘿呀,你不知道,我走上去,眼睛朝下面这么一扫啊,哎呀我的天,就要晕死过去了,那叫一个怕,我什么时候看见过这么多脑袋呀!不骗你,我当时滚下台来的心都有了,可是,关键时候,我想起了领导的殷殷期望,各位同仁的拳拳之忱,我要命也得撑下去呀,所以————我和他互相贫着。
哈哈哈哈,他笑得那叫一个爽!
从他那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今天在会场上看见的那个人,那并不是幻觉,真的是他,江少陵!
张主任以前是省教研室的主任,今年换岗,到省教育厅办公室任主任,而教研室主任他说是新来的江主任,以前是哪个地级市教育署的。张主任热心地说,老江我们以前就认识,相当不错的一个人呢,怎么,要不要给你们介绍一下,以后见面互相关照的机会还多呢。我当然拒绝了他的热心。这个世界真的不太大,居然在这里又碰到了少陵!
三十三
我没有立刻回宾馆去,而是沿着大街漫无目的地走着。快九年了,我们从来就没有联系过,我心里并不是没有回想过那些曾经的点滴,不是没有过感叹和失落,就在我最失意最痛苦的日子里,我眼前也会浮现那张英俊得让人眩目的脸孔,我也时常咀嚼着“你如果反悔了就来找我”的话,但是———我总觉得人的命运就象早已经被人在三生石上刻好了一样,冥冥之中总有人在掌握着你,所以往往“阴差”对的是“阳错”,“南辕”对的是“北辙”。
就那样,逛得街灯辉煌起来,我才往回走,到宾馆时已经夜深人静了。大厅里,还有新来的客人在登记,我穿过大厅就要上楼,这时,有人叫我,扭头一看,是他!
到房间坐下来,我们才开始说话。
今天你运气真好,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位校长今天赶回去了,好象她们学校出了点什么事,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和我多说会子话,我笑着打破僵局。我觉得我很聪明,很自然地就先说出话来了,因为从在大厅里和少陵见面到现在,我和他都很沉默,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话刚说出口,我突然觉得我简直滑稽得窝囊透顶,这么多年的同学见面,互相没有问声好,就说那些无油无盐的话。
还是他比较“老练”一点,打破尴尬,和我说起今天的典型发言出现的窘场。原来我开会刚来时他就知道我来了,一直没有露面,一是因为还不知道怎么和我见面,二来他也刚调过来,工作交接千头万绪。今天他们教研室全体都参加会议,他不想让我发言前看见他,就一直没有出现,没想到,我刚往讲台上走去时,他就走了出来,站在门口,连座位都还没有找,鬼使神差,我就那么一眼,就看见了他。我们有感应吧,他笑着说,都怪我,出来得太着急了点,差点就误你大事了。
看他的眼睛笑起来还是那么好看,刀切般的双眼皮,整齐均匀,一笑起来,眼皮都能说话,呵呵,我讨厌自己居然看得那么细致。和少陵见面,要说的话千头万绪,一时间还真不知从何说起。看着他还是那么年轻,悄悄说,更有男子汉的魅力了,怎么男人这么多年就没什么变化呢,甚至越变越有味儿,我心里坏坏地想。
想问问他的家庭,又怕提起过去的事情,想问问他的工作,又明显在无话找话,想问问他的子女,又怕他问我,踌躇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他看起来也难受,干瞪着眼什么都没有说,两人就象在比谁更有耐心,我实在受不了,刚要说点什么,他却突然站起来,说,今天不早了,明天还有一天的会,你早点休息吧,会议散了之后,我请你去我家做客。说完,他伸过手来,我机械地握了他的手。我莫名其妙地有点失落,我郁闷地想,分别这么久,居然两人都没有说几句话!我想象的好象不应该是这样的。
送他下楼,走出大厅,他再次伸出手来,这次,他没有很快就松手,而是拉着我的手说,后天我来接你,你一定要等我,啊!握着我的手很用力,我脸一下子热了。他眼里尽是笑意,如水一样动荡着。
三十四
又过了一天,我们的会议也结束了。他来接我时,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我刻意地打扮了一下,我现在一直留着短发,因为发质好,头发总是象瀑布一样,李丽总羡慕我的头发说:也就一个最普通的短发,怎么就那么可爱地贴你头皮上,还会无风自动?平时我可没有心思去管什么头发可爱不可爱,今天我才有心情去仔细打量自己的头发。我穿了一件宝蓝色的呢绒长大衣,一条大红的羊毛围巾,在镜子里照照,嘿嘿,还有那么点风韵,我对自己说,不能让他把我衬得比他还老。话是这么说,潜意识里有没有怕被他老婆比下去的思想,说不清楚,自己拍自己一下,就算是对自己的惩罚吧。少陵看见我的时候,一下子呆了,也许他就没有想到我会这么重视去他的家,总不会是因为我美得让他吃惊吧,我心里有点得意。真漂亮,你今天,他一边开车一边说。是不是哦,老同学可不能恶搞比你弱势的人呢,我和他贫,我今天心情也出奇地好。
少陵开的是自己的车,什么车,我叫不出名字,现在是九十年代,有私家车的并不多,我坐在他车上就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直犯傻,我比那姥姥更惨,人家姥姥进了一个大园子才晕乎,而我,别人就一台车,就让我看傻了眼。
少陵的房子更让我傻眼。他的父亲是高干这我知道,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爸爸是省里的干部,在哪个省就不知道了,好象就是我们省吧,那时的人多纯洁,他不说,大家也不问,就象那约定俗成的规矩,换了现在,可能八个爸爸的事都抖落出来了。
进了小区的大门,我就看出这里住的可能都是有钱人,因为那房子太漂亮了,是我在以前绝对没有看见过的楼房,小区里面就象公园,到处都是花草喷泉,还有名人雕塑,我不禁想起我住的单人宿舍楼来,我们几个住那里的单身汉,把那栋楼叫“炮楼”,因为它又高又细。一条楼梯不转拐就直通到顶,每一步楼梯又高,所以爬上楼梯口时,任谁都会气喘如牛。我们常常自我安慰,科学表明,每上一步楼梯,就会多活七秒钟,我们的楼梯间距又高,肯定超过七秒钟。哈哈,我们不知比别人要多活好多年,到时候我们这栋楼里还不出几个老不死的妖怪,我们常常在一起互相取笑着。楼梯不远就是学校的猪栏和厕所,一阵风吹过,那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感觉,哈哈,很经典的。我悄悄想着,有点忍不住笑了。少陵看我一脸的喜色,说,这个小区是去年开盘的,在这个城市应该算是最好的。你觉得还行吧。
我都说了,我今天就一“刘姥姥”,你可别笑话我,等会和你家里的人见面时,有些什么不恰当的地方,你可得提醒我,我有点没有底气了,我今天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少陵见我这么说,没说话,我瞄他一眼,看见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进门,要掏钥匙,进去,没有人在家,我奇怪,回头看少陵,他正换鞋呢。见我问他,他说,急什么呀,坐下来说多少话。看他的样子,什么都运筹帷幄呢,我瞎用词,在心里。参观完他的房子,我更奇怪了,你家就————几个人在这住啊,我不好怎么“用词”了。就我一个人,他说。哦,我明白了,你刚调过来,老婆孩子还在以前的根据地,理解理解,我赶忙聪明地说。
我想起胡县长:老婆孩子又不是砖,哪能搬来搬去的?是的,你现在就是一块刚被搬到这里的砖哦,就住这么好的房子,啊,原来那个地方肯定比这里差。我自顾自地说着很冒失的话,少陵显然没有听明白我的话,瞪眼瞧着我,我一想,胡县长的说法少陵要么没听说,我将那几句话解释给少陵听,他笑了。说,你们县里的领导还真油,说话瓤子不多,壳倒不少。哈哈哈,我高兴地大笑起来,我觉得少陵的话倒是很“油”,回去正好在那帮不知死活的这长那长面前显摆一下,免得他们尽想着欺负我不会说“油”话。
在县里经常开了负责人会后就吃个“工作餐”,饭桌上,那帮在人群里“人模狗样”的家伙,一个个就剩下一张嘴了,又要吃,又要说,看谁会说,看谁的话有水平,这个水平,还真不是墨水的“水”,我觉得,那个水,就和那“下水”差不多,反正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当然,这话是绝对不敢明说 的,否则,那些家伙还不把你“隔离 ”死,轻者背着你说你“不懂水”,假正经,重者你找他办事效率低,弄得不好他克死你。财政局的余局长,是个最好饭桌上讲“段子”的主。最开始我还真抹不开脸面,记得有一次,饭桌上,余局长又开始了,先是一段老掉了牙的“长江黄河”颂,他是鄂西人士,只听他用鄂西土话开始了:长江啊,奶牙那么呢么长,黄或啊,奶牙那么呢么黄(长江啊您怎么这么长,黄河啊,您怎么这么黄)。然后,看见我在桌上,就开始讲“旺仔小馒头”我极力不让自己笑出来,我当时幼稚地想,我就不笑,我憋死你!没想到,恰恰错了,你越不笑,讲的人越觉得没有效果,他就越要讲,于是,他又开始讲“女人的两个优点和一个漏洞”。我受不了那种氛围,借故走了出去,没想到,这一走,余局长生气了,觉得我没有给他面子。那次,教育局长也在坐,恰好当时我们学校正在找财政局要盖教工宿舍楼的款子,教育局长发现事情不对头,赶紧找我商量,没办法,后来还专门请了余局长的客,虽然我没有“赔礼道歉”,但彼此都已经心照不宣,从此,我也明白了官场上的所谓的一些“潜规则”。
少陵见我这么高兴,问我,你是一直都这么高兴呢,还是看见我高兴。他真是个精明人,其实,我自己都感觉到我今天的高兴有点莫名其妙,或者说是自己极力培养出来的,我有什么好高兴的?
少陵亲自下厨房,我给他打下手,我发现,他这里一应俱全,什么都有,我又奇怪了,你不刚来吗,东西置办得这么齐啊。他说,要有个起码的生存条件吧。我说,你不是刚来吗,看你的样子,倒象在这里居家好久了。这次他没有笑,说,别问了,咱俩吃过饭,我什么都告诉你。
哎哎,别这么正式啊,我可胆儿小,经不起吓的,你什么悲惨旧世界可别给我描绘呀,我看着他正色的脸,好象有什么大事要说,我故意贫着,想冲淡一下气氛。
没有悲惨旧世界,只有共产主义新世界在向我招手,他也贫起来。
三十五
吃过饭,他不让我收碗,他自己一个人干着,我闲了没事,转到他的书房里,看见一本法国作家萨特的散文集正摊在书桌上。他进来了,看我在翻着那本书,问我,你看过他和波伏瓦的故事吗?没有,我说。萨特和波伏瓦可是长达几十年的感情,有人说他们是情人,又有人说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第三性”,你相信男女之间有所谓的“第三性”吗,少陵说。我感慨他比我强多了。我现在就典型的一管家婆,什么都在做,又什么都没做。我说,我不知道萨特和那个姓波的,我现在就是一个文盲加土莽,哪能象你,还能正经看点书。
他拉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下,他自己也坐下来,他没说话,然后头朝后仰去,靠在椅子的靠背上。他的脸上,胡须刮得很干净,青灰色的皮肤给人强烈的男人的性别特征,端正的鼻梁挺括修长,嘴唇线条极为分明,我在想,这张嘴唇如果长在一个女人的脸上,那这个女人要少好多事,每天就少了画唇线的工序了,我无聊地想着,自己也觉得有点想入非非了。我静静地等着他给我讲故事,刚才还英姿飒爽的他转眼怎么突然一脸的沉寂,看见他突然弥漫出来的落寞,我不禁有心痛的感觉,我明显感到,他有了很大的麻烦事。
少陵————我想打破局面,还没有说出来什么,他坐了起来,给我做了个手势,打断我的话,自己说了起来。
我离婚好几年了,你知道吗?他第一句话就这样开始了。啊,什么!我大声地没心没肺地嚷嚷起来,然后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