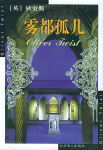花氏孤儿-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笑过之后,去罹道:“今日虽退了韩夜,但恐非长策,还要另想办法。”
初尘正色道:“这个我也想过,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去罹问。
初尘道:“金蝉脱壳,一石二鸟。”既能让韩夜彻底死心,也好让自己跟侯府撇清关系——她既已决心跟定倾之,就不得不早作打算,免得日后因己之故,连累父母兄长和整个渤瀛侯府。
“有这样的好办法?”去罹眼眸一亮,“怎么讲?”
初尘便将自己的计划如此这般一说,去罹听完,道:“好是好,只是侯爷跟夫人……”摇摇头,“恐怕不肯答应。”
初尘咬了咬嘴唇,“我去说服他们。”
是夜。初尘让小花儿请傲参殷绾屏退众人,在厅中等候,傲参夫妇虽不知女儿又要耍什么鬼花样,但闲来无事,倒也乐得陪她。
夜色浓照,烛光微烘。如火花钿,如雪白衣,她就那样一直微笑着,缓缓的从夜幕中走来,穿过交织的烛光。跪拜,起身,微笑。
“父亲,母亲,女儿有喜欢的人了,女儿想嫁给他。”
……
生疑
【章九】生疑
《渤瀛方志》:渤瀛侯有女初尘,姣美聪慧,甚得喜爱。惜哉,泽深不寿,妙龄早夭。参立爱女像于龙帝祠帝像之侧。明眸少女,手奉箜篌,霞披云裳,丽荣娟娟,世人神之……
瘦红居。一场秋雨过后,水澄天青,涨了几指的湖水正没过木板的边缘,人在其上,仿若凌波。雪白的衣裙如清明的秋风拂过墨色残荷,三两尾红色游鱼好似尚未凋落的红荷在湖中的倒影——黑白水墨之间笔锋一抹,平添了些许灵动活泼。初尘正拿了一根蒲草,蜻蜓点水似的轻敲湖面,闲斗鱼儿。
人入景,景如人,宜静宜动。
去罹记得他们兄弟初来渤瀛时在此山中寻马,一晚倾之浑身湿透的回家,手里正是攥着一捧舍不得人碰的蒲草,想必那时他们便是见过的吧……
去罹兀自感慨,不知何时初尘已提着裙角蹦跳到他面前,摇着蒲草在他眼前晃了晃。去罹下意识向后一躲,才怃然发现自己方才想事情想得出了神。
定睛一看,初尘正笑眯眯盯着他,去罹不由打了个寒噤。
“去罹哥哥,”初尘进,“你想行已大哥和倾之吗?”
“想,想啊。”去罹退。
“那你想不想回凤都找他们?”初尘再进。
犹豫——这妮子打什么主意呢?“当然……想。”去罹再退。
“那我们一起去凤都如何?”初尘三进。
去罹站定,瞪眼,不容反口,“想都别想!”
初尘仰头望了望直直地站在她面前,一堵墙似的去罹——他头顶上毫无杂质的深秋之天射下的阳光无有遮拦的耀眼——初尘眉一蹙,嘴一嘟,耍性儿地从地上抓起一把碎石,“咚咚咚咚”丢进湖里,吓得鱼儿四散,青蛙乱蹦,“咕呱咕呱”,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去罹不动声色的悄悄后退,暗中叹气:他能体会初尘的心思,只是若他将她带去前线,就等着倾之与他“兄弟反目”,“拔剑相向”吧。比心机、比功夫,去罹自认不是三弟的对手,他好不容易从战场上捡了条命回来,还不想“英年早逝”。再说,那所谓的“千里寻夫”、“千古美谈”不过都是话本罢了,还能当了真?
初尘宣泄够了,便双臂抱膝坐在地上,没精打采地把头搁在膝上,望着犹自涟漪荡漾的湖面平静了下来:那夜她对父母坦言自己喜欢倾之,为了跟他在一起,也为了不累及家人,从此世上再无傲初尘!
父亲缄默,一言不发,母亲的反应却出乎意料的平静,她只问她一句——花倾之如今人在凤都,生死未卜,如果他回不来怎么办?叹了口气,沉默片刻,一向温顺的母亲提了一个强硬的条件:若不幸花倾之死在凤都,今后她的终身大事须得全凭父母做主,由不得她说半个“不”字。
初尘答应了——以自己的妥协换得父母的妥协。可万一……,她懊恼地抓着头发,心里埋怨,却又万万不敢骂一个“死”字,着实恼人。
小花儿知道初尘近来心情烦闷,喜怒不定,早识趣地躲了老远。去罹昨日钓了两条尺长鲤鱼养在缸里,说是今天炖了喝汤,她便提刀来宰。
左看右看不知从何下手,反是两条“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大鱼悠然自得,甚至神态轻蔑,时不时掀一下尾巴,拍得水面“啪啪”作响,气焰嚣张。小花儿不服,扔了菜刀,高高捋起袖子,伸了手去捞。
渤瀛侯夫妇与公子天俊到时正瞧见小花儿一只脚踮着,一条腿翘着,腰际贴着缸沿儿,半个身子斜探在水缸上方,伸了双手在水里左一下右一下的摸,摇摇晃晃,险险整个人要跌进缸里。
傲参看了直是好笑,殷绾又好笑又紧张。忽的小花儿身子一坠,就要头朝下脚朝上栽进缸里,天俊疾走两步,揪着后领把她从水里拎出来。
只见小花儿双臂前举,手里正握着条噗噗打挺的大鱼,吓得她眼不敢睁。鲤鱼左扭右摆,“哧溜”从小花儿手中滑脱,“通”一声落进水缸,砸出好大水花儿,溅了小花儿满头满脸,甚是狼狈。
天俊将小花儿稳稳妥妥地放在地上,殷绾赶紧上前拿了帕子给她擦脸,小花儿看看殷绾和她身后的傲参,又回头瞧瞧天俊,才知道方才的窘态全被三人看了去,可她却毫不介意,弯起眉眼笑道:“侯爷、夫人、公子,你们来啦!我去告诉小姐。”说着挣开殷绾,飞跑去湖边找初尘。天俊笑笑,也跟了过去。
自从初尘假死,搬出侯府至瘦红居,父母兄长虽不能日日相聚,但阳春踏青,盛夏避暑,清秋郊游,冬日狩猎,身体力行,体察民情,渤瀛侯不乏出外的理由,近日更兼侯爷夫妇新失爱女,渤瀛侯夫妻恩爱,侯爷三五不时携夫人出来散心也是人之常情,非但不会惹人疑心,更于街头巷尾,传为恩爱佳话。
傲参边等,边给殷绾指点风景。
“看,这边山上都是海棠,待到春日,漫山遍野云蒸霞蔚,煞是好看。”
殷绾笑道:“难怪尘尘喜欢海棠,原就是在海棠中生的。”
……
初尘心急,跑在最前,赶到之时正听见父母谈话,便停了脚步,并示意随后而来的天俊、去罹和小花儿不要做声。三人看向背对他们的傲参殷绾,前者细揽妻子于怀,指点秋色,后者轻轻倚靠,低语轻笑,老夫老妻亲密得羡煞旁人。
三人见状偷笑,却不知初尘的心思:城南林中的瘦红居她跟小花儿三年前就发现了,那时满屋尘垢蛛网,久无人住,更不知主人是谁,她们见屋外海棠成林,湖光山色,便将屋子打扫出来,做玩耍休憩之用。不料这次父亲安排她们的地方竟是此处,即是说,这屋子先前的主人是她的父亲,渤瀛侯傲参。
这也无妨,初尘猜想此处大概是父母亲年轻时幽会之所——不论是妆台明镜,绣架箜篌,还是瑰色罗帐,金粉被褥,都是女子所喜所用。
可若是父母年轻时相会的地方,父亲怎么会给母亲指点山上的风景?更可疑的是母亲那句“难怪尘尘喜欢海棠,原就是在海棠中生的”——她是在哪里生的,难道母亲还不清楚?况且她从来“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出生在渤瀛侯府!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初尘心里忽冒出些有的没的的念头吓坏了自己:难道她一直以为对母亲专情不渝的父亲在外面另有所欢?甚至她并非母亲亲生?
天俊见初尘脸色不好,关切道:“小妹,怎么了?”
“没……没有。”初尘不敢将这荒唐无据的想法说给哥哥。
“初尘?”
“尘尘?”
傲参、殷绾听见天俊、初尘的声音,双双回了身。
“娘。”初尘一头扑进殷绾怀里,心慌得厉害,害怕失去,便抓得更紧。
分别几日,殷绾倒觉得女儿更粘人了,心中欢喜。她怀抱着初尘,揉着她的头发,含笑轻责道:“你呀,来了也不出声。”
初尘不语,只是埋头在殷绾怀中。
“侯爷,最近可有凤都的消息?”去罹上前问道。
殷绾怀中的初尘也抬起头来,眼睛一眨不眨地望向傲参。
凤都的消息当然有,只是……
“暂时还没有。”傲参隐下实情。
初尘闻言有些失望,却又窃喜——至少听到的不是坏消息。
“不过……”
“什么?”众人才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我近日占卜,倒恐朝中有变。”傲参叹道,“左都在外征战,不寄望韩嚭能襄助一臂之力,但不在背后毁谤中伤,已是幸甚。”
初尘思索:朝中勾心斗角非她在意,只是倾之人在左都军中,唯恐不妙……
大军越过凤脊山后不知所踪,留守山北的先锋左骥前前后后派去十几路人马入山接应,却都是有去无回。心知大军恐遭不测之险,左骥安顿了军中事务,带三五亲随,露宿风餐,马不停蹄赶回钰京求援。
掠影浮光,千山飞度。
人到城下之时正是深夜,城门紧闭,守城将军验明身份,知有紧急军务,才肯放行。甫一入城,左骥轻轻勒住坐骑——钰京城,似乎有异。
“左先锋,天色已晚,现在入宫怕不合适吧?”随从问。
左骥拧眉,扬鞭道:“去找我叔父!”打马先行。
青石板路,马蹄渐远,空寂的长街只留下几串急促的碎响,似将整座城池都踩在了脚下——那不同寻常的,是安静!
统领府的护卫见了左骥大吃一惊,忙将他引入府内,恰好左护当日休息,自家叔侄相见,又兼事情紧急,便省去了许多客套,左骥道明来意,最后问道:“叔父,朝中近日出了什么大事?为何数封紧急军报至今都没有答复?”
左护紧握着左骥的手,生怕一个松手,连眼前这个小侄儿也会陷入险地。大哥、侄儿遇险,他能不心急如焚?可现在……
“叔父,怎么办?”左骥早已没了主意。
左护咬咬牙,也不顾了那许多了,拉着左骥就走,“随我面见陛下去!”
两人骑马至宫门外,果不其然被人拦了下来。左护扔了令牌过去,喝道:“不认识我左护,也不认识禁军统领的令牌吗?还不速速放行!”
军士抱拳道:“今日并非大人当值,大人有事,还请明日再来。”
“我有紧急军务,刻不容缓!骥儿,走!”左护扬鞭,欲要硬闯。
门内一人骑马而来,鞭梢轻扬,正与左护的鞭子绞在一起。来人笑道:“左统领。”手上却紧拽着鞭子,暗暗与左护较劲儿。
左护见是韩嚭,既惊且怒:惊的是他们叔侄刚至宫门,韩嚭竟然就得到了消息,可见宫中遍布了韩家的势力;怒的是,左护知道,韩嚭不安好心!
“啪”,鞭子挣开。
左护压下心中怒火,客气道:“韩将军,在下有事求见陛下,还望将军通融。”
左骥在一旁暗道奇怪:他离开钰京不足半年,宫中发生了什么大事以至于一向由风云两翼戍卫的王宫改由天执右将军总管?
韩嚭微微一笑,“并非韩某不通融,只是陛下早有旨意,谁也不见。”
想到陛下近日无心朝政,左骥提到的紧急军报定也是被韩嚭压下,左护更怒,语气也冲了起来,“韩将军,凤都战事吃紧,左护必须要见陛下!”
左护作势要闯,韩嚭一挥手,数百手持兵刃的军士从暗处涌出。
韩嚭眼眉微瞟,看向神情惊愕的左护叔侄,勾起唇角,慢悠悠道:“左统领,太子病危你该是知道的,难道还要拿这芝麻绿豆的小事去打扰陛下?左统领可不要明知故犯,逆龙之鳞。”
太子病危?左骥吃了一惊:太子才只有六岁,怎么会……然而即令太子有恙——他双手紧攥缰绳,以至肩膀都跟着轻轻颤抖:这韩嚭,分明刁难!
小事?左护剑眉倒竖,“韩将军将十几万人的性命视作小事吗?延误了军机,将军可担待得起?”
韩嚭不以为然,哂道:“莫说是十万人,就是百万人也比不得太子一条命金贵。”摆明了不会放行。
左护大怒,“韩嚭,你这是挟嫌报复!”
便是挟嫌报复,你左护能耐我何?韩嚭冷笑,“请左统领、左先锋回府!”
“你……”左护欲动,明晃晃的刀枪已到眼前,而韩嚭则在众军士掩护之下拨转马头,慢慢行远。左骥心焦,可见叔父被阻,他也不敢鲁莽行事。
思及十年来左家失宠,韩家得势,且不说他的大哥、侄儿在凤都浴血奋战、生死未卜,而韩嚭养尊处优、清闲安逸,单说从玄都到钰京,他贴身侍奉陛下十数年,如今想见陛下一面却难比登天,怎不叫左护悲愤难平?
心中郁愤,唯有仰天长啸,清泪满面,“陛下!陛下!”可纵然他喊裂肝胆,宫门重重,商晟也听不到一字。
“父亲。”
韩嚭下了马,扔了马鞭,听见一声“父亲”转过头来,才发现给他牵马的不是别人,正是儿子韩夜。韩嚭不悦,“怎么是你?”
韩夜不答反问,“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