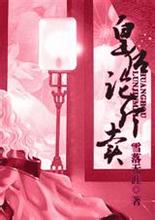战争论-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鳎以诟男辞傲币惨⒒幼饔谩6郧傲髡庋男薷模崽蕹橹械囊恍┰惆兀植挂恍┞┒矗铱梢园岩话悖缘亩鞴槟沙杀冉厦魅返乃枷牒托问健�
第七篇《进攻》( 各章的草稿已经写好〉应该看作是第六篇的对照和补充,并且应该根据上述更明确的观点立即进行修改。这样,这一篇在以后就可以不必再修改了,甚至可以作为改写前六篇的标准。 第八篇《战争计划》( 即对组织整个战争的总的论述〉的许多章节已经草拟出来了。严但这些章节甚至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素材,而仅仅是对大量材料进行了粗略的加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工作中明确重点之所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我想在完成第七篇以后,立即动手修改第八篇,修改中主要是贯彻上述两个观点,并且简化一切材料,但同时也要使它们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我希望,这一篇能够澄清某些战略家和政治家头脑中的模糊观念,而且至少要向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何在,以及在一次战争中到底应该考虑什么问题。
如果在修改第八篇的过程中能使我的思想更加明确,能恰当地确定战争的重大特征,那么以后我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这种精神带到前六篇中去,让战争的这些特征在那里也到处闪闪发光。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着手改写前六篇。
假使我过早去世,因而中断了这项工作,那么现有的一切东西当然只能叫做一堆不象样子的思想材料了。它们将会不断地遭到误解和任意的批评。在这些问题上;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提笔想到的东西都是很完美的;已经可以写下来发表了,并且认为它们就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们也象我一样花费这么多精力,长年累月地思考这些问题,并且经常把它们同战史进行对比,那么他们在进行批评时,当然就会比较慎重了。
尽管这部著作没有完成,我仍然相信,一个没有偏见、渴望真理和追求信念的读者,在读前六篇时也不会看不见那些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对战争的热心研究所获得的果实的,而且或许还会在书中发现一些可能在战争理论中引起一场革命的主要思想。
1827年7 月10日于柏林除了上面的《说明》以外,在作者的遗稿中还有下面一篇未完成的文章,这篇文章看来是他在晚年写的
在我死后人们将会发现的这些论述大规模战争的手稿,像目前这个样子,只能看作是对那些用以建立大规模战争的理论的材料的搜集。其中大部分我是不满意的。而且第六篇还只能看作是一种尝试,我准备对这篇进行彻底改写并另找论述的方法。
但是在这些材料中一再强调的主要问题,我认为对考察战争来说是正确的。这些问题是我经常面对实际生活,回忆自己从经验中和同一些优秀军人的交往中得到的教益而进行多方面思考的结果。
第七篇是谈进攻,其中谈到的问题只是仓卒地写下来的。第八篇谈战争计划,我打算在这篇中特别阐述一下战争的政治方面和有关人的方面。
我认为第一篇第一章是全书唯一已经完成的一章。这一章至少可以指出我在全书到处都要遵循的方向。
研究大规模战争的理论〈或称战略〉是有特殊的困难的。可以说,只有很少数的人对其中的各种问题有清楚的观念,即了解其中各种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在行动中大多数人是单单以迅速的判断为根据的,而判断有的很正确,有的就不那么正确,这是因为人们的才能有高低之分。
所有伟大的统帅就是这样行动的,他们的伟大和天才,一部分也就表现为他们的判断总是正确的。因此,在行动中人们将永远依靠判断,而且单靠判断也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不是亲自行动,而是在讨论中说服别人,那就必须有明确的观念并指出事物的内在联系由于人们还很缺乏这方面的素养,所以大部分的讨论只是一些没有根据的争执,结果不是每个人都各持己见,就是为了顾全对方而和解,走上毫无价值的折衷的道路。
在这些问题上有明确的观念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而且人的思想一般说来都倾向于要求明确性和要求找到事物的必然联系。
为军事艺术建立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在这方面所作的许多糟糕的尝试,使大多数人得出结论说,建立这样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研究的是固定的法则不能加以概括的东西。如果不是有很多毫无困难就可以弄清楚的原则的话,我们或许会同意这种看法,并放弃建立理论的任何尝试。这些原则是: 防御带有消极目的,但却是强而有力的作战形式,进攻带有积极目的,但却是比较弱的作战形式,大的胜利同时决定着小的胜利;因此战略的效果可以归结到某些重心上;佯动是比真正的进攻较弱的一种兵力运用,因此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采用; 胜利不仅是指占领地区,而且也指破坏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会战胜利后的追击中才能实现,经过战斗取得的胜利的效果总是最大的,因此从一个战线和方向突然转移到另一个战线和方向,只能看作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只有在具有全面优势或者在交通线和退却线方面比敌人占优势时才能考虑迂回;同样,只有在上述情况下才能占领侧面阵地;进攻力量在前进过程中将逐渐削弱。
作者自序
所谓科学的东西不仅仅是指或者不主要是指体系和完整的理论大厦,这在今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了。在本书的叙述中,从表面上看,是根本找不到体系的,这里没有完整的理论大厦;只有建筑大厦的材料。
本书的科学性就在于要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它们同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之间的联系。作者在本书中没有回避哲学的结论,但是当它们不足以说明问题时,作者就宁愿放弃它们,而采用经验中恰当的现象来说明问题。这正象某些植物一样;只有当它们的枝干长得不太高时;才能结出果实。因此在实际生活的园地里,也不能让理论的校叶和花朵长得太高,而要使它们接近经验,即接近它们固有的土壤。
要想根据麦粒的化学成分去研究麦穗的形状,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要想知道麦穗的形状,只要到田野里去看一看就行了。研究和观察,哲学和经验既不应该彼此轻视,更不应该相互排斥,它们是相得益彰和互为保证的。因此,本书里具有内在必然性的一些原则,或者建建筑在经验的基础上,或者是建筑在战争概念本身的基础上,就象拱形屋顶建筑在支柱上一样。因此可以说,这些原则是不缺乏根据的。
写一部有思想有内容和有系统的战争理论也许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有的理论还与此有很大的距离。我们暂且不说这些理论缺乏科学精神这? 点,仅仅由于它们极力追求体系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在它们的论述中就已经充满了各种陈词滥调和空话。如果有人想看一看它们的真实面目,就请读一读李希滕贝格从一篇防火规程中摘出的一段话吧。
如果一幢房子着了火,那么人们必然首先会想到去防护位于左边的房子的右墙和位于右边的房子的左墙,、因为,如果人们,比如说,想要防护位于左边的房子的左墙,那么这幢房子的右墙位于左墙的右边,因而火也在这面墙和右墙的右边( 因为我们已经假定,房子位于火的左边〉,所以,这幢房子的右墙比左墙离火更近;而且在火烧到受到防护的左墙以前如果不对右墙加以防护;那么这幢房子。 的右墙就可能烧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未加防护的东西就可能烧毁,而且可能在其他未加防护的东西被烧毁以前先烧毁。所以,人们必须放弃后者,而防护前者。为了使人们对事情有深刻的印象,必须指出: 如果房子位于火的右边,那么就防护左墙;如果房子位于火的左边;那么就防护右墙。
为了避免用这样罗苏的语言吓跑有头脑的读者,为了避免在少数好东西里掺入清水,冲淡它的美味,作者宁可把自己对战争问题经过多年思考而获得的东西,把自己同许多了解战争的天才人物的交往中和从自己的许多经验中获得的和明确了的东西,铸成纯金属的小颗粒献给读者。这本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在本书中;章节之间的外部联系不够紧密;不过,但愿它们并不缺乏内在联系。也许不久会出现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给我们的不再是这些分散的颗粒,而是一整块没有杂质的纯金属铸块。
第一篇 论战争的性质
第一章 什么是战争
一 引言我们想首先研究战争的各个要素,其次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也就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但是研究这个问题时,比研究其他问题更有必要先对整体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部分时更必须经常考虑到整体。
二 定义在这里,我们不打算一开始就给战争下一个冗长的政论式的定义,只打算谈谈战争的要素一一搏斗。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荒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二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F 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
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暴力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装备自己来对付暴力。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在实质上并不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即物质暴力( 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 是手段;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为了确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因此从概念上讲;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真正的目标。这个目标代替了上述目的并把官作为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而在某种程度上排斥掉了。
三 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物质暴力的充分使用决不排斥智慧同时发挥作用,所以,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这种趋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
问题必须这样来看。由于厌恶这个残暴的要素而忽视它的性质,这是没有益处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那么,这也是交战国本身的社会状态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虽然战争是在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是由它们决定、限制和缓和的,但是它们并不是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它们在战争发生以前就已存在,因此,如果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敌对感情和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我们所以选择敌对意图这个要素作为我们的定义的标志,只是由于它带有普遍性,因为,甚至最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没有敌对意图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在野蛮民族中,来自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而在文明民族中,出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但这种差别并不是野蛮和文明本身决定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状态、制度等决定的。所以,并不是每个场合都必然有这种差别,而只是大多数场合有这种差别。总之,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可能燃起强烈的仇恨感。
由此可见,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的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
理论已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最近几次战争纠正了它。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
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