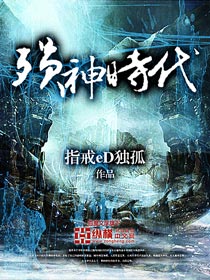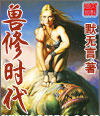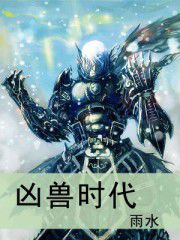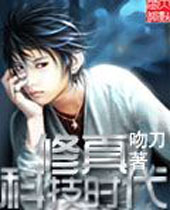文艺时代-第4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六百二十三章华语新势力(2)
北京,艺术中心。
这里是三楼最大的一个会厅,摆着一百多张椅子,前方是高台,十张小沙发形成一个半弧。论坛九点钟开始,现在是八点十分,褚青正在场中来回检查,看看有无纰漏。
不多时,外面进来一位身材略胖的中年女人,他连忙凑过去,笑道:“大姐,今天得麻烦你了。”
“哈,你讲得那么言辞切切,我拒绝都会有负罪感诶。”
来人正是焦雄屏大姐头,个子不高,气场十足,将兼任活动主持。她与褚青相识在2001年的金马奖,此后每年都会在各大影展中碰到,一来二去便成了忘年交。此番前来,主要是推介魏德圣、钮承泽这两位新导演,顺便为朋友站台。
魏德圣的年纪挺大了,出道很早,一直没机会上位,《海角七号》是他的第一部长片。钮承泽却是演员出身,还有不小的知名度,也同期拍摄了处女作《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
又过了片刻,郭子健、黄真真、黄修平三位香港帮到场,宁浩、张猛、滕华涛、曹保平四位内地帮也陆续现身。
时间临近,褚青便示意员工,准备让观众入场。二十块一张票,算是茶水钱,在半个小时内就被抢光,多是艺校学生、新人编导和业余爱好者,另有媒体席位。
纯娱乐的传媒不会报道这种事,都是综合性报刊,大概有四五家。
随着观众就坐,嘉宾也齐齐上台,褚青到台下第一排,屁股刚沾上椅子,立马又起身,讶然道:“小宝哥,你怎么过来了?”
“刚好在北京剪片,就来捧捧场喽!”尔冬升拍了拍他肩膀,一贯含蓄的表示力挺。
紧跟着,王小帅、陆川、方励、李玉、管虎、黄渤、徐峥、俞飞鸿、徐克依次亮相。褚青又惊又喜,连忙让人加位子,整个会场塞得满满当当。
“哇哦!”
底下更是一阵骚动,没承想能看到这么多的腕儿。而那些不请自来的家伙,反倒令台上的一票菜鸟很紧张,焦大姐见状,便敲了敲话筒,直接开始:
“鄙人焦雄屏,担任本次活动的主持。今天很荣幸跟大家共聚在这样一个场合,没有炫目的灯光,华丽的红毯,疯狂的影迷,只有这九位出色的电影创作者和在座的各位行家。当然我也蛮意外的,徐导演、小帅、李玉这些优秀的电影人能自发前来,我为这种态度而尊敬,这也是前辈对后辈应有的一份支持。”
“哗哗哗!”
掌声过后,她继续道:“不过老实讲,我从没参加过这么寒酸的交流会,连个主题名字都没有。褚先生对我讲的是,随便你们怎么样,只要有互动就好。这句话我蛮赞同的,思辨的空间最重要,结论不重要,因为每人有每人的答案。那好了,既然随便我们,我就先抛砖引玉……”
说着,她转向旁边,道:“宁浩导演,当年在戛纳看了你的《香火》,开心得不得了,直接跑过去找你。后来又看了《绿草地》,也是一样的出色,但后来又看了《疯狂的石头》,我发现你变化蛮大的。以前都是现实主义的社会关系,镜头很平稳,不花哨。不过从石头开始,你好像加入了很多商业思考,电影语言非常有颠覆性,那种很年轻的视觉风格。”
“呃……”
宁浩拿过话筒,组织了下语言,道:“我觉得,与其说是我的变化,倒不说是环境的变化。《香火》那个时代,我对世界的印象就是山西的小县城,很旧很慢的那些东西。但到了石头,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到,物质成了生活中的第一要素。石头的剧本很早就有,后来又不断加工,里面每个人的目标都很明确,就是围绕一个东西,围绕钱来展开。呃,它有一些我对自己,对身边人的某种思考。”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将来环境再变化,你的风格可能跟着变。”曹保平开了句玩笑。
“就是当物质饱和的时候,又去思考其他事情,诶,我要这么多钱有用吗?我要不要追求一点别的东西。”钮承泽接道。
“对对,指不定我哪天就拍一部中年危机,渴望真爱什么的。”宁浩也笑道。
焦雄屏特自然的转移对象,道:“那曹导演,您是剧作家出身,您觉得石头的剧本还合口味吗?”
曹保平摸了摸半秃的头发,道:“每天吃糠咽菜,忽然来这么一道拼盘,当然合口味。”
“就是说,大多数的电影你都难以下咽?”
焦大姐挖坑的技巧一流,但曹教授也不是好惹的,直接开喷:“我看了很多上映的片子,那叫个烂啊,连基本的章法都算不上。叙事完整,营造可信度,这是标准,但放眼全世界,几乎没有像中国这样不重视剧本的。就韩国特别火的那部电视剧《豪杰春香》,我都很认真地看了一遍。你可以说它庸俗,但人家有基本章法,有清晰的人物设定,完全在承受范围之内。”
“嗡嗡嗡!”
话落,下面又是一片窃语,不少人觉得太过了。
而听了半天的郭子健,似乎有所触动,他跟褚青同岁,编剧出身,已经拍了两部电影。他的国语不太好,讲得很慢:“我拍过两部片,不太喜欢被人叫黑帮片,或者古惑仔电影。在大的范围内,我觉得应该叫剧情片。所有的电影都是叙事的,我们希望它真实,但如果是非常强烈的冲突,大家又会怀疑它的真实性。那我想请问您,这个矛盾怎样平衡?”
哟!
曹保平一歪头,觉得这个后辈很不错,便道:“我们要在假定的叙事范畴里,模拟出一种极度的真实,但巧合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怎么那块石头刚好砸他头上?怎么他俩就刚好错过了?怎么他就出车祸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我的方法是借用演员的力量,让他们达到一种极其自然的状态,可以保持一定的平衡……对,就是这个!”
他扭头看去,后面的大屏幕已经亮起,定格在一张周迅的剧照上。
“这是我的新片《李米的猜想》,周迅就用她的力量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们看这张照片,一般特写用得越多,信息量越少,但当我的镜头集中在她脸上,她给我的东西简直令人惊叹。那种焦灼的,绝望的,从内心挖出来的,比氛围渲染要更震撼。所以我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好演员能让观众相信,即便有巧合,这个故事也是真的。”
接着,曹教授看着对方,总结道:“没有什么比演员更重要,这是我的观点。”
“……”
郭子健点点头,若有所思。焦雄屏则补充道:“我昨天看了初剪版,不得不说,周迅的脸太有魅力了,我觉得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大家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
嗯?
褚青正听得过瘾,忽觉得气氛不对,四处瞧瞧,不禁冒出三条黑线:人家提周迅,你们都瞅我干锤子?
……
“每个人都在讲,香港已是电影空城,我却觉得这是新导演最好的时代。前辈们集体北上,新人才有机会留守本土,尽情发挥。港片曾经的辉煌,也留下了很丰厚的财富。我们都年轻,更清楚年轻人的习惯,将不同类型的影片加以改良、创新,如果能良性循环下去,我觉得香港电影是有救的。我们缺乏经验和商业运作条件,但我们也很幸运,有一众前辈为我们保驾护航。”
黄修平都有些哽咽,道:“像志伟哥、小宝哥、华哥、南生姐……他们帮我们找演员,做监制,做发行,这个情分不光是前后辈,或者教徒弟,我相信这是一个信念,港片不死!”
说到这儿,尔冬升忍不住起身,要过话筒,道:“我当导演的时候才29岁,我当时的目标是把前面的老导演都干掉。如今香港有过长片作品的新人,一共不到10个,我希望他们能迅速成长起来,欢迎他们取代我。”
接着,徐克也道:“老港片是有传承的,比如警匪片,这是香港人最擅长的嘛!你们先从这类电影入手,因为你们的思维比我们活跃,只要能拍出新意,那就OK。至于别的方面,交给我们!”
“……”
全场都在沉默,没人觉得刻意或煽情,只是看到了一个缠绕无数情怀的东西,在时代的褶皱中奋力挣扎。
之后,魏德圣和钮承泽也聊了聊台湾电影的现状,以及对复苏的期望。可惜国内接触不多,Get不到那份情愫。
这场交流会从九点开始,十一点就该结束的,结果一拖再拖,耗到了一点钟才散场。先是台上的十个人聊,后来台下也加入,从剧本创作,到拍摄技巧,再到市场判断,三地电影的渊源风格等等。
总之,没说够,更没听够。
尤其俞飞鸿这种刚刚起步,徐峥这种抱有心思的菜鸟,绝对受益良多。俞飞鸿甚至翻出一个本子,不时做笔记。而她印象最深的,是曹保平的两段话:
“现在这个从业环境,商业元素越来越强烈,不会再当成一个很神圣的事情来做,所以导演营造的氛围很重要,你能给演员什么东西,让他们对电影,对这份职业,怀有敬畏和尊重。
当演员对戏的理解,和你自己的理解有差别时,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沟通、解决,凭什么让对方信服你,这是导演最大的难题。”
第六百二十四章第二场
“第五代刚出来的时候,完全是反戏剧、反故事,追求一种形式感和视觉化。因为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比较人文,全民都在思考,你够偏够怪才有市场,就是大陆的所谓文化精英的市场,人家会高看你一眼。比如《红高粱》拿金熊的时候,张艺谋简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肩负国家兴衰的那种感觉。”
台上,张献民侃侃而谈,接着道:“而且西方社会爱看这些东西,我们有十多年的文化断层,就没在国际上露过面,他们觉得中国特神秘。第五代的片子不是反应当时的中国,可由于这种窥探癖,反倒成就了那些荣誉。然后到了九十年代末,第六代冒头,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也发生转变,他们想看一些相对真实的东西。所以第六代早期那些表现边缘群体,城乡变迁带来的种种困惑,在海外有大量的市场……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内艺术电影的变化与海外市场的变化,从来都是相辅相成,是互相的一个作用。”
在他左右,还坐着几位嘉宾,分别是葛文、市川尚三、杜特龙、阿尔伯特和程颖。台下,仍然是曹保平、焦雄屏等人,还多了几家影视公司的高管。
昨天是交流一些新人导演的生存状态,今天更高端一点,针对国内电影在海外发行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而张献民说完,葛文消化着翻译机里的内容,点头道:“我同意张先生的看法。94年,王小帅带着《冬春的日子》来到鹿特丹,那里面的技法和思考让我们全场惊艳。但如果五年后,另一个导演带着类似的作品来鹿特丹,哪怕他拍得更好,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拒之门外。因为你没有创新和进步,电影三年就会更替一批观众和审美口味。作为导演还在走前人的老路,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看过很多中国独立电影,无论新导演还是比较成熟的导演,他们通常会犯一些相同的毛病。比如,喜欢将纪录片和剧情片结合在一起,中国做得最好的就是《三峡好人》,但它已经是巅峰了,后来者竟然没想着做些改变。甚至当西方观众已经看腻的时候,那些新人导演还在做这种尝试。
另外,我觉得中国独立电影都非常的慢。有八成的人都会采用长镜头,以表现所谓的残酷生活。可能这几句话不太好,但我确实认为那些片子的质量很低,声音差,字幕也基本看不懂。而且中国电影的类型非常单一,题材很匮乏,它们缺少让观众产生兴趣的能力,更达不到与现实合理的联系。”
老外说话就是直啊,这顿喷下来,大家的脸色都不太好。
紧跟着,戛纳的前选片人阿尔伯特道:“葛文先生讲的我深表赞同,不过我想接着张先生的话题。他刚才说电影与市场的共生性,这个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中国电影在海外的探索与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红高粱》到《霸王别姬》,第二阶段从《冬春的日子》到《三峡好人》。这其中的共存关系,张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我想说的是第三阶段,就是从现在到后十年。其实不仅是中国电影,全世界的影视产业除了好莱坞的特效片,都在面临着一种回归——讲故事的回归。”
他顿了顿,继续道:“现在的观众需要看一个好故事,这是我们自幼就有的本能。你可以拍那些冷门的题材,运用古怪的技巧,但它们只能在电影节上做几天的宠儿,马上又会打回原形。而我恰恰认为,中国大部分的导演很缺乏讲故事的能力。现在已经是第三个阶段,你还在用第二个甚至第一个阶段的手法去创作,市场当然不接受。”
话音方落,程颖便拽过麦克风,接口道:“我一直跟着公司跑海外,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