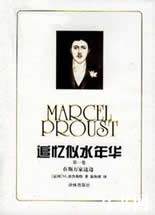橙色年华-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使劲地喘了一口气,眼睛也紧紧地盯着我。
我大声地喊着:“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够朋友吗?”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了,我的眼睛里面一下子充满了泪水,就像瀑布一样倾泻出来,我的头瞬时剧烈地疼痛!我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膊说:“你怎么,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一点你与周可冰的事情?你为什么……”
我开始笑了起来,迷茫地像一个在暴风雨之中的小孩,脸上已经满是泪水了。
滴滴滴——
我的手机响了,宁静的空气一下子仿佛冷了,冷得我难受。其实不知道已经有多少次听到过铃声之后打颤了,但是现在是颤抖得厉害。
林欣!
我仰起头长叹了一口气,用手胡乱地抹了一把泪水,接通了电话。
没有声音!
“林欣……”我几乎要哆嗦了!
她终于讲话了,声音脆弱得很:“痞子,我现在就要走了,我已经在离云彩最近的地方了。”
电话已经挂断了,里面是嘟嘟的声音。我马上就回拨,里面终于说:“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离云彩最近的地方!
离云彩最近的地方!
我嘴里默默地念了两边,啊!林欣!
我一下子放开了叶子往酒吧外面冲出去,将服务生的盘子都撞翻了,我跳到公路上面看见了一辆红色的富康的士就伸手拦了下来。
司机说:“朋友,上面有人了……”
我“啊”地大吼一声,一把将里面的胖子乘客拉了下来,然后对司机大喊:“快,快去中山大厦,我急着救人命!”
我的声音几乎没有人声了,嘶哑得像灰黄色的沙子。我的灵魂可以感觉到我们的车子穿越了生与死的极限在武胜路上狂奔着,窗外的大小公汽从我的脸旁呼呼地飞过,我看见了自己在暗灰色玻璃窗里的影子,憔悴得可以看见一个少年的最后的悲哀,我想,我要飞了,我要崩溃了。
我的脑子里面是林欣的影子,伴随着“捷克”的游动在记忆的大海里漂浮,是血一样的味道与骨头一样的苍白,看见海面上起风了,幻想却没有一个避风的港湾,依旧是孤独的自己在海上流浪。
我看见了远处的简陋的竹排漂过来,却怎么也抓不住了,只是看见上面插着的郁金香的影子在已经模糊的眼睛里徘徊。
在凶狠的幻觉里,我也看见了刀,上面已经滴了血液,但是我不知道是谁的,惨淡得很,像我的血管里面的液体一样的颜色。我于是就开始吼叫,发疯似地吼叫,我的声音瞬时间被幻像吞噬了,孤寂的没有一丝生命的信息。你可记得,在你们初见时,
唉!那初次的致命的会见,——
她的迷人的眼神,她的话语,
和那少女的微笑是多么甜?但现在呢?一切哪里去了?
这好梦究竟有多少时辰?
唉,它竟像北国的夏季,
生命边缘最沉重的一抹弧(8)new
只是一个短暂的客人!
5
……
林欣!
我已经看见她的影子了,那身与我第一次见面时的衣服,她在高高的中山大厦楼顶伫立着。
下面已经有近二百人云集了,警察也赶来了,今天是五一,中山大厦的门已经锁上了,下面开满了大片的郁金香;就是我梦境里的颜色与芬芳。一个警察正在联系大厦的负责人。
我从车子里面跳了出来,大声喊着:“林欣,林欣,我是痞子啊!”
她没有说话,静静地注视着我,我隐约见到她的微笑,在凄惨的春末。
手机响了,我马上翻开盖。
“我不希望你上来,痞子,今天的告别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怨言,不是吗?我始终是要去我自己的世界的。”林欣脆弱而平静地说。
我凄惨地哭着说:“林欣,我求你了,你下来我们谈好吗?你下来吧!”
“对不起,痞子,当一个人的生活失去了意义时,她不会留恋这个世界了。不仅因为你,我已经对人世没有留恋了,我想应该见爸爸了,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如此地想他。终于,我将摆脱最后的肮脏!”
我对着话筒大声地说:“不要,不要!呜……你下来好吗?我求你了!”
我的泪水已经是河流在泛滥,我知道世界已经在我面前暗淡下来了。
我知道只要坚持两分钟大厦的负责人就来了。
“痞子,‘捷克’交给你了,它会陪伴你的,就像我陪伴你一样。我终于可以摸到云彩了,好美丽,好美丽……再见了,痞子!星座的传说就在我这里永远终止吧!”
电话已经挂断了!
我慢慢地仰起头,我看见林欣正朝我摆着手臂。
不!
不!
我的心里在呼喊着:林欣,求你了,不要!
我迅速疯狂地往玻璃门上面撞去反而被弹了回来,我重重地摔在地上,额头上慢慢地流出鲜红的血液来。我又一次爬了起来,但是已经没有用了,我歇斯底里地喊着脑袋里已经不清晰的话语。我感觉到疼痛的自己已经陷入了流沙之中,挣扎开始变得徒劳!
“下面经常摆满一盆盆的郁金香,浓艳得很,是爱情的标志啊!我想,有一天我会睡在那样的郁金香上面,我就是花的主人!”
第一次见面的话语在我的耳畔罪恶地回荡着。
上帝!我选择了仍旧挣扎!挣扎!
但是……人群终于骚乱了!
不!!!我开始失望地蜷跌在大厦的门旁,双手掩住了眼睛。
我的眼前的黑暗的幻觉里看见成熟的天使张开美丽的翅膀,她开始从离云彩最近的地方轻轻地飞扬,在现实与梦幻之间飞扬了。
一道生命的弧线只是在节日的空气里面持续了三秒钟!
天使静静地跌落在生命的深渊——那里就像最后的流沙,熟睡在我梦境里的花丛上面,我在迷离的泪水里望着那些花儿,大片大片的郁金香啊,已经是火焰一样的颜色,它们开始燃烧了,最终幻化成为美丽、忧伤、诱惑而遗憾的白羊。
尾声 蝉
尾声:蝉(1)new
2005年6月1号,今年庐山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回忆。
今天是星期三,NIKE包在微风里面轻轻摆动。
莫叔叔让我去北京,他说Luck可以为我的实习提供良好的环境,可是周可冰的表哥在深圳,他们已经说好了实习见面,叔叔后来就说,你应该南下,那里是你的幸福所在,昨天我和你父亲通电话,他不愿意再阻拦你的任何事情,你大了,自己做主吧。
“你是不是对我特别失望?”我问他。
爸爸最终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我,我在电话里面听见妈妈叫他吃饭的声音,可是他没有走开,最后却说了一句:“实在不行,你就回来,扛不住的东西,老子和儿子一块顶!”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初他给我说那么多意味深长的话语了,我看见远处有几对情侣在雨中走动着,来来回回地闲逛,我接下来却听见爸爸问了我一句:“痞子,你还记得寒假时候我说的当兵的小伙子的爱情故事吗?”
我记得啊,就说:“我当然没有忘记。”
他欣慰地笑了,最后说:“里面的故事是虚实相生的,但是两个人物是有的,知道是谁吗?”
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还有一点玄机在里面,我赶紧问他:“是……是谁啊?爸爸,你告诉我啊!”他仍旧很欣慰地说:“是你爸和莫老……”
天渐渐地黑了,我的头脑轰地一下,原来事情是这样的,那么说,莫老与爸爸的友谊是怎么来的,是那样来的。
爸爸……
没有人知道我这一个月是怎么过来的,迷离就是我周围的全部,在人们异样的目光里面,我看到了种种复杂的神情。林欣的事情就像梦魇,我渴求知道同龄人的世界是否也是这般的杂乱,平静的湖水是圣人的权利,作为市井里面平凡忙碌的我们就只有勤劳地卖命。
为什么说自己“摆脱了最后的肮脏”?我想起林欣的话,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终于后来莫老告诉我:“奥地利有一个哲学家叫维特根斯坦,他有一句名言:自杀是肮脏的。”
天意的解释!
那天碰到叶子,她已经憔悴了,比我还要悲惨的样子,她远远地看着我站在酒吧的门口,她则在柜台里一个人喝酒。
我们彼此没有说话,我直接走了进去,坐在我以前习惯待的地方,与她对视着,她读不懂我眼睛里面的含义,因为我也不懂自己在看什么,但是我的脑海里面她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叶子。
她也是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看我。时间让人感到窒息,我不想来对叶子说什么,只是来寻找一种往日的感觉,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日子里,我感到生命像香烟一样经不住燃烧,那些美好的日子,在水面上面飘荡着。
一支烟后,我静静地离开了酒吧,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叶子,那天的云,淡淡的。
但是我后来在江滩边对自己说:“痞子,你会回来的,不是吗?”感觉就像是叶子自己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耳边。
有一个周末,我去图书城散心,远远地就看见了《沙床》摆在书架上面,是一本我读了很久的书,看看价钱也不贵,就将它买了下来。
管理员问我:“你喜欢这本书吗?我比较喜欢,是一种真实而迷茫的生活状态!”
我笑了,然后对她说:“其时我已经在网络上读过了,但是任何东西你有实物就是和虚幻的不一样。但是我不喜欢里面的生活方式了,那毕竟太悲观、太残酷,我接受不了,所以,买下它来是一种对生活的怀念与记忆!能够共赴生死的爱是伟大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享受的。”
我知道她听不懂我的话,可是我想,有一天她经历那样的生活之后,她就明白了。从这之后,就是读一些生活哲理的书来打发时间,郁闷不是我的全部,但是我感到头发竟然也在一根根地变白。
我就是这样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梦里面也是复杂的流沙一样紊乱的影子。
生活就是卖命。
但是我疑惑的是:“究竟是什么出卖了生命?”
莫老说最近会给我一个好消息,说我可能就要长一辈了。我当初没有明白,好好的怎么就长了一辈呢?后来脑子一开窍,我顿时清醒了。
“不会吧,这么快就有黄金下一代啦!”我跳起来,开着音乐,伴随着莫老爽朗的笑声在房间里面激荡。笑声是收获的产物,大家都有收获了,不是吗?我已经从主任的位子上面退下来了,所以连于小蒙也底气十足地对我说:“我最后会将你的主任取代的!”
我笑了,然后说:“小蒙,你爱情事业都如意了现在,所以请我吃东西吧!”
她眨了一下眼睛,之后就问:“说一个优秀的理由!”
我想了一下,很稳当地说:“哥哥都可以被抱了,难道就不可以拥有要求一顿饭的权利啊?”她打了一个很怪的手势:双赢!
尾声:蝉(2)new
那时的野草越长越疯了,淹没了所有美好的与丑陋的事物,南湖边的风景也开始见小样了,宿舍楼旁的郁金香据说又要复苏了,大片大片的绿色在我们的视线里面招摇。行政楼旁边,紫色的和红色的花,在褐灰色的树枝上开着,那时,除了园丁,几乎没有人比我更加关注它们。在春风吹过夏日来临的日子里,我的心在慢慢地舔食心灵的伤口。
“可冰,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啊?”我问自己。
你现在是怎么看我的?
我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似乎已经将自己的心狠狠地拧上了一个结,也许随着那次梦魇的出现,我的结已经长死了。
终于有一天,咖喱在梦里喃喃地说:“小灵,我,我和你回家吧。”
在半夜里的床上,听着这断断续续的话,我的脸湿成一片。
大家都要实习去了,不知道什么日子亲爱的哥们儿可以再相聚。随着放假时间的到来,我也开始准备南下深圳的行李,杂志、履历、衣物一件件清点,将我最喜欢的《父与子》也塞进NIKE包里。
两年前的今天说与周可冰过两周年的,现在一切已经融化在青春的时光里面,看着武汉这座让我沉浸了激情与痛苦的城市,我再次感受了它的厚重与迷茫。
我的所有的感情,似乎已经随往日的黄鹤翩翩而去,我最近就一直在怀疑一个命题:存在即是合理。我对自己说:“是吗?痞子!”
我似乎一直被某种情愫冲击着,仿佛应该给自己的感情一个新的了断,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对于可冰,我总是惭愧地面对她。
但是叶子终于打电话说,不管怎么样,你与周可冰今后总算在一块了……是吗?
当时,在听筒里面,《蓝色多瑙河》的调子也在大厅的酒杯里面回旋,多少年华已经像音乐一样让我们的心痛得流泪,我们可以毫无思考地拥抱着离别,谁知道我这时已经悄悄地变了?
我知道,年华是无效信。
我对咖喱说:“我以后再也不上QQ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今天是星期三。
火车启动的声音再一次响彻在武昌火车站的浑浊的空气里面,我看见卖《楚天都市报》的小贩在眼前不停地晃动着,我挎着行李,眼睛盯着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