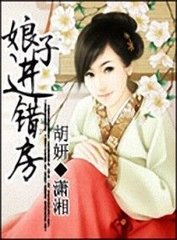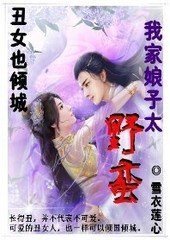娉婷娘子-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脸盆架也贴了红。墙上挂着一面荷花鸳鸯图的喜幛,垂迤到地面,旁边高台上燃着一对龙凤烛,一屋喜红映出一屋锦霞般的润光。她在这当中,用固执的、强装镇定的幽幽眼眸回望他,莫名的,他左胸感到一阵拉扯,极想抚去她的不安。
“慕家货船遭劫的事,我会与岳父大人详细谈过,待看如何处理。”他峻唇静牵,眉字有抹温柔神气。“你别忧心。”
慕娉婷身子一颤,呼息深浓。
猛然间,她被那张刚毅有型的男性脸庞重撞了胸房一下,既热又麻,一泉无以名状的温潮从方寸底端涌出,漫漫泛开,不住地泛开,无法抑止地泛开……
她须得道谢,说几句漂亮话。
她该要回他一笑,真诚的、大方的笑,藉以化解周遭浓郁得教她有些晕眩的氛围。
因此,柳眉柔扬了,扣着胭脂的朱唇掀启了,她想笑,想柔软地对他说些什么,挤出的却是哑哑嗓音。
“我……我、我喉发燥……可以给我一杯茶喝吗……”
“啊?”男人浓眉飞挑,略怔,又带趣地对住她笑。
第三章 共君此夜迷情多
慕娉婷喝下的不仅一杯茶而已,她几把锦绣丫头特意为她备上的枣花红芹茶整壶全灌进肚里了。
洞房花烛夜里,她跟新婚夫婿讨茶喝,她的相公该是个厚道之人,没当场笑话她,还下榻替她提来整壶茶,即便她晓得他其实笑在心里,也够让她感激了。
“够吗?要不要吩咐厨房再煮壶茶来?”他温言问,在桌边坐下,静看她捧着细瓷杯,一杯接一杯饮着。
尽管说是喉头发燥、干渴,她喝茶的姿态仍旧秀气而矜持,小口、小口地饮下,滋润含养着,像是每一口皆是天降的甘霖,不能轻慢。
“不用了,够的……”她克制不住脸红,捧着杯,呵出胸肺里腾乱的气息,努力让声音平稳。“谢谢……”
“你我已是夫妻,无需如此客套。”这话自然说出口,刀义天心中凛然,顿时有所体会,往后生命里将有另一人介入,不再是单独一个,他得对她的终身负责。
微笑,他对她招招手。
慕娉婷仿佛中了蛊。他招手,她想也未想便立起身,盈盈步至他面前,眸光直勾勾交缠着他的,不放。
他仅裹袜套的脚尖勾来一张雕花椅凳,拉着她的霞袖,要她落座。
她乖乖坐在他面前,两人近近相对,高台上的红烛火光窜跃,一屋的喜红宛若映在彼此瞳底。
她有些张惶、有些不知所措,微晕又微眩,朦胧想着他意欲如何,而自己又该如何?结果她糊成烂糜的脑袋瓜什么也思索不出,只怔怔由着他取走她紧握在手的茶杯。
“张嘴。”他从满桌的小碟小碗里挑出一物,抵到她唇瓣下,半带命令的口吻拨弹她的心弦。
她轻颤,极自然地启唇由着他喂食。喂过她后,他自己亦吃了些。
“再来。”他又挑一物抵近,她听话照办,檀口轻启,让那东西落入芳腔,眸子始终幽幽凝住他棱角分明的五官。
“还有。”他再取一物,她乖乖配合。
第四次喂食,他无语,仅将东西拿近。
她自然地掀唇轻含,把他的指也一块含住了。
他指尖抵着她的舌,上头的硬茧好粗糙,与她的丁香软舌全然不同,一粗一细,湿润地碰在一块儿,滋味甜得惊人。
真的是“惊人”!慕娉婷吓了一大跳,神魂整个从不知名处拉扯回来,脑袋瓜忙往后仰,放掉他的粗指,也跟着察觉到在舌尖爆开的那股甜味,其实是因为含着他喂入的一颗糖莲子。
秀脸赭红,宛若染就的大红织幛,她胸口仿佛来了一群野鹿,在那儿杂沓奔跑,冲撞得她胸骨生疼。特别是当她看着他从盘中取起另一颗糖莲子,自然无比地放入嘴中!糖粉黏着他的指,他探舌吮净,根本是把她适才“不小心”沾在他指上的温稠也一并舔去了。
糖莲子……
糖莲子?
她陡地会意过来,他喂她吃的东西分别是蜜枣子、落花生、桂圆和糖莲子,也就是所谓的“早生贵子”。她脸蛋又一次爆红,喉头的燥意已不够瞧,根本是从头到脚全融在荧荧火焰里,热得发汗。
见自个儿的新妇对着他发愣,傻呼呼的模样着实有趣,刀义天心口微暖。
他取来温酒,在两只小杯里斟入八分满,一只放进她手里,然后举起另一只,沉而清明地道:“成了亲,从此便是一家人,望夫妻缘分长长久久,不离不弃。”
他说的话亦是慕娉婷心中所想、所盼,有缘成双,那就真心诚意在一块儿吧。
津液缓缓濡碎舌尖上的糖莲子,她咽入那份清甜滋味,手紧握着小酒杯,心似也浸淫在甜酿里。
“嗯。”她低柔应着,在男人深意潜藏的目光中,红袖腼腆地绕过他同样持着酒杯的手臂,与他交杯共饮合卺酒。
酒香而不辣,甚至泌着桂花香气,在唇齿间流转。
酒不醉人人自醉,慕娉婷捧着发烫的小脸,觉得自个儿像是有些醉了,微醺着,身子轻飘飘,嘴角不自觉要往上翘。
男人离开桌边,没一会儿又折返回来,她正欲扬脸瞧他,一方喜红忽地兜头罩下,是她方才替自己揭掉的红头帕。
“唔?”眨眨迷蒙的眸子,她尚不及说些什么,眼前的红幕已被撩开、掀起。
男人刚毅俊脸沉静带笑。
“娘子,有礼了。”他弯身一揖。
她又嗅到酒里的桂花味,心窝温热莫名。撑着桌面,她温驯立起,还礼。
“……相公,有礼了。”
原来要对初次会面的男子唤出那个亲昵的称谓,似乎不是太难,倘若,对象是他……
*** 凤鸣轩独家制作 *** bbs。fmx。cn ***
“寻常”的洞房花烛夜,该是怎样的光景?慕娉婷愈思愈迷惑。
因娘亲走得早,她又无出嫁的姐妹,那些洞房、生娃娃的事也是直到她即要嫁做人妇,阿爹才让府里的老嬷嬷和大娘们私下同她说过。她们的口吻隐晦且神秘,说着、说着,眉目间还悄悄流荡出嬉谑和暧昧,仿佛无声道着:那事儿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光用嘴皮说不清、讲不明。
她却也非全然无知的。
前年春,爹往南方视察慕家在当地的养蚕户,打算早一步估量下半年收丝的货量和价钱,浏阳的布行暂由她和几名老管事打理。
她那日上布行盘点,午膳时候仍未休息,独自一个逗留在偌大的货仓里,温朗天光徐徐由高窗上洒进,周遭飘着细小浮尘,她先是捕捉到极低的呻吟声,断断续续的,像是肉体疼痛着,却又费劲儿压抑住。
她悄悄地循声而去,瞧见就在墙角、被成批蜀锦圈围出的一个小小所在,男人和姑娘衣衫不整地抱在一块儿,他压在她柔软的身段上,她雪白的腿大胆地圈住他的腰,他伏在她腿间着魔般撞击,粗嗄的低吼声中混着女儿家的娇喘……
那是慕家布行的伙计和丫头,大着胆子在货仓里干起苟且之事,她身为主子既已发现,实该出声制止,但在那当下,她又如何说得出口?
那便是老嬷嬷和大娘们说得暧暧昧昧、在洞房花烛夜时必会发生的事吗?
倘若必要发生,那么,她的洞房花烛夜算是极不寻常,相敬如宾且相安无事得很哪!
“春宵一刻值千金”的那晚,他揭了她的红头帕,互见过礼后,他便离去。
她怔怔地傻在原处,瞅着满室喜红和满桌碟碗,好半晌,扯不紧脑中一根思弦,待她提起力气打算到外头瞧瞧,他却推门进来,两手各提着一大桶热水,白茫的热气直冒,他把两桶水全倒进屏风后的桧木浴盆里。
“很烫,别碰,我再去井边打些水上来,一会儿就能沐浴身子。”他叮咛着,丢下话,人又跑得不见踪影。
“这……”这回,她追到门边,原要唤出唇的名字陡地羞涩而止。
不一会儿,男人再次提水返回,将浴盆里的水加至七、八分满。
慕娉婷想象不到他会为她做这样的事,他提来茶壶为她解喉燥,如今又提水供她沐浴。在“云来客栈”初见他身影时,当时的他全然强势,手段利落得近乎冷酷,须臾间便把一千恶人打倒在地。
他不像会伺候妻子的丈夫,但他确实做了,只差没动手解她衣衫、替她擦背。
那晚,她沭浴过后,他就着浴盆中的水洁身,听着传出的水流声音,她脑海里不住想象着屏风后的画面。
心跳促急得如飞奔百里,她脱下绣鞋上榻,弓脚而坐,下巴都快顶到双膝,藕臂环抱住自个儿,不想发颤,却又克制不住。
仿佛过了许久、许久,一道高大的黑影无声无息地来到榻边,笼罩着她。
她强迫自己抬头,看见他好深的眼睛,她勉强想挤出笑来,他却先给她一抹徐缓的笑,语气亦徐缓。
“折腾了一天,你肯定累极,好好休息。”
他旋身离开。
这一夜,她傻愣了好几回,与寻常帮着爹打理慕家家业的慕大小姐相较,简直判若两人,差上十万八千里。
直到前头与内房相连的小厅里传出声响,她才猛地回过神,连忙下榻冲出去瞧。
这一看,她又怔了,她的新婚夫婿并未离去,而是选在小厅边角的雕花檀木长椅上躺将下来,因身形高大,还拉来一张太师椅并在长椅下端,好让他跨脚。
他面壁睡下,像是累了,不一会儿便响起细沉的鼾声。
他没像老嬷嬷和大娘们所说的那样,猴急又粗鲁地扑来,脱光她的衣裙,一树梨花压海棠。
洞房花烛夜,她怀着问不出口的疑惑,独卧在自个儿一针一线绣出的鸳鸯锦上,思绪如在织布机上往来不停的梭子,想着爹和骏弟、想着这桩急成的婚事、想着拜堂成亲时,扶住她的男人的手、想着他饮酒泛红的脸庞、想着他喂她喜果,与她饮交杯酒时温朗的笑意、想着他揭她喜帕后的那双深邃眼瞳,以及那声“娘子,有礼了”。
她迷迷糊糊地睡着,醒来时,身上密实地覆着锦被,八成是到了子夜,她觉得冷,自个儿拉来裹紧的,只是原本收在两旁的床帷竟也垂放而下,教她有些儿想不通透……
“……少夫人,场子里的运作大致就是这么回事,前头铺子固定安排两个伙计照看,仅应付些简单的接待和寻常的议价,若顾客有所指定,伙计会领着人来到场子这儿,由打铁师傅当面和对方谈款式、开价钱。”管着刀家打铁场子和铺面的周管事年近古稀,皱纹满布的老脸上一对眼精光闪闪,瞧起来仍十分健朗。
此处是湘阴城南,长长一条南门大街上,聚集了不少打铁铺,专营各类铁器、农耕与狩猎等等用具的制造与贩售,三、四十年以上的老字号多得数不尽,常是父传子业、开业授徒,学得一技之长的徒子徒孙又在同条街上开设铁铺,就如此一间接连一间绵延下去。湘阴城南铁铺的名气大响,不仅当地百姓爱用,连邻近县城与南北方皆有商人过来批购。
刀家在城南设有自家的打铁场子和铺头,今早,慕娉婷便要府里管事备车,亲自来见识一番,藉以了解夫家所经营的买卖。
她原先没要这么做的,嫁了人,初来乍到,依她沉静的性子总觉凡事低调些好,内敛温顺,守拙而不争强。但新婚隔日去到前厅向公公婆婆敬茶时,当场,婆婆便把府内库房、账房、地窖等等的锁匙交由她,沉甸甸的一大串,她得捧在掌心里才不至于摔落,而公公则温言对她道,要她若得空,便到场子和铺头走动,那儿的老管事会帮着她。
于是,她来了,与锦绣丫头在周管事的陪同下,花了一整个上午扎实地逛过刀家铁铺和场子。
今晨飘雪,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草木霜冷,天寒风冻,百姓人家的屋瓦上皆覆着薄薄一层皎白,想她是在刀家打铁场里的二十三座风箱和长年不熄的熔炉边待久了,那热气烘暖她身子,她软裘早已解下,仅着一袭淡粉色的冬衫,长发中分绾起,梳着出嫁女子应有的款式。
为不碍着人家做事,她退到场子边角,眸光仍注视着每座炉火的动静。
她一边瞅着老师傅和年轻徒弟们挥汗如雨地敲敲打打,一边问着周管事。“我瞧过一轮,咱们场子里接的多是刀、剑等等兵器的打造,农用与家用的器具倒是少了,是兵器类的利润较好吗?”
周管事呵呵笑,抓了抓灰白山丰胡。“倒不是这么回事,咱们长期与当地县衙合作,透过官府取得生铁,就专办刀、剑的打造,却非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供给湘阴的民团和各地衙门使用,除此之外,也常送圣邻近几个地方,盈余是有,但不多就是。”
闻言,一旁的锦绣丫头忽地瞪大眼睛,话想也未想便冲口而出。“好大一座场子,挣没几个子儿,那做啥儿打铁打得这么使劲儿啊?”
周管事没答话,仍搓着胡子笑呵呵,瞥了神态宁静的新主母一眼,似乎也知这疑问无需他多此一举地作答。
慕娉婷心中明白的。
刀家与宫府间的合作并不单纯。或者,在铁铺这儿获利不丰,但“若欲取之、必先予之”,放长线钓大鱼,许多时候若官家可以给些方便、多有通融,办起事来效率就更彰了。
“刀家五虎门”不仅是个大家族,亦是江湖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