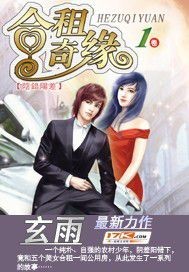乱舞缘-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吴佩妮向我讲了许多关于我们离别后的事情,我看见的尽是她的笑容,纯真、浪漫,还有可爱。但也很显然,她故意隐藏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在她讲完了后,我也向她讲述了我的事情,无论悲欢喜泣,都毫无保留的讲了出来,惟独没有说的是那次跳楼的事件。
其实,我们都不愿意打扰这快乐轻松的一下午,过去的只能成为一幅收藏的画卷,我们只需要好好的保存,无须太过认真。
后来,我与吴佩妮还做了一些无聊的事情,但很有趣:她带我冲进了女生宿舍,我带着她冲进了男生宿舍。这些都是相对彼此的禁区,但我们犹以打破。其实,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实质的禁区,只要存在的,人们都能走到;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禁区,惟有心灵的伤口。
晚上,似乎出了一些以外,月丹儿没有来上晚自修。而我右眼的眼皮跳动的频率也更加多了,下午快乐与轻松顿时蒙上了一阵灰。我的心不由的起了一阵担心,担心月丹儿,这个我喜欢的女孩子。
回到寝室后,我发现卫帜锋也没有胡来。这倒使我稍宽了一些心,我想,卫帜锋一定会照顾好月丹儿的。
然而直到第二天我仍不曾见过月丹儿。我的心头猛然冲出一股不好的念头,,莫非月丹儿当真出了事情?
我赶紧找到吴佩妮,问了她昨天下午去喝酒的有没有人回来。吴佩妮说,除了关祖还有卫帜锋,其他的人都回来了。我心中不祥的预感更加明显了,我拜托吴佩妮去问一下那些随同卫帜锋一起去喝酒的人,卫帜锋到底去哪里了。
吴佩妮有些不解,问我: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倒挺关心卫帜锋的那。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一味的催促她,道: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不听话吗?快去问问,我有重要的事情。
她笑了笑,说:我当然听话咯,我现在就去了。
可是,待她回来的时候,却告诉了我他们也不知道卫帜锋在哪,只是说在喝酒的时候和他的女朋友先离开了。这让我一时间不知道是该放心还是该提心,我想,我已经连卫帜锋都不能相信了。
月丹儿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中午,终于有人来告诉我,卫帜锋回来了,在寝室里。我没有顾的上吃午饭,抄直跑到了寝室。
在寝室里,只有卫帜锋一个人,他神态疲惫不堪,略有些颓唐之色,仿佛刚经过一阵剧烈运动,比如,打架。在他的眼睛里,尽是饱含内疚与惊恐的泪光。我的心扣上了弦,仅此我就能断定,月丹儿真的出事了。
我挪开了步子,怀着千斤巨石般徐徐的向他走去。他已经麻木了,对于我的步近丝毫不闻不问。直到我站在他的面前,预备开口的时候,他抢先说了三个充满哭泣之声的字:对…。对不起。
我的心弦顿时被拽断了。这次个字犹如一阵巨大的霹雳,将我抱有的仅仅一丝希望劈的灰飞湮灭。
我也麻木了,木然的问他:她…。。出了什么事情?
他的泪水再也衔不住了,大颗大颗的滴落下来,片刻间已经成了泪泉。
我默默的等着,等着他的回答;然而我也想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喜欢他永远不要回答,因为我害怕。
他无声的哭了一阵,终于回答了我:昨天…。。月丹儿被灌下了…。。迷幻药……
我的心猛的一震,有如里氏十二级地震一般,甚至牵扯到全身也霍然的一阵抖动。我突地打断了他的话:是谁下的药。
我不希望他再说下去,因为这样对他对我都是一阵折磨。我已经知道了,月丹儿步接了吴佩妮的后尘。
我开始燃烧了,业火即将到达无法控制的地步,就跟我两年前听到吴佩妮说她已经怀了孕时候的那一样,愤怒,爆发,撕裂——其实,那时我也仅仅只是喜欢吴佩妮,与现在仅仅只是喜欢月丹儿一样。喜欢,就已经足够了。
卫帜锋看着我沉寂且隐约透着抖动的脸色,眼中的惊恐接近面对死神时的那样子。他慌张难控的说:樊义,对不起,对不起,我对…。。对不起你…。。这件事情很复杂……
我的内心已经只剩下知道凶手,然后惩罚他。我提高了声位,再次打断了他的话:你不用对不起我,我现在只想知道凶手是谁?
卫帜锋有些不知所措了:樊义,你别再问了,算我求你…。。这件事情…。。我……
我再度提高声位——将近咆哮,打断道:说,凶,手,是,谁!
卫帜锋底下了头,许久后才缓缓的抬起了头。他木然的说:那晚,是关祖端来的酒,我和……
我肯定了下来,不需要再听什么闲言碎语。我阻止他的话,又道:关祖在哪?
他睁大了眼睛,忙道: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已经再也听不进他的其他废话了。我厉声问:他现在在哪?说呀!
他依旧慌忙的道:他现在还在学校前面的酒吧里,但是昨天晚上是我…。。
“是我”后面的内容我已经是听不清了。我没有再说什么。调转头冲出了寝室。我的步伐在加快,眼前的一切事物逐渐模糊,感性功能处于了麻木状态。
我真想哭出来,但又找不到哭的理由,于是只能干挤出了几颗愤怒的眼泪。泪莹中,不断的闪先月丹儿的身形,我们相遇,我们相识,我们相别,我们相决,一幅幅的影象一颗颗的泪,连穿在一起有如重现在眼前。
无论怎么说,出此之事也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去刺激月丹儿,也不应该允许卫帜锋带她去。我错了,都是我的错,就象曾经我眼睁睁的看着吴佩妮离去而不加去追与样,是我的错。想到昨天晚上月丹儿挣扎时候的情形,以及她的泪,她的呼唤,她的血,她的无力的反抗,我的心不由的一阵剧痛,痛的足以出血。
耳边的风猎猎作香,伴随着人声、汽笛声、碎裂声……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甚至都不知道我跑到了何处,但是我能肯定,我跑了许久,跑了很远。我驻了足,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分清了路道再次疾跑起来。
我来到了酒吧,毫无顾忌的冲了进去。里面很暗,在吧台处却依稀能看出几个身影,我走了过去,一步一步的走了过去。
果然是关祖。他正在和另一个妖艳的女孩子嬉戏着,在他后面还有另外一些小混混,他们都在笑——禽兽般的笑。
我在关组面前站住了,寒森森的盯着他。
他瞥了我一眼,惊讶起来:妈的,是你?
我冷冷的说:她在哪?你把她怎么样了?
他大惑:你说什么她她她的啊?她是哪个啊?
我生硬的吐出了三个字:月,丹,儿。
他豁然明白了似的,说:卫帜锋的女朋友?我怎么知道她在哪。还有,你说什么我“把他怎么样了”?我能把她怎么样?非礼?绑架?拐卖?
我没有耐心了:昨天晚上你他妈对她做了什么你自己心知肚明。
关祖还未来的及申辩,他旁边的女孩子已经拧紧了眉头:你昨天晚上做什么了?
关祖吓了一跳,忙是又抚又哄:我昨天晚上能干什么?还不是在家想你呗,嘿嘿。
他有转向我:小子,你快给我滚,别在我眼前碍着了。
我依旧没有动,但心中却有了几欲想动的念头。我大声斥道:关祖,你他妈的还算是人吗?你昨天晚上玷污了月丹儿现在还有狗脸在这里调戏其他女孩。
我心中的怒火已经熊起,燎原之势足以倾城。脑海里,月丹儿受辱的假想再度涌现,我看见他狰狞的兽态,我看了她挣扎的泪珠,我看见了,我都看见了。雄怒的火焰上再次洒上了一把燃油。我的拳头已经捏成了砖头,预备尽力的发泄出来。
只是,就在这个时候,关祖身边的女孩突然有了举动,她突地站了起来,竟手中的一杯酒泼在了关祖的脸上,然后一言不发的转身冲出了酒吧。
那杯酒中有一颗酒珠溅到了我的脸上,是冰的,是凉的,也是咸的。它是一颗泪。
我的心中的怒火竟然被这一颗酒珠浇灭了。是啊,命运注定要发生的申请是谁都无法阻拦的,到来也不过只是早晚的问题。事情既然如此了,多做举动也是无补于事了。
我注定还是犯了错误,月丹儿她此时此刻一定很脆弱,稍微的一阵风便能将她带走;她现在需要的不是报复,而是温暖,哪怕只是一丝的微温也足够了。可是我,竟然将这些全部都忽略了,只知道血气沸腾的去报复,去打击。这些有什么用吗?能带回已经失去的吗?
我想,月丹儿此时已经无法再顾及其他的了,她很冷,需要一张宽厚的肩膀去为她御风。
我真是个混蛋,我真是个笨蛋。
我的手不由的松弛了。
关祖愣了一阵子,随即转过脸来冲着我:你他妈的,吴佩妮给了你还不够么?你……你他妈的……
他已经气的说不出话来了,索性回过头朝身后的那些小混混们施了一个眼色,然后赶出酒吧去追那个女孩去了。
我没有动。看着关祖匆匆离去,然后看着徐徐向我走来的那些小混混。被揍一顿也好,我也是应该被揍的人了,也许这对月丹儿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我更是应该被他们捅上两刀,往喉头里去捅,网心窝里去捅。
突地,酒吧的门被推开了,是卫帜锋。他赶了过来,拦住了那些小混混,低声对他们说了一些话。我听见他说的:等等,我认识他,他好象是跟超哥的,不要轻举妄动。
“超哥”果然是有来头的人物,一言刚出,那几个小混混立即便变了色,当场愣住了。卫帜锋回过头,朝我使了一个眼色,示意我快走。
我转过了声,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走出了酒吧。我想,有卫帜锋在,我决计是挨不了揍的了,更别说被捅上两刀。
出了酒吧,一缕晖光抚过,空气顿时从压抑中解放了出来。可是,谁又能从寒冷中解放月丹儿呢?
晚自修我没有去上课,卫帜锋也没有去上课,我们都坐在寝室阳台的地上,沉默,发愣,看着渐渐被黑幕取代的红霞。
当黑暗杀死了最后的余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的时候,卫帜锋动了。他机械的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包烟,包装盒已经扁了,里面只剩下最后一支烟。
他将烟缓缓的取了出来,拿着包装盒的手仿佛突然失掉了力气,无奈的松开了。包装盒掉在了地上,梆的一响,犹如打雷。
卫帜锋将烟轻轻的递给了我。我看着他瑟缩的手,牵动着那根烟也抖动起来。我徐徐的摇了摇头。
他收回了烟,放到自己的嘴边,燃着了。
此时的他,每吸一口烟都变的很沉重,失去了往日的洒脱劲,就象一个只能开烟来麻醉烦恼的人一样,他只能慢慢的吸,让毒药缓缓的流遍全身。
那根烟只吸了一办,便被捣灭了,搁在了一旁的底墒。
卫帜锋说话了,带着淡淡的烟香与浓浓的心绪。他说:其实,这都是我的错,我很…。。很没用。
我沉吟了一会,淡淡的说;我们都有错,而且,错的最多的人——是我。
他动了动嘴,欲言又止。
沉默。
我说:有话就说吧,说出来会好一些的。
他怔了怔,终于说道:我们以前是朋友,但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我想问你,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么?
我再次沉吟了一会儿,没有声色的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朋友了?
他一愣,双眼顿时失去了光泽。他低下了头。
与此同时,我又开口了:我们,是兄弟。
他在次一怔,重新举起了头。但不一会儿,他又垂了下去。他说:我不佩。
我说:没有不佩,只有不愿。
几天后,卫帜锋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要去一趟上海。我没有多问他要到那里去做什么,他没有主动告诉我,就已经表明是没有必要告诉我了。
他最后朝我一笑,随着那个“超”一道上了火车。那一笑,我总觉得是《无间道》中梁朝伟临死前那苍白的一笑。
我着实的没想到,这一别,是真的彻底的没了消息。就象月丹儿一样,毫无音讯。
直到几个星期后,市公安局带回了卫帜锋的死讯——他在上海抢劫一家银行的时候,被赶到的警察当场击毙。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默默的哭了。他曾经的笑,曾经的恼,曾经的疯狂,都变成了黑白的颜色,凝固在了我的心间。这到底都为什么啊?
后来。卫帜锋的父母泣不成声的来到了学校收拾他的遗物,临走的时候,他们还特地的找到了我,将一封宗皮信封交给了我。他们说是在卫帜锋的枕头下找到的,信封上写着是我的名字,几经打听后找到了我。
我看了看信封,还是新的,没有拆开过的痕迹。封面上,卫帜锋的字迹留着我的名字。我完全没有感觉的拆开了信封,取出了信心读了一遍。
我吃了一惊,眼睛不由的睁的老大。
原来,事情居然是这样——
樊义;
首先要说的还是对不起。
其实那天晚上是我欺辱了月丹儿,我不奢望你会原谅我,而我也没有脸再在你的面前说明真相了。我已经查出了在我和月丹儿酒杯里下迷幻药的是超哥。我不会原谅我自己,更不会原谅他。
今天下午,超哥找到我,让我随他一道到上海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