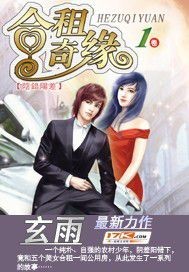乱舞缘-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声音很稳重,一时间让新武良怔住了不少。
但是,他还是开口了:你们想知道这家伙过去的丑事吗?刚才的进猪笼已经摆的很明显了,他是——一个奸夫啊,和别人通奸啊!
全场已经是一片惊哗,我听见“这不可能吧”、“太不可意思啊,他才多大啊”、“通奸…。。通奸啊,这事情闹大了”等种种议论。
我已经开始抖动,就象火山爆发时候的震动一样。
过去的伤口再次闪现,令人刻骨铭心的画面一幅幅的涌入了视线当中。吴佩妮妖艳的躺在床上,不断的做着挑逗的动作,不断的眨着诱惑的眼睛。房间的灯光很柔和,就如同吴佩妮的胴体一样柔和。房间一下子变的狭小起来,只能容得下一个人,两个身体只能结合起来才能生存。一个是吴佩妮的身体,另一个是谁的身体?
我在心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吼叫——不,不,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根本不是我,另外一个不是我!
我的手捏的很机紧,只差没有把自己的手骨头捏碎。
新武良愈加猖狂起来,他提高了声位,又说到:你们很惊讶吧?就是他,曾经还是一个初中生就跟人家女生上床,是不是很厉害?是不是很拽啊?他妈的还搞的那个女生进了医院做堕胎手术。厉害,当真拽的要命。他……。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因为我已经一拳击中了他的下颚。我将过往的恨,过往的痛,过往的伤,丝毫不保留的都转移到我的拳头上。新武良颓然的掀倒在地,而我并没有因此收回我的恨,我的痛,和我的伤。我扑在他的身上,将一切怨恨发泄在他的身上。拳头宛如雨点一样,甚至还溅出了血腥。
我的眼睛已经什么也看不清,不是泪水,而是仇恨攻心。
当我的眼睛从黑暗中苏醒过来的时候,新武良依旧躺在地上。我看见我的一只手扯着他的衣领,另一只手还在没有知觉的击打着他。他的脸上已经抹上了一层血迹,而他仍然还在笑。
我住了手,站了起来,沉默。整个体育馆里只余有新武良苍然却不失兴奋的笑声。我突然意识到,我中了新武良的圈套。新武良信口乱说了一通话,以我现在的身份谁又会相信呢?但是我出手打断了他的话,这是不打自招。
七
新武良还在笑,苍然的笑声回荡在整个体育馆里,也回荡在我空洞的心里。既然已经揭开了,也就无须再做挣扎的挽回。
我不再多说什么,麻木的走到体育馆的门前,将那大门轻轻的打开了。门,仿佛被尘封了许久,有如我尘封了许久的心灵。现在,门开了,我的心也开了。一缕阳光射了进来,正照在了我的脸上,很温润,很柔媚,很协和,也很苍茫——因为它射穿了我的心,射穿了我空洞无实的心。
体育馆外又是一批人,是夏雨请来的。
我从容的穿过了他们,眼前一片虚无。夏雨在问我,简杰一脸欣慰,陆宁沉着的在说些什么,然而我没有听进去一句话,我的听觉神经已经麻木了。
我失魂落魄的走着,也不知道来到了什么地方,只觉得这里防呢感很大。在我面前是一道栏杆,我开了过去,蓦地有发现栏杆后面就是天空,而天空的下面是一片绿茵草地,过过往往着许多学生。
我这才隐约的感觉到,我已经来到了七层高的教学楼顶上了。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风愈加的猛烈,搅的我的心也愈加烦乱。是啊,很烦,很乱,空虚无实的心突然间乱无头绪。我的头开始发闷,呼吸粗喘起来。曾经的种种长潮一般的再度涌现出来,那一段丑闻,那一段尴尬,那一段爱恨情仇。
负担,都是负担,都是我屡屡想甩却怎么也甩不掉的负担。
在我脑海里,生硬的记忆着,在医院里,在手术室外,在烟云中,我做在那里,心绪正如现在一样混乱,但毕竟那时候还有得选择放弃,而如今却什么没得选择了。医生出来了,告诉我们堕胎手术已经成功结束,而我也做好了最后的思想斗争,我向吴佩妮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及其在场的大众点下了头,说出了奇耻大辱的话——是我做的。
现在,我后悔了吗?
我后悔了,然而后悔也无济于事了,正如泼出去的水,正如失去灵魂的肉体,都生意经是无法挽回的了。
我的双手忽然抓紧了眼前的栏杆,一阵头晕目眩后,我萌发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应该翻过栏杆,然后纵身跳下去,不过只是七层楼罢了,几秒钟后,一切烦恼,一切痛苦,一切回忆,一切的一切,都将归于沉寂。我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牵挂的东西了,我的身誉,我的颜面,我所要隐去的一切,都已经完了。与其让所有人用厌恶的目光瞅着,还不如让一切都归于沉寂。多么轻松,多么令人向往。
我不有的双臂一使劲,翻身过了栏杆。那片草地瞬间近了不少。
就在我已经屈下双腿,准备让一切都归与宁静的时候,一个歇斯底里的声音让我滞住了。
我回过头,离我仅仅三步之远的地方,赫然出现了安琪的身影。她在冲我尖叫:不要。
我痛苦难奈的摇了摇头,说:我实在受不了,我很累了,背着的包袱很沉,我已经支持不住了。
安琪的双眼闪动了晶莹,她哀求似的说:不要做傻事,难道就是为了这毫无考证的传言?这不值得你这么做。你快点过来,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不知道是风沙眯眼,还是情绪难控,两行苍然的泪从我眼中溢了出来。我有些沙哑的说:时间的问题?你说的倒是很简单啊,我背着这个包袱快两年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两年我每走一步都塌陷的很深吗?包袱很重,重的就好象是一座山,我根本扛不下去了。
安琪的泪水早已经忍不住了。她哭着说:扛不下去你就干脆扔掉它。我早已经知道,你与吴佩妮的事情事实上根本不象新武良说的那样,新武良所说的只是你想要掩饰的表面。你根本就没有和吴佩妮睡过觉,你只是为了帮她掩护怀孕的真正缘故。说出来吧,这能让你好很多的。
我的脑海里猛地掠过一道闪光,一些过往的画面再次出现。它们很模糊,很残旧,也许是因为我掩埋在最深层的地方过久了。
是一个雨夜。夜幕下,束束银丝倾泻着大地,一切都被润湿了。吴佩妮跑着到我家找我,她单薄的身躯被雨水密密的侵袭过一遍,发缘还在滴着晶莹的水珠。她红润着双眼,不知道是曾哭过还是正在哭,有一种凄美。她憋了很久,告诉了我她被人玷污了。我很吃惊,也很愤怒,冲动的想去找那凶手。可是,她竟然阻止了我,并且哀求我替她保密。她说,她已经怀孕了,她不希望自己是被其他人玷污的。她希望让我冒名顶替,让我承认,是我玷污了她。没错,最后我选择了冒名承认,可是不到第二天,吴佩妮便露出了真形。她背弃了我,跟着凶手一起走了,留下我一个人,背负着黑名。
我再次无奈的摇了摇头,对着安琪轻轻的说:你给我住嘴!
这句话之所以说的很轻,是因为我的力气全部都用在了阻止泪水上,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吼叫了。
安琪向前走了一步,与我的距离只余下两步。她泣声到:既然她已经背叛了你,你又何必再为她苦守着秘密,这值得吗?
我不知道安琪为什么会知道真相,也没有多余的心神再去探究这个问题。我依旧痛不欲生的冲她丢出一句:你给我住嘴,听见没有,住嘴呀。
这句话较比前一句话更为轻了,因为我的泪水已经决了堤,不仅我自身的力量用去抗洪,连超支的力量也都拿来堵住堤口。
安琪又向前有了一步,现在离我只有一步之距了。她挣扎着说到:我不要住嘴,我要说下去。我要说,其实我一直都是喜欢着你的。
我的心震了震。
她抽噎了一下,继续说:简杰曾经不是告诉过你,我老是在一个本子上记载着什么东西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在那个本子上写了一些什么,我写的是你,都是你,你的悲欢离合,你的喜怒哀乐,你的言辞谈吐,你的一举一动。没错,我很喜欢你,但仅仅是喜欢,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我爱你,只会让我更痛苦和徘徊,在你的心里,其实早就已经不可能有我的位置了。我每天只能用笔将你收藏在我的本子里,去慢慢欣赏,去慢慢了解。我……
我大断了她的话:住口,住口,我不想再听什么了。
安琪又进了一步,站在了我的面前。我们之间,仅余一下一道栏杆。她大叫着:我就是要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如果你跳下去,我……我也跟着你跳下去。
我再也按耐不住了,爆发似的的甩了她一耳光,并且吼到:我的事情,用不着你来管。
也许是堵住决堤断口的力量突然撤走,让得猛烈的洪流发助了一把力量,这一记耳光的力道着实的超长了,竟然将安琪打翻过栏杆,抄直从楼顶跌了下去。
我吓了一跳,想回过身去扯住她。然而待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坠过了六楼的位置。我的手空空的挣扎着,在虚无中打捞她逝去的残影。
安琪是面朝着我,她的双眼还含着泪痕,而她的嘴角却是扬起的。她在笑,仿佛在告诉我——我可以替你死去。
我只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她徐徐离去的身影,还有被气流吹散的毋发。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空际,我感到了我不能死,我也感到了她不能死……
**************
你也许从不相信巧合就是缘分,然而巧合就是缘分的初始化。
安琪没有死,这也许就是证明巧合是缘分的最好的证据。安琪从七层楼高的地方坠下去的时候,正巧陆宁从下面经过,她就坠在了他的身上,两个人当场都晕了过去。而与那同时,我就那么的呆在原地,直到被几双手拖回过栏杆。
医院里,医生说安琪和陆宁都已经脱离了危险。
陆宁是先清醒过来的,他刚醒过来,我与他同时问了对方同一个问题:你没事吧?
接着,我们便相视一笑。我说:我若有事,还怎么能坐在这里和你说话呢?
他的笑容忽然间断。他忙问我:出什么是了?我记得我在体育馆门口见到你后,一转身你就不见了。我看你当时神不守舍,后来我又听我老哥说了…。。关于你的那…。。那件事情,我怕你一时间心里承受不来,就与简杰分头寻找你。早到操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被一个什么东西给砸晕了。哎,现在的年轻人啊,环抱意识真差劲。
我笑了两下,对他说:砸晕你的可不是什么垃圾,就在你身后躺着呢?
陆宁扭过头去,只见安琪躺在另一张病床上。他立刻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但不一会,他又换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来。他惊诧的问我:她怎么可能掉到我身上来?她是掉下来的?
我点了点头,没有做声。
陆宁显得更是难以相信,他说:到底出什么事情了?她是从哪掉下来的?别告诉我她是想不开,想去…。。想去寻短见。
我沉默了一会,然后淡淡的回答到:出了大事,她是从教学楼顶上掉下来的。
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没有答全,因为我认为往往寻短见的人不是因为想不开而去寻短见的,而正是由于他们想开了一切,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想下去的,生命淡虚了 ,所有才去寻死——这是我的认为。于是,我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丢下了一句:她不是寻短见。
接着,陆宁又向我问了一阵关于安琪坠楼的问题,而我去没有真正的回答过他——我又怎么好意思再去提起这件事情。
*************
两天后,我回到学校。我听学校说,领导对于我跳楼这件事情很重视,甚至仅在刚才的一段时间还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校长恼羞成怒,拍案时拍案,摔差杯时摔茶杯,只差没叫着要看批斗会批斗我了。会议最后,校长不顾老师们的苦求,硬是宣布要把我开除。听到消息后,我便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走人。但我刚从书桌里拿出书包,就又听见校长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兴许校长在开完第一次会议后被一阵冷风给吹冷静了,考虑到我是不可多得的好学生,为了振兴中华,于是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只记我大过,留校查看。不过第二次会议的结果刚传到我耳朵里不久,我的书包还没来得及放回书桌,便又有了校长紧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的消息。八成是校长完全清醒了,为了祖国的未来,不惜抛开校荣,终于连记大过的惩罚都收了回去,改作了记小过带写一份检讨。
我没有写检讨,也没有再去知道学校到底看了几次会议。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第二中学,因为这里留下了我太多的过去,留下了容不下我的东西,留下了我缭乱的心。它留下了它们,所以我不能留下。其实走与留之间只介于一念的思量,而仅仅是一念的思量就能改变许多东西。
我轻轻走了,走的也轻松了!
**************
记得我临走的时候,有许多人来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