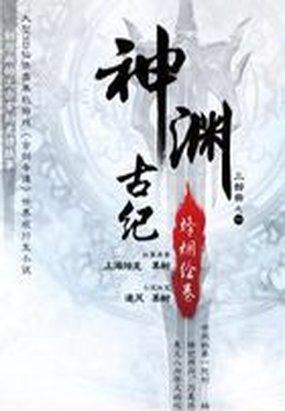烽烟杂感随笔集--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仍然尊重新诗音乐性、建筑美、诗质和谐性的原则下,“丁香般的姑娘”以其个体对命运的纯粹伤感成就了戴望舒的现代诗歌三十年代领袖位置。包括卞之琳、废名、何其芳、纪弦(台湾)、徐迟等。共同树立起三十年代“先锋现代派”诗歌的大旗。然而不久,他们又抛弃了这一诗学审美原则,以更深更广义的现代知觉意识试图超越西方前期象征主义。这个良好的愿望不可否认地成为共识,并因此而派生出大量实验主义诗人。
但在极度的喧哗中,“实验”的纵欲埋葬了“现实”理想。这是造成大量优秀诗人没有载入史册的真正原因!我个人认为:这个时期诗歌的喧哗甚至影响了后世诗人对诗歌从审美
意义上的判别原则。在没有深刻理论基础的背景下,大量实验诗的紊乱与无序左冲右突,它们想合围诗歌的圣地。但他们只是点燃了诗歌边缘化的火种。
“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诗不是某一感官的享受,而是全感官或超越感官的东西”,“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情的程度上。”(《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这个论断恰当地再现了这个时期的创作倾向。“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戴望舒终于借《我的记忆》陈述语言的形式,完成了先锋的最后实验(这或许也是目前现代诗歌陈述语言形式复活的原因之一),完成了个体主观世界的理论体验和放弃外部世界描摹或投影的行为实践。
“是深夜,
又是清冷的下午,
敲梆的过桥,
敲锣的又过桥,
不断的是桥下流水的声音。”——
卞之琳《古镇的梦》
卞之琳敲出了现代实验诗歌从象征主义到智性、玄学主义的微妙变化。成为又一轮先锋诗歌的代言人。而三十年代的诗歌终究笼罩在这种智性与玄识的起伏与更迭轮回中。
历史的盛宴,邀请的总是两种人:政治家和诗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无疑使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歌蜗居于边缘地界。蹲伏着的潮音式微,但现代诗歌艺术的诗学方法与诗性喟叹并未消失。从哲学、绘画等艺术类别中提炼诗意的花朵,并结合个体人生体验与历史相融共渡沉潜的种养创作观,基本构成了“存在主义”现代诗歌的内质。
“我常常想到人的一生,
便不由得要向你祈祷。
你一丛白茸茸的小草,
不曾辜负了一个名称。”——
冯至《十四行集》第四首
建立在表达人世和自然相融基础上的诗意链接,深刻再现了“内咏性”诗歌向外部世界的借鉴于试探行为。冯至的“存在主义”抒情方式,是对现实人生或伟大或平凡事物的歌咏。由于诗意的自然渗透,形成了强大的诗性空间。相继而来的是“九叶诗人”——郑敏(女)、袁可嘉、穆旦(查良铮)、辛迪(王馨迪)、陈敬蓉(女)、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唐祈(唐克蕃)和唐扬和。他们注重智性与感性的融合,象征与联想的互动,把现实的存在意义通过更为活泼和生动的语言形式进行加密加厚,并赋予这种存在性一定的韧性和弹性。而这时期与之呼应的还有另一重要诗群“七月”(以曾卓为代表),承接了象征主义的内核,形成两条不同的现代诗歌河系。
无疑的,诗歌结构的完整与格式的严谨以及语言的精粹构成了“九叶诗人”明显的创作标志。而诗运的衍变,使得“九叶诗人”成为四十年代诗群的象征。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野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远山
围着我们的心
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郑敏《金黄的稻束》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语言所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穆旦《诗八首》第四首
在高雅、纯洁的表述中,智性话语的从隐伏到凸现的不断更迭,造成诗歌内在律动的波形曲线。而更多的哲学意味则融入自然与人性的对视中。这时候,蕴籍含蓄的意念传达不断通过自我拷问的深入而无比诗意:一方面“中国古典文学”推波助澜,一方面西学思想乘风破浪而至。在高度统一的主旨下完成诗意的完整合围。
但沉迷的,低隐的,智性的诗歌仍然掩饰不住自身心理的褴褛,在四十年代大众注意力分解的作用下,诗歌的身份仍然是盲流或流民。
从现代诗歌的源起“旧诗新意境”到四十年代的诗歌“内在感动”,尽管一个世界有许多声音不断响起。但诗歌是寂寞的。它在做着一个自己无法抵达的梦。
“世界上有哪一个梦,是有人伴着我们做的呢?”(郑敏《寂寞》)
就这样站着吧。站成现代诗歌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秩序。
2004。1。25——26于深圳
第三篇:文化裹足及悲剧现象
第三篇:文化裹足及悲剧现象
论文化的“裹足现象”及诗歌的“悲剧意识”
文/烽烟
生命存在于文字之中。文字是一种不断创造奇迹的行为。“它们是人类的光明——也是人类的黑暗。”(《英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的文化史,从某一角度来说,属于奴才抗争的历史。从《史记》中列入《游侠列传》开始,到后来由于文网稍疏产生的《红线传》、《聂隐娘》、《昆仑奴》、《虬髯客传》等侠义小说,均从开放型的时代特征中觅到文人的抗争性意识。最后出现了《水浒》、《西游记》达到抗争的高潮。建立在一种主观上的虚假的前提下的存在意识,这类文字的普遍意义在于:它们作的仅仅是客观上的一种精神反击。
包括李白、杜甫。包括一切仗剑行走的诗人。他们最终都将回到这个虚假的前提,变成文字的奴才,生发出悲剧意识。
而一部中国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是一部诗的历史。文化与诗除了有一种土壤和植被的关系外,它们之间还存在有另一种契约,一种感应,一种相互适应对方的性格。当然,还有一种强烈的融汇于对方之中的愿望。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诗人注重的不是天人的对立、冲突,而是天人的渗透、协调。这种偏重于人格的自觉和道德的追求,形成诗人主体对外界的感性认识。重阐释,轻认识。造成诗歌大面积的技术化、实用化、经验化倾向。中国古代的诗人之间的竞技,更多着力于机智、才气和学问,而缺少认知讨论。庞大的诗人群沉醉于“风雅”之中,忽略了对自然与社会本质的深究与叩问。在一种隐逸的追求中,在技巧的沧浪里,淹没了自己的全部价值。
中国文化只是在诗歌中才表现出自己的活力,但最终也许会让人哀叹。相对来说,诗歌的审美、教化、认识三种功能中,以认识功能为弱。比起具有广阔的社会生活容量的,作为“人生科学”的小说、戏剧,诗歌的认识功能就更弱。在人格与道德的交织催化中,诗人表达着主体性和经验性的东西,最终完成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教化作用。
“中国缺乏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朱自清语)这时候,诗歌作为一位“形象代言人”传递一种“心灵密码”。
在使命感的百般折腾中,痛苦的中国文化的先锋者,注定要孤独。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诗句
三十刚出头的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完成他的爱情传奇。一位是“使君有妇”,一位是“罗敷有夫”,浓妆淡抹的西子湖畔,诗是美的。但诗终归是诗,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终究锁住了胡适“圣人”的面孔和姑娘无限的惆怅。
这种情况下,诗歌沾满了道德的脂气,道德渲染着诗歌的悲剧性。作为文化的核心中坚,诗歌以“穴居”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存在使命。而这种穴居的方式决定着诗人的极度隐忍性——很不幸,这是一种更大的悲剧。
“坚决无情地或者把思想发挥到光辉的顶点,或者把它归结为廖误。”(金岳霖语)不可否认的是,诗歌的极限美感在于一“隐”字。美而隐,隐而美。基于生活场景中的“避难性”行为,诗人领悟到“隐”的重要性。但“隐”不是裹足而足不出户,它存在一种乖巧的探望(类似推窗问月的行为)。
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有“空框结构”的特质。欣赏者可以从容地在空框中填入感受、理解、联想等。如果阅读者找不到这空框,“隐”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但协调、整饬这种复杂的关系,必然会导致伦理至上主义。而诗歌一直都是在试图拒绝所有主义的介入。构筑在一种强烈化的忍耐与观照上的诗歌自觉意识,是诗歌对文化的自然反馈和暗示。参预、补充,甚至修改着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在这样的不断变动中,诗歌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这时候,我们应该看到:一种文化面临变革、发展的关头,总需要有一个对比参照系。也许,只有将内与外的参照移到未来与传统的参照上,一种文化才能自觉自愿地向着新生命走去。而这过程中,诗歌必将排斥某些共过患难又失去意义、完成使命的精神产品。
“兴奋源自错觉——云层是最后的札记
卸下三十年的固执溶入自然
皱巴巴的脚印,是一种签名习惯
合上日子,测量久违的炊烟
你将再次去远方潜伏卧底,并捎回早夭的涛声”——
摘于自选诗《先行者》
“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元好问句)“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可者为物。”(王国维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传。文言传》)追求“无人无隔”之境的中国诗人们,虽然因社会与历史的原因,试图达到盎然生命及自然生机的契合与同流。但诗歌的价值并非仅仅体现于此,它有着更深更广的社会包容性与历史使命感。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
秋风庭院藓侵阶。
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
晚凉天净月华开。
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李煜《浪淘沙》
破碎的人生需要有取舍的描述,需要有取舍的想象。技术的存在类似一位德高望重的责任编辑,他将对一切复杂的描述作重新组版或裁剪。诗歌在这种看似简单的线性排列中捕捉历史的哀婉和虚无的诺言。
“犹之说没有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恐怕隋唐佛学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没有隋唐佛学的特点及其渲化,恐怕宋代的学术也不是那个样子。”(汤用彤语)正是基于文化的奇特承接性和包容性,诗歌作为文化的代表与核心,应该理所当然地坦然扛起大旗,不管有多少文化冲突、争鸣,不管自身发展如何多元,都该露出自己的精神面貌与气质。
“想与人相似是真的与人相似的开始。我们将据以为己的词正是早已回荡在我们心灵中的词。”(莫瑞斯。弗雷德曼《否认虚无》)
“小心弄碎慈眉善目的保护
灯光为你穿上制服
你守候一种秩序
孤寂地观察世界的荒芜”——
摘于自选诗《书签》
诗人“兼济天下”的宏志是诗歌“入世”的根本原因。
入世未果,落笔有霜。诗人在大悲大喜大痛大乐的爆发临界点,寻找属于自己的风趣。那里有遁逃,也有征服;有豁达,也有绝望。
2003。3。1于深圳
第四篇:说说诗歌的非自觉时代
第四篇:说说诗歌的非自觉时代
(临屏感悟)说说诗歌的非自觉时代
◎烽烟
生活中能够出现的所有现象,包括情感,都将在语言的精心谋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