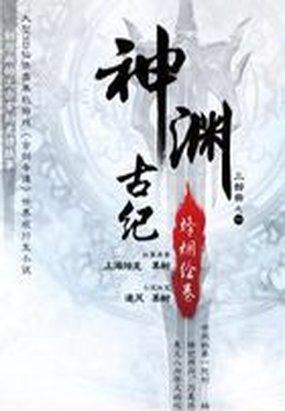烽烟杂感随笔集--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在论及“当爱情普及时,我们是否应该普及历史和文化“这一问题时,提供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教学版本。
未曾衰老的,必将衰老。衰老,并非意味着完全死亡。它仅是一种奇特的过程,或者说是一段必然的历史。
如一盏青灯的命运。“夕阳山外山,今宵别梦寒。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李叔同清音横流,自斟自酌倒也罢了,后世王孙为何硬要那些稚嫩的声音唱这种诡异之句呢?
居高声自远。放下万因万缘,放下念念浊流。“聚是因,散是缘”,弘一法师恢复本来面目说法。网开一面是佛性,别有洞天是道理?类似的模糊逼迫文化传承开始它的荆棘之旅。
历史应该是不分性别的。文化也是。不分性别的历史才是最自然的历史。泱泱大国,千秋帝王,令我最为关注的是康熙。把他列入“民族英雄”模式的典范,我想他会扭捏不安的。而称之为“民营企业家”,可能比较恰当。某一日,也许他刚刚狩猎归来,也许还喝了一点自己调制的上好陈酿,他厚积薄发,为孝庄太后写下一“福”字作寿诞贺礼。通体琉璃净身,字体挺拔瘦劲。喻意:多田多子多才多福多寿。后世谓之“天下第一福”。作为文化的特别象征(或替身)。它表达着一种不分性别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合理的文化传承性。
如果可能,我十分乐意并希望他做我这顿晚餐的特邀佳宾。我们会微笑,会有趣地讨论“焚书坑儒”和“长城情结”的关系。我们可能因过于兴奋而醉了。忽略了陶渊明从世外桃源发来的急电:科技进步,文化殒落。堪忧。速回。
但我们早已醉了。醉在历史的子宫。
有一些义士拧起了灭火器或自动加入清道夫的行列。开始剿灭烽火狼烟,清除满腹悲歌这些令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罪恶源泉,其实都抵不上因文化的丧失或崩溃造成的“移民屯田”(见附注)。历史的无奈缠满了绷带,象个悲观的被迫移民者,向土地的叹息倾诉:某个黄昏刚刚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故事韪崭辗也许,我们应该把<<二十五史>>拿出去晒晒太阳了。晒净,晒透。然后重新放回溢香的书架。
“俄罗斯大地辽阔,可我们已无退路,因为后面就是莫斯科!”这不是哪位作家文人的豪言壮语,只是一位普通军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呐喊。细弱的呐喊沿着人类扭曲的灵魂一路攀升或许,在暮色启动星光之前,历史和文化,会扛起鱼竿,淡然作一朴素的转身。偶像就是生产力。创造奇迹的不是星光,当一个物质和娱乐相煎的时代到来时,2002年巡演的文学列车,停在逐渐歪斜的黄昏交错处,冲洗伤口发炎的照片。而星光早已魂飞魄散,它们满身创伤却掩饰不住万古的沉寂。灯光却一头钻进狭小的房间,在躁动中喝下剩余的砒霜。远远地,远远地呐喊着逝去的精神和文明。
附注:“移民屯田”指由于兵灾水火造成的人口迁居,大量的迁居同时造成区域性土地承载过重,水土流失,生态失横。大患也。
2003。1。26于深圳
第四篇:文化随想
第四篇:文化随想
文化随想
文/烽烟
(一)
2002年,有许多种潮流袭卷而来,其中包括时装和文化。型台上裸露的东西越来越多台上内衣薄如蝉翼,透明装裙袂飘飘。在音乐里蜿蜒的时代,渐渐吸引更多的眼睛。而这时候,余秋雨刚刚完成一段文化苦旅,卷入一场古怪的官司风雨。我不知道他的文字带来了多少文化审视、社会效益和商业价值,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他至少释放了文化大胆介入市场的脚步声。与之相向而行的还有旅德画家萧瀚先生正在进行的世界文化苦旅,作为新安画派的承传人,他的山水画印证着中国几千年的脚步声。“穷尽色彩之光辉,融合笔墨之精神,抒发现代之情怀”,他卷起学术界一阵飓风后穿过商业文化圈的包围,安然在笔墨山水中与范曾手足交谈。
放下眼前的流光溢彩,对于T型台的感官印象,好象所有的陈列只是为了较量脂肪的厚度或含量。当然会有一些惊艳,如刚刚流行过的宽大腰带,它们环游世界,它们面带微笑轻松扼住我们的呼吸。2002年的冬天寒气逼人。四大潮流之都竞相汇聚,登台亮相的肌肤冷酷无情。型台上的文化开始武装自己,它们爬上钢盔,袭击面部,甚至武装到牙齿。都以为占据人们视野的唐装会蟋蟋蟀蟀走来,并且不会轻易离开。但转眼就凉了。在天空下,灯火中,飞扬的流苏和民族风情完成最后一次篝火晚会。夜幕中,屋檐下,仿佛李清照和她的妇女解放的口号正慷慨陈词。而柳三变在这样的夜晚一定会“姻脂粉里花袖红,娇艳百种”,从文化意义上说,柳永是幸运的,虽然没有做官,却少了官司纠葛,安心创作造就一代宗师。从商业行为来说,“奉旨填词”难道不是最佳的商业招牌?只可惜文人相轻之态作弄着中国文人,尔后花间一派只余周邦彦唏嘘长叹。想象是无罪的。慢慢从花丛中出来,绕过一些历史渊源和文化故址,屈从或反抗、泪水或欢歌只是时代胸前的饰物,而我们不必过多地追究千疮百孔的文化历史。
(二)
波普艺术的本源在英国,它的滥觞却是从六十年代的美国开始。这期间有两个人纳入我们的视野:汉弥尔顿和罗伯特…安纳森。一前一后,代表一种行业艺术特征。同属于行为艺术的一部分,论及波普艺术就会令人想起“玩物志”。作为实验剧、摄影、DV、装置、架上绘画、广告、海报等多种艺术门类的代名词,“玩物志”作品的创作从个人审美出发,通过工业科技“技术”提供形成艺术的基本保障。波普和“玩物志”的共谋,试图搭建行为艺术的天堂,它们的灵感主要来自电影、卡通、标志、摇滚甚至色情的变形与夸张。我相信这些西方行为艺术并不能威胁中国近现代艺术,更何况古典文化。因为它们多少显得散漫了一些,并且带有过份的商业行为。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和艺术可以依附于商业行为孵化文字激情和时代铬印,但过份的商业行为却可能给文化和艺术带来本性变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所谓骨气侵淫过无数日子,山高水远,文化和艺术远离或背弃生活的行为本身就是对自我价值取向的一种否定。但不容忽视的是现代人的这类所谓全新偿试,融入商业行为的偿试,不过是借助高新科技生产的材料而不是全新的文化思维。这是时代的致命伤,也可说是文化和行为艺术类的不治之症。
这让我想起《兰亭序》和《祭侄稿贴》的纷争。同为公认的书法艺术的登峰之作,却有不同的评判命运。〈兰〉因其符合中国文人的中庸思想,因而成为“天下第一”。而〈祭〉却因有“剑气”而屈居“天下第二”。我想当颜鲁公闻讯后,一定会在悲痛的基础上增加一点“愤”。因了上述的“规范思想”及到后来的“馆阁体”,中国文人岂能不“愤世疾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的演变,文化和艺术的噪声;二是文化和艺术缺乏商业嫁衣。
自由是美好的。但自由有时却是不可靠的。有序、合理的空间才能产生回肠荡气的文化和艺术,也包括无限商机。从时装表演到波普艺术的眩目,从文化苦旅到文化纷争,中国文人早已“纵欲过度”。就我而言,以为自己一直在走一条通向自然的路,其实,我不过仅仅在更加远离生活而已。
2003年4月于深圳
第五篇:文化的宗祠
第五篇:文化的宗祠
文化的宗祠
文/烽烟
很想写首诗的,况且思维刚同纪弦(原名路逾)象鱼一样散步归来。余晖未尽。却一头掉进余光中的《乡愁》里。纪弦的脚步够寂寞了。洁净。凄清。余光中的乡愁却一缕一缕浸过来。正应了西方的一句妙语:“诗人向他自己说的话,被世人偷听了去。”
“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一时觉得他们就象蜗居在我家乡的宗祠里。忽然起了一阵凉风,飘飘的竟吹远了宗祠的神秘,散尽崇山峻岭之中的满目萧索之意。努力驯服泪花后,我想我应该买些香回去。看看罢。
宗祠于我,感观上一直是壁垒森严的。周围常有密密丛林,也有环水。建筑样式怪异。空洞。我常常想:它须有些思想才好。
我们这个年龄,幼时大约都体味过一种简单的传承:衣服的传承。兄弟姐妹,相互传承一件衣服。很旧。也过时。肥瘦宽窄不论,竟蛮好。象那时玩的击鼓传花。往往是在春天踏青时节,一溜淘气的笑声圈一圈,由老师击鼓。鼓点停,花在谁手中,就由谁受罚。却不罚做苦役。唱支歌,跳曲舞,背首诗。简单,有序。虽满脸桃红,形态有些窘。竟兴奋异常。没有花的阴戚之叹,亦无雨打梨花的调子。只是笑声在坡上一阵阵打滚。
没有注意到萋萋丛中隐藏的那座宗祠。阴郁的宗祠。
其实我是去过的。几个学童吟着唐诗一溜青烟。摸着四大金刚的铠甲爱不释手,菩萨似乎微笑不语。我们就在她的手心里放些鸟蛋。看她还是微笑不语,我们急怒,干脆一脚踹开山门,让凉风灌她脖子。当然最后只能罢了。只记得当时我余怒未消,还在宗祠大门上阴毒地写过一行字:魔鬼的地狱,人的天堂。
现在想来,似乎菩萨的衣服都是会说话的。每一处皱褶里都藏有神秘的文化。神秘的佛性文化。
佛学其实不是宗教。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大抵都从佛经里提取过养份。王阳明从佛经里受到“知行合一”的启示,遂名动天下,传承后世。中国文人常与僧道为友,出入山林庙舍。并不是简单地想逃避什么,而主要是冲着一种文化而去。
按照佛经记载,教师进修的制度就是释迦牟尼佛首创的。如孔老夫子一样,“教不倦,学不厌。”他当年也有许多成就可瞩的学生。这些学生分派到各地去教学,但每一年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要回到老师身边,称为“结夏安居”。我们可以理解为“知识复读”。那时印度从四月半到七月半淫雨霏霏,在外教学不方便,所以统统回到老师身边,接受老师的再教育。同时,学生之间也可相互磋研。类似现在的教师进修。
这是应该的。释迦牟尼就象一座移动的宗祠。所以佛学的伟大在于它的传承方式。合理的,有序的,具前瞻性的传承学习是文化延续的根本。
从这种意义上说,宗祠,并不是通风报信的阴司入口,也非上等的棺材。它属于一种文化。有宗祠的地方,都会有宗谱,记录了几百年的家族史。完整。可信。但靠什么传承下来呢?——是靠一部无形的宗族教育法。有几分宗教的影子,有几分复苏人性的召唤。却没有提到文化。这里可能有一点暗示:并不能奢望每一代的子孙都会记得烧香,加之宗祠自身的悭吝脾性,因而竟衰败了。试想想:宗祠的肚里装的香炉、烛台、幔帐、银器……没一件是它自己的,它会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快乐是缺乏醒世的快乐;痛苦是充满习惯的痛苦。
文化的宗祠不是时间冲刷的马桶,虽然蹲踞着,也还有它自己的威严。
所以,我还是很怀念以那座宗祠为背景的孩提时代。如今站在那里,却只余下惘惘的荒凉了。
2003年4月于深圳
第六篇:历史的气质
第六篇:历史的气质
历史的气质
文/烽烟
我们不习惯单独用拇指去丈量地图,通常还得加上它的邻居。土地和空气为我们送来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历史却要靠我们的脚步去标注它的灵魂栖息地。
而大于我们生命的是时间。时间拂袖而去,穿着记忆的套装——读书,学习,上班,下班班——旋开门,旋开“现在”的门,感受饥饿和性欲、法律和暴力。我们在十字街头怅然若失,哼流行歌曲,吹口哨,强行攀爬街栏,看一场血腥电影……然后恍然大悟:正是中学历史课使我们远离了历史,疏远了那些大于我们生命的时间。历史忽然慈祥起来。我们为过去的事情简单排列一份时刻表,为古老的面容(通常是慈祥的面容)系上红领巾或黑色蝴蝶结,以表达我们的尊重和全部爱意。那一刻,我们的眼眶满含泪水。很不幸,那一刻也许我们才会发现:其实,我们对历史的脾性、气质竟一无所知。
人类对历史最直接最迫切的情感应该不是从教科书开始。课本堆积如山,但充满无数断点,它把历史分割成许多古怪的丧失乐趣的版块。我们凭借想象去残酷链接、自由组合。我相信历史受此腰斩、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