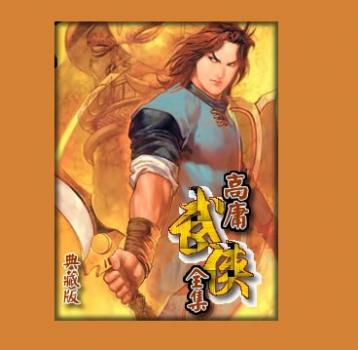寻找张爱玲-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喜欢到痴狂。喜欢到背井离乡地来上海。喜欢到穿越时空来寻她。喜欢到即使现在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仍不能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不过,也许这一幕本来也不是真实的,而只是我的一个美梦。
“有很多人说喜欢我的东西,但是姐姐你也这样说,我很开心。”她眨眨眼,带一点喜滋滋。
“崇拜你的人,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多。因为你对读者的影响,不仅在今世,要深远半个多世纪,甚至更远。”我看到桌子上堆积如小山的信件,“这些,都是崇拜者的信吧?”
“是呀,都来不及看。”爱玲又现出那种若有所思的神情,“姐姐,为什么你说每句话,都像预言似的。好像,你知道很多事,都是我们不知道的。如果你不是神仙,那么你就是天才,智者。”
我一愣,忽然想,或者所有的智者都是穿越时光的人吧?是因为预知预觉,所以才思维深广。再平凡的未来人,比起不平凡的旧时人,也还是高明的,因为,他已经“知道”。
佣人走来换茶,果然是奶酪红茶。
我不禁微笑,但接着听到禀报:“有位胡兰成先生求见。”
“胡兰成?”爱玲有些欢喜,“我听说过这个人呢。”
我大急,脱口说:“推掉他。”
“为什么?”爱玲微微惊讶,但立刻了然地说,“也是,我好不容易才见姐姐一次,不要让人打扰。”她回头吩咐,“跟客人说,我不在家。”
我松了一口气,但是很快又紧张起来。如果胡兰成不放弃呢?如果他再来第二次第三次,我难道能每次都守在这里阻挡他?
佣人下去片刻,执了一张纸片上来,说:“胡先生已经走了,他让我给您这个。”
我偷眼看上面的字迹,秀逸清隽,才情溢然纸上。古人说“字画同源”,从胡兰成这随手写下的这几行字里,我清楚地看到了画意,不禁百感交集。这的确是个不世出的才子,我有点遗憾没有见到他的真面目。历史的风云和政治的沧桑给这人涂抹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让我反而好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男子,会令张爱玲这样秀外慧中的奇女子倾心爱恋呢?
虽然,在时光隧道里旋转时,曾见过他一个背影,但那不能算是认识吧?他站在她的楼下按门铃,求她拨冗一见。而我,及时阻止了这一次会晤,并期望就此阻止以后所有的见面,最好,他和她,从来就不相识。
但是,爱玲反复看着那张字条,颇有些嗒然的意味。分明在为这次错过觉得惋惜。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他们甚至还没有见面呢,可我分明已经感到,有什么事情已经在他们之间悄悄地发生了。
“爱玲,我可不可以请求你一件事?”我望着她,迫切地请求,“可不可以答应我,不要见这个人。”
“我不是已经把他推了吗?”
“我不是说今天,是说以后。以后,也永远不要见这个人。”
“永远?你说得这样严重。”爱玲有些不安,“为什么会提这么奇怪的要求?你认识胡兰成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认识。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有害的人,对于你而言,他意味着灾难。你最好离他远远的,越远越好。”连我自己都觉得口吻如同巫师,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白,想了想,干脆直奔主题,“他替日本人做事,替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做事,他是一个……文化汉奸。”
“文化汉奸?可是他前不久还因为写文章断言日本必败南京政府必败,而被汪精卫关进牢里呢。”爱玲不以为然地反驳,“他是苏青的朋友。那次,我还和苏青一起去过周佛海家,想有什么法子可以救他呢。”
我又一次愣住。再度感慨自己对历史的贫乏。说实话,我只是一个张爱玲小说的痴迷读者,对于胡兰成的故事却所知甚浅,对上海孤岛时期的历史,也只有浮光掠影的了解。我同样说不清胡兰成究竟是哪一年入狱,哪一年出任汪政府的宣传次长,又具体地做过哪些伤天害理出卖国家民族的事,对于胡兰成的正面报道甚少,所有的传记故事里也都只是蜻蜓点水地提一句“文化汉奸”,历史的真相呢?真相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我所知晓的,只是他和张爱玲的这一段。以如此贫乏的了解,我对张爱玲的说服力实在是太力不从心了。
而且,24岁。再聪明的女子,在24岁的恋爱年龄里,也是愚蠢的。我也曾经24岁,清楚地了解那种叛逆的热情,对于自己未知事物的狂热的好奇,对于一个有神秘色彩的“坏男人”的身不由己的诱惑与向往。
关注一个人,先注意他的长处,但是真正爱上一个人,却往往是从爱上他的缺点开始的。
对于一个聪明而敏感的24岁少女而言,一个坏男人的“劣迹”往往是比着英雄人物更加让她着迷的。
命运的危机,已经隐隐在现,仿佛蛇的信子,“咝咝”地逼近。
我有种绝望的苍凉感。
“爱玲,”我困难地开口,“你写了《倾城之恋》,写了《沉香屑——第一炉香》,但是,你试过恋爱吗?”
“恋爱?”爱玲俏皮地笑,“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往往是第二轮的,总是先看到海的图画,后看到海;先看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情。”
我有些失落:“通常,你便是这样回答记者问的吧?”
她太聪明,太敏捷了,24岁的张爱玲,已经机智活跃远远超过我之所能,可是因为她还年轻,还没来得及真正体味爱情的得失与政治的易变,还在享受荣誉与赞美的包围,所以尚不能静下心来沉着地回答问题,不能正视自己的心。
一个人的智慧超过了年龄,就好像灵魂超越身体一样不能负荷,于人于己都是危险的。
我可以和8岁的张瑛无话不谈,却与24岁的张爱玲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隔阂。
而这种不和谐,张爱玲分明也是感觉到了的,她显得不安,于是顾左右而言他,站起身走到阳台上招呼说:“姐姐,你来看,哈同花园又在举行派对舞会呢。”
我点点头,也站起来走向阳台,一步踏出,忽然觉得晕眩,眼前金星乱冒,仿佛电梯失控的感觉,又仿佛楼下的万家灯火都飞起来一起缠住了我。
幸好只是一刹那,当眼前再度清明,我看到自己已经稳稳地站在阳台上,望下去,万家灯火都已复位,远处的霓虹招牌在滚动变换,画面是一张周润发的海报。我更加恍惚。发哥?他也到旧上海来了?他出演的《上海滩》,讲述的是张爱玲同时代的故事吧?难道因为一部电视剧,把他也送到这里来了?
“锦盒!锦盒!”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
阳台门再次推开,从房间里走出的竟是沈曹,他紧张地招呼:“锦盒,你觉得怎样?”
我怔忡地看着他,渐渐清醒过来,原来实验已经结束,可是,实验开始前我明明站在屋子中央的,怎么现在竟跑到阳台上来了?
楼下的巷道里不知从哪个角落依稀传来胡琴声,越发使一切显得如真如幻。
这回又出了新问题
沈曹十分困惑:“锦盒,这回又出了新问题。试验做到一半,你忽然站起来往外走,就像梦游一样,开门走了出来。我又害怕又担心,又不敢大声喊你,怕有什么后果。只得忙忙把时间掣扳回来,再出来找你。你感觉怎么样?”
“我……”我仍然沉在与张爱玲的谈话中不能还魂,“沈曹,如果你不扳动时间掣,我是不是就会一直留在那个时代?是不是就跟着那个时代的时间来生活了?那么我今天离开张家,明天还可以继续上门拜访,我可以一直和张爱玲交朋友,陪着她,看着她,不让她和胡兰成来往。”
“我不知道。不过如果是那样,你在这个时空的肉体,岂非就成了植物人?”
“植物人?会不会植物人的思想,就像我刚才一样,是走进了另一个时空,不愿意回来,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够回来,所以才变成植物人的呢?”
“这个……大概要属于医学范畴的问题了。植物人及梦游,在医学上还都是个未知数。人类大脑对于人类而言,还是个陌生的领域。”
我喟叹:“人类多么无奈,拿自己都没有办法,都无所了解,还奢谈什么改造世界呢?”
“好高骛远,原本是人类本性。”沈曹苦笑。
我们一时都不再说话,只并肩望向远方。
正是夜晚与白昼的交接处,人声与市声都浮在黄昏中,有种浮生若梦的不真实感。夕阳余晖给所有的一切都染上一层柔艳的光,绿的房屋,蓝的江水,绯红的行人和靓紫的车子,像童话里的城堡。
我忽然有些想哭。这阳台,张爱玲和胡兰成当年也一定曾经并肩站过,看过的吧?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虹橋書吧:book。hqdoor。 (TXT下載 免費在線看 更多更全盡在虹橋書吧)
那些往事,写在书上,写在风中,更写在这残阳余照的黄昏里。
张爱玲遇到胡兰成,顾锦盒爱上沈曹,一切,都是命运吧?谁知道这一刻我们看到的上海,是实景还是梦境?五十年前的月亮和五十年后的月亮是同一个月亮,五十年前的上海和五十年后的上海是相同的么?
沈曹说:“从黄浦江外滩起,由法大马路到静安寺,称为十里洋场。这房子,刚好是十里的边儿,也刚好在高处,可以看清十里洋场的全貌。”他指下去,“喏,那里是哈同花园,那里是起士林咖啡馆。”
起士林不是奥菲斯,顾锦盒不是白流苏,而沈曹,会不会是范柳原呢?
天色一层一层地暗下去,灯光一点一点地亮起来。
从这个角度望下去,整个城市就是由一点一点的灯光和一扇一扇的窗子组合而成,屋子是不动的灯光,车子是行动的灯光,闪闪烁烁,一起从人间游向天堂。
沈曹叹息又叹息,忽然说:“从小到大,我最怕的就是看到人家窗子里的灯光。因为我会觉得,那灯光背后,一定有个非常温暖快乐的家,而那些温暖和快乐,都不属于我。我非常嫉妒……”
我惊讶极了,惊讶到噤声。快乐的沈曹,优秀的沈曹,才华横溢名气斐然的沈曹,我一直以为他是童话中那种含银匙而生的天之骄子,从小到大整个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予取予求的。然而,他的童年,原来竟是如此的不快乐!难怪他潇洒的外表下,时时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阴郁。
少年时的伤,是内伤,没那么容易愈合。是那道看不见的伤痕和与生俱来的孤独感给了他迥异于人的独特魅力,
我没有发问。我知道他在诉说,也是在释放,我不想打断他,不想追问他。如果他信任我,如果他愿意说,他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的。
他沉默了好久,好像在清理自己的思绪,然后才又接着说下去:“小时候,我常常在这个时间偷偷跑出来,扔石头砸人家的窗子,有一次被人抓到了,是个大汉,抓我就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把我拎到半空。我怕得要死。但是这时候有一个女人从那里经过,她劝那个大汉把我放下来,并温柔地对我说:”小朋友,这么晚了,别在外面闯祸了,快回家吧,妈妈会找你的。‘我当时哭了。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很能打架,有时赢有时输,不管输赢,都会带一身伤,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是我从来没哭过。可是那天我哭了。我哭我自己没有家可以回,没有妈妈会找我……“
沈曹。哦沈曹,原来在你的风光背后,藏着的竟是这样的辛酸苦难。我的心,柔弱地疼了起来。眼中望出去的,不再是面前这个高大的沈曹,而是那个稚龄的到处砸人家玻璃的可怜的顽童,那个满心里只是仇恨和不甘心的的倔犟的孤儿。我的泪流下来。沈曹,我多么想疼惜你,补偿你以往所有的不快乐,所有的孤单与怨恨。
沈曹抬起头,看向深邃的夜空,用一种朝拜神明般的虔诚的语调继续说:“那个女人,非常地美丽。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懂,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她的长相,真的很美,很美,她穿着一条白裙子,那款式料子,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的笑容,就和天上的月亮一样,有一种柔和的光芒。她拉着我的手,问我:”你衣服上的这幅画,是谁画的?‘那时候,我总是喜欢在所有白色的东西上乱画,不管是白纸,白墙,还是白布。所以我自己的衣裳上,也都是画。她看着那些画,对我说:“你画得真好,比很多人都好。你将来会是一个很出色的人,有许多伟大的发明。所有认识你的人都会尊敬你,佩服你。你可不能因为打架闯祸就把自己毁了呀。’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曹是孤儿院院长的姓。我不知道生母为什么把我遗弃,襁褓里连一张简单的字条都没有。长到这么大,所有的人都歧视我,除了曹院长。但是即使是他,也没有对我说过这么温暖的话,鼓励我的话。那个美丽的女人,她使我相信,我是个好孩子,她给了我一个希望。在我心目中,她美如天仙,她的话,就是命运的明示……”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忽然有点酸酸的,听着沈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