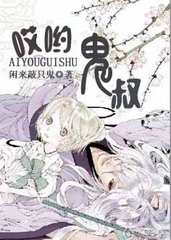一品宰相-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何元九会把今日的羞辱化作对陈四维一生的仇恨,陈四维注定了跟他就是一对冤家,现在想不去得罪他也晚了,开弓没有能收得回来的箭。
做人谁能做到一辈子一个人都不得罪?道不同则不相为谋,陈四维从来没想过跟所有人都过得去,没有敌人就是没有朋友,谁都不得罪就是没有立场。
王大人其实不想跟在后面看何元九的笑话,但是他若是不跟,何元九一定会以为他是怕丢人才没有跟着的。
也罢,他跟着还能多少照顾何元九一点,毕竟日后他们之间的来往不会少。大理寺和御史台就是一个锅里搅食的关系。
高敬元本来不想跟着,他没有看热闹的兴趣,他只觉得凑热闹很无聊,但是白景辰的兴致非常的高,不让白景辰跟着那是不可能的,他一蹦老高的尖叫。
所以高敬元也没有说什么,默默的跟在了后面。高敬元年事已高,他可不能跟别人一样在地上一步一步的走完整个汴梁城,他坐着八抬大轿慢慢的跟着。
何元九抱着上身穿着白色的中衣,下身穿着红色的裤子,脚上只有袜子没有鞋,满心的屈辱让他抬不起头来。
怀里抱着令人羡慕的官服、纱帽,手里拎着一双朝靴,每一步都走得跟挂牌游街一样的艰难。
走在他身后的陈四维‘扑哧’一下笑出了声,他忽然想起了南唐后主李煜的那句‘刬(音chan)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白景辰跟他并肩而行,自然要问他一句:“笑什么来?”
陈四维实话实说道:“想起一句词来‘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倒有三分应景。”
“噗!”白景辰指着何元九大笑道:“你可污死南唐后主了,李煜就跟这么个货约会?”
陈四维又没说小周后就长得跟何元九似的,白景辰放肆的大笑就像钢刀划过何元九的心,何元九心里恨恨的发誓,有朝一日他若得了势,说什么都不会放过陈四维和白景辰的。
“那就改改,‘刬袜步御街,手提上朝靴。’如何?”
“妙极!”白景辰竖起大拇指,诚心的夸赞陈四维,陈四维只淡淡的一笑,被小孩子夸又没什么可荣耀的。
何元九平素也不觉得这汴梁城的御街有多长,今天怎么感觉这么街长的像没有尽头似的?他心急火燎的恨不得一步走完御街的路,偏偏有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一个衣衫破烂的汉子忽然挤出人群,双手举着一条白布,屈膝跪倒在何元九面前。那白布上墨迹点点,显然是一条状子。
那汉子并不言语,只是举着布条跪在当街。高敬元吩咐停轿,命人上前去询问到底有何冤情,为什么不去当县告状,为何要拦轿喊冤。
告状这回事,州有州官,县有县官,越衙告状是很吃亏的,而且一般情况下越衙告状都没有人审理,都会被打回原郡去告。
在原住地告不了的,有人会上京告御状,一般都是拦轿喊冤的路子。平民百姓也不知道哪个官是管什么的,反正见轿子只要不是娶亲的花轿就跪下试试运气。
那汉子今天拦住了大理寺正卿王大人,算是老百姓能告到的最高级别法院了。但是王大人并没有理会他,倒是卸了任的高相爷派人过去问问情况。
王大人与何元九正想赶走那汉子,高敬人落了轿,他们也就没敢吱声。高相爷派来的人怎么也问不出一句话来。
那汉子只是执意的向前递状子,下人无奈只好接过状子转身向高相爷复命去了。白景辰上前问道:“你为何不说话?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有何冤情,你只管道来。”
陈四维伸手扯过白景辰:“不必多问,他不能说话。”
“他为何不能说话?”白景辰眨巴着大眼睛,满眼都是疑惑,那汉子嘴也没堵上,为什么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哑人不能说话,另一种是有难言之隐无法开口,他既然来告状就没什么不能说的了,想必是第一种情况。”
那汉子看着陈四维满眼是充满希望的光,他‘呜呜’的给陈四维磕头。
第19章 遗产争夺
第19章遗产争夺
高敬元看罢状子,只是一桩遗产纠纷的小案,没有什么血海冤仇也没有什么男盗女娼。
这样的小案自然没有人愿意理会,这根本不值得越衙审案。越衙审案肯定得罪当地县官,官字两张口,上口通下口,没有大事谁愿意给同朝为官的同僚找麻烦?
像这样的小案,就算你审的再清又有什么用?挣不来为民伸冤的好官声,更没有半个铜板的利益可图。
当地县官审理不清,上面的州官不肯受理,这汉子就这样到京城来告御状了。理民词本就不是丞相的事,更何况高相爷已经卸任五年了。
这状子若是交给王大人处理,那就跟扔河里了是一样的,拖拖也就过去了。高敬元不可能久居京城,也不可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去监督大理寺有没有受理此案。
做一辈子官的人看不得有民怨积累,这汉子是个哑巴,被兄嫂赶出家门没有一丝一毫的财产,若是没有人管他真的就活不下去了。
一个人若是被逼到生存都有着极大危机了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怕了,人性渐少兽性渐增,那就什么杀人越货的事都敢干了。
这件事往小里说就只是这个哑巴的死活,往大了说便是影响到社会治安的事。高敬元落了轿,家院上前打起轿帘。
那汉子眼巴巴的望着轿子向前跪爬了几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高敬元‘呯呯’的磕起了头。
高敬元一摆手,两个护卫上前搀起了那个汉子。高敬元手里握着状子,看了看白景辰和陈四维,问他们俩道:“依你们所见,此人所告何事?”
白景辰愣愣的看向那个汉子,哎我去,就这么街头碰上一个告状的,我就能看出他告什么?当我是神仙下凡啊?
陈四维也看向那个汉子,那人衣衫破烂不整洁,凌乱的不堪入目。衣服又脏又破,头发像乱草堆成的鸟窝,裤子膝盖以下跟灯笼穗似的。
一般的乞丐都比他好些,他脸不算脏,大概也是刚在河边洗过。陈四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微微点点头,基本上心中有数了。
王大人和何元九也气呼呼的望了这边一眼,一个死叫花子有什么好看的?这个高敬元真是多事,分明就是想拖延时间多在这街上停留一会儿罢了。
白景辰不说也得说,他必须回答老师的提问,于是他答道:“此人必有奇冤。”
“为何?”高敬元微眯着双眼,光说出个结果不行,还得说出你推断的过程,这才是他要考量的地方。
“看此人境遇不堪,千辛万苦拦轿告状,心中必有不平之事。”白景辰猜想来告状的都是为了争一口气,这个人都穷到没饭吃了,还要坚持告状足见心中怨气之大。
“嗯。”高敬元略点了点头,不管怎么说他算是动脑思考了。高敬元又亲切的唤了一声:“秉之,你如何看此事?”
“此人面带焦虑并无憎恨之色,想来他所告之事与平冤雪恨无关。他落魄如乞丐又是个哑人,足见他衣食无着又没有一技傍身。他有状子可见他求过人写状,他执意告状应该是为了谋个生路。告状能让他活命,必是他的财产为歹人所霸占,他想讨回自己的活命钱。”
陈四维又上下打量了那人一番,继续说道:“他应该不会写字,又口不能言,告的事情又小又难以沟通,因此县官不爱理,州官不愿管,他才乞讨进京来告御状。”
陈四维话未说完,那汉子鼻头一酸已然落下泪来,他‘呜呜’的冲着陈四维点头。
“不错。”高敬元满眼赞赏之色的点了点头:“此人叫姚二牛,家住在李家村。他父母过世之后,兄嫂霸占了所有的宅院和田产,把他赶出家门。他告到县里,他兄长说他是父母抱养来的,他根本不是姚家人,他没有证据,县官驳回了他的状子。”
“这还要证据?街坊邻里不能作证?”白景辰觉得这么桩小案实在容易得很,县官连这么点事都办不明白?
“姚大牛承认他在姚家长大,但这不等于说姚二牛就是姚家人啊。”高敬元淡然的看着白景辰,白景辰气得小脸涨红,显然他是毫无办法。
有办法就不必动怒,动怒的都是没有能力掌控局面。这件事说起来很滑稽,自己姓姚还需要证据?
打起官司来就是需要证据,他们姚家是后搬到李家村的。没有人能证明他姚二牛是在姚家出生的。如果他不是姚家血亲,他就没有资格继承姚家的遗产。
他们家是从哪儿搬到李家村的?姚大牛只说搬家时他年纪尚小,不记得祖籍何处。而他们的父母都过世了,根本无从查起。
高敬元看向陈四维,等待他的看法。陈四维刚才的分析清楚简练又贴合事实,高敬元越发笃定陈四维必是治国良材。
陈四维微微带笑躬身说道:“有两种方法可了结此案,一是滴骨验亲。掘开坟墓,劈开棺材,将他父母尸首去皮去肉,抽条骨头出来,待骨头干透,滴他的血试骨,血入骨为血肉至亲,反之则无亲。”
滴骨验亲,这在现代社会是没有问题的,为求真相解剖尸体是寻常便饭。在古代则万万行不通,古代重后事,讲究厚葬,死者为尊那是不能惊动的。
莫说为他一个哑巴,就是二十个哑巴也不行,动人家坟地是大忌,开棺还要将尸首去皮肉抽骨头,这样做恐怕会引起民愤,搞不好会造成小范围的****。
“第二种方法呢?”高敬元也知道滴骨验亲之法,但这个法子确实不能轻用。高敬元宁愿把自己的俸银拿出来资助一下这个哑巴,也不会用这个法子去断这桩官司。
“第二种方法倒也容易,只要略施小计即可,既能要回他应得的财产,又能小小的出口恶气。”陈四维向前一步对高敬元低声耳语了几句话,退回一步恭敬的说道:“学生只能想到此等拙计,不知可行否?”
第20章 扭你见官
第20章扭你见官
姚二牛的事很小,小到没有人愿意理会。姚二牛的事很麻烦,麻烦就在于只要姚大牛死不承认他是姚家人,那就谁都没有办法替姚二牛争取老人的遗产。
高敬元也没有想出太好的法子来解决这桩小案,他想到的无外乎就是给当地县官压力。
让县官追查出姚家祖籍在何处,从姚家其他的远亲近支中找到人证为姚二牛做证。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了,毕竟姚大牛不会主动承认姚二牛是他的胞弟。
高敬元借这件小事考验白景辰和陈四维的断案能力,也没指望他们能有什么奇谋良策,他们能中规中矩的回答问题,他也就知足了。
没想到陈四维立马就想到一条计,至于计好不好用要试过才知道,起码在理论上他的计谋有可行性,听起来合情合理,因此高敬元就把这件事交给陈四维处理了。
陈四维倒是没有什么事,闲着也是闲着,他不介意跑一趟。只是他跑到李家村也没有用啊,县官怎么审案轮得到他指手画脚吗?
“相爷”陈四维躬身一礼:“学生一介布衣,草民如何做得了县太爷的主?”
“秉之,你这是在抱怨吗?”高敬元似笑非笑的看着陈四维,你这个世子爷角色转变的适应性也太好了,才两三天的工夫,口口声声布衣草民,倒是半点世子爷的架子都看不到了。
高敬元哪里知道如今的陈四维就没享受过世子爷的待遇,他睁开眼睛就是爵位被褫夺。他从来也没摆过世子爷的架子,这样倒是挺好,他挺适应的,若是真让他做世子爷,他反倒需要适应一阵子才行。
“学生不敢。”陈四维就算傻也不可能当街抱怨,抱怨就是对朝廷不满,就是对圣上不满,那岂不就是花样作死?
“也罢。”高敬元把手里的折扇连同姚二牛的状子一并交给陈四维:“你带我的扇子前去,山泉县令自会听命于你的。”
“谢相爷。”陈四维双手接过状子和扇子,有了高相爷的信物那就好办得多了,满朝文武有几个人敢不给高相爷面子?
白景辰一看陈四维接到了出城办事的任务,羡慕的要哭,他出来转转都难比登天,哪里敢奢望能有机会出城?
陈四维爵位在身的时候是根本不可能出城的,候爷是至死都不得离开京城的特殊存在。
“我能去吗?我也想去。”白景辰激动的两只眼睛直冒光,就好像出城一趟能长多大的见识似的。
“好,你们一同去吧。”高敬元一句话,让白景辰欢喜的跳了起来。不像是让他去帮别人了断官司,倒像是让他去趋任作官一般。
陈四维和白景辰坐着同一辆车马大轿,直奔山泉县而去。姚二牛和保镖们坐着另一辆车,到了山泉县在离李家村十余里的地方姚二牛一个人下了车。
陈四维和白景辰大摇大摆的来到县衙,侍卫过去递上高相爷的扇子,门官拿着扇子进去复命。
过了片刻山泉县令动乐相迎,喜笑颜开的把陈四维和白景辰给迎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