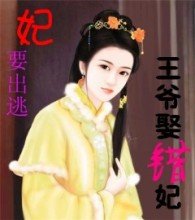你死,我活-第8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喊之中,未免就夹这不少呻吟哈乞之类的怪声。也有人乘机整顿松散的云鬓,搓揉酸麻的腰,伸伸僵硬的腿脚;也有人使劲吸两口鼻烟解乏,或是猛按太阳穴,擦些迷炼膏药;有的干脆头歪在地下打个盹,反正这一跪至少是一刻钟的时间,起来时自有旁人提醒。门口站着的管事太监那是早收了银钱,睁着的两眼只盯紧了锣,任这些小姐太太们撒野。
只苦了林大小姐,脚伤并未痊愈,稍站得长点就喊腿软,这一上午若不是身旁的几人连搀带扶甚至带背,早趴下了,要长跪那是说什么也不成。此刻干脆躺在地上,已是“一腔孤魂兮游四方,两眸寒星兮睁半只”,拿着手绢一个劲的抹汗,心中自是对那坐在金銮大轿里,被人到处抬着显威风的皇帝老子愤恨不已,念头转动,已盘算好了数十种要那皇帝老子好看的毒药,正想着要找谁做替死鬼。周围几个命妇人也各自脸青面黑的擦汗,那刘夫人乘前面的人直起腰再拜时,附在林芑云耳边低声道:“要不是今年要大庆皇上凯旋,本早就该完的。林丫头,你再撑一会?”
林芑云怎么擦也擦不完虚汗,干脆甩了手绢不擦了。她神色惨淡,额头鬓边的头发被汗湿,软软地贴在苍白的脸上,长一口短一口的出着气,道:“什么劳什子的祭天!哎……看来我今日小命是要断送在这此了……”
正说着,殿门处人影晃动,筌明术站起身来,扯着已近嘶哑的嗓子道:“起──。有旨:圣驾祭天,汝等立而从之,钦此。”念完圣旨,他转身要退出去,不料又跑又跪的忙了一上午,此刻一时脚软,被高高的门槛绊住,一个踉跄飞出门去,只听门外摔得山响,数名太监侍卫慌忙冲上去搀扶。林芑云听着声音,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撑地板直起身,看着门口,确信那人当真摔了,咯咯一笑。
忽感衣裳一紧,几个命妇人抢上来下死力将她扯倒,更有一人伸手捂住她的嘴。林芑云自知理亏,也不挣扎,一转眼,却见到殿中倒有一大半的人正掩嘴葫芦而笑,不禁大是高兴。
又折腾了一个多时辰,到了下午庚时,筌明术方一瘸一拐的进来,宣布:“圣上祭天礼毕,有旨:宣汝等入明云殿侍侯──”
这说是侍侯,其实只是几位娘娘出来接见一趟,完事后就可休息一阵了。众人差点欢声雷动,第一次心悦诚服的将头磕得山响,随即搀老扶幼,一起涌出殿门。林芑云总算松了一口气,但转念想到马上就要见到武约,心中说不出是怕是恨,刚两眼一翻想要装昏,几个命妇人左右一夹,不待她开口,已飞也似的跟着众人去了。
※※※
山林之中,风云变幻无常。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不知什么时候已浓云四合,寒风凛冽起来。天地似乎顷刻间就变了脸色。云雾在山间四处游走,一点一点,悄无声息之中将这林间空地严严实实围了起来。
阿柯穴道仍未解开,泥塑般力着,无力的看着四周再度变成白茫茫的一片。雾气很重,他的衣服很快便湿了,贴在肌肤上,再被寒风一吹,冻得他直哆嗦。
可还是动不了!阿柯鼻涕眼泪一起下来,拼命打着喷嚏,忽然觉得脸上一凉,接着又是重重的一下──这次是冰寒刺骨的水直接打在头上。
下雨了。
一滴接一滴,虽缓却重的打在阿柯头脸部分。周围的草地上也响起了一阵沙沙的声音。
冬季的雨,照理不该这么大才对啊。阿柯眼睛翻上去,才发觉原来是高大的树在做怪。那雨其实早已下了一阵,只是仍未枯黄的树冠接住了大部分雨水,汇集之后,再沿着叶片的边缘一颗颗的滴落。刚才还勉强能见的山头,此刻已彻底被纷纷扬扬的雨丝笼住,天地间除了眼前这块苍绿,便只剩下了白、灰、黑的单调而生硬的颜色,在刺骨的雨与肆虐的风中若有若无的舞动。
冷啊冷啊冷!
冷……
“啊……啊……”阿柯仰头,阔嘴微开,鼻子里奇痒难忍,全神贯注的等着那惊天动地的一下。
“阿柯……好冷啊。你进来啊。”林芑云没有鼻音的声音自车内传来。阿柯吁一口气,强忍下打喷嚏的欲望,抹了抹脸,低头钻进车中。只见林芑云裹着重重叠叠的被子、布料及能找到的衣服,只隐约露出口鼻,缩成一团的坐在大堆药材之中。她一见阿柯进来,伸出一只白得耀眼的手拍拍身旁。
“坐……啊。”
阿柯一屁股坐下,使劲揉鼻子。
“来……”林芑云用手捅捅他。
“恩?”阿柯一回头,见林芑云指指旁边一件衣服,便抓过来胡乱披在自己头上。
“喂……”林芑云继续用手捅捅他。
“干嘛?”
“替……替我搭上啊。”林芑云又指指自己脑门。
“哦……”阿柯伸伸舌头,半躬着给她搭好,再把她身上一些未盖好的被子拉好。干完这一切,又龟缩着坐到一边。
“喂。”林芑云脑袋蠕动,从厚厚的衣服被子后露眼睛来:“你不冷吗?”
阿柯使劲吸鼻子。
“哦,这样啊。”林芑云僵直着想了一下:“你靠过来点吧。”
阿柯挪挪屁股,靠林芑云近些。
“再过来点啊。”
阿柯再挪挪。已经要靠到林芑云身体了。
“再过来点。”林芑云一双清澈的眸子在暗中隐隐发光。
“哦。”阿柯扭扭身子。
在这个位置,已经可以很清楚地闻到林芑云身上那股淡淡的草药的馨香。阿柯通常以此为界,阻止自己再靠近。
林芑云不再说话,却低低的叹了口气。阿柯耳尖听见了,心中不明所以,又偷偷往外挪了挪。他看着外面稀稀沥沥的秋雨,看着似水墨淡染的画卷般败叶枯枝的森林,看着那顺着篷顶一滴一滴落下的水珠,随着风斜斜地溅落在车前的横木上,破碎成更小的水珠,融入阴冷潮湿的空气中。那寒润的泥地上便升起了雾,顺着草黄露莹的林间空地悄然弥漫开去。
“阿柯,我冷。”林芑云也使劲的吸鼻子:“还有多久才能到下一个集市?”
“快了……明天吧。”阿柯拿不稳。
“可你昨天就说过明天了,明天到底是哪一天?”
“这……这不是雨淋坏了路,把车子陷住了吗?”阿柯翻动面前的包袱,一边道:“这里还有一块饼,你吃点吧。”
“不吃!哈──啾!哈──啾!呜呜呜……帮我一下!”
阿柯忙转身,帮林芑云擦拭打得到处都是的鼻涕,一面道:“你还冷啊?再喝点药吧?”
林芑云满脸飞红,脑袋缩得更进去,就只剩张嘴露在外面,嘶嘶的吸气,道:“没……没有了。那药再过一个时辰才能喝……你别老看着我啊!”
阿柯哦了一声转过去,继续看车外的秋雨。他一边盘算一边说:“到、到了洛阳就好了。洛阳地方大,人也多,我们卖药赚点钱,就买辆新的牛车,不会再这么漏风漏雨进来。那儿也比这里暖和,你也不必再病了。”
突然一双柔软温暖的手自背后绕过来,将他轻轻环在臂弯内。林芑云将黔首埋在阿柯惊慌的背上,低声道:“傻瓜,我身子弱,要生病,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你靠着我,就不冷了……”
阿柯头中嗡的一响,只觉背上靠着的人似火一般,烫得他几乎脑门冒汗。但他不敢稍动,只暗暗用力挺直腰身,让林芑云靠得舒适一点。
“阿柯……你干嘛在抖啊?”良久,林芑云模糊的问道。
“啊?我、我、我没有抖啊?”阿柯愣了片刻,突然道:“我没抖,是你在抖!”
身后“咕咚”一声,林芑云滚落下去,露出被子的通红的脸上全是虚汗,已然昏厥过去……
“啊!”阿柯手往前一伸,突然身子剧震,一步跨了出去──原来是穴道终于解开了。他站了几个时辰,脚下酸软,一个踉跄摔在泥水中。冰寒刺骨的水一激,阿柯立刻又跳起来,一抹脸上的雨水,呆了一呆,“呵呵呵”地叫着往车子冲去。刚冲到车前,却又突然一个急刹,险些再摔一交。他扶着车辕想:“那丫头会不会再给我一下?”但此刻被雨水打湿的衣服似已将全身的热气都耗尽了,连肚府之中都是冰冷一片,也顾不了许多,一翻身爬上去。
“喂喂喂!别、别打,别打!我绝不碰你一根头发!你再来,我……我不客气了!”阿柯闭着眼弓着身捂着脑袋一阵乱喊,想来个先声夺人,同时一只脚踩在外面的车辕上,预备随时逃命。
过了半响,并无一人应声。
阿柯睁眼一看,吓了一跳──那少女斜着靠在车篷上,早已昏死过去,胸口衣襟敞开,那晚阿柯给她包着的布也被松开了,胡乱的搭在胸前,血流了一身。想是她自己给自己换药,但伤重乏力,终于晕倒。阿柯慌忙凑上前去,先摸摸她的额头──似火烧一般,再将那布扯掉──果然,伤口处已溃烂老大一块。阿柯冷汗一下袭上头顶,他知道,这条弱小的生命已在须臾之间。
阿柯环视左右,除了那瓶什么归元散,并无一可用之药。他略一迟疑,猛的一咬牙,似下了决心,伸手入怀掏出火折子,一怔,失望地丢在地下──那火折子已被雨水浸湿了。他心中乱跳,想了一想,将那柄短剑咬在口中,跳下车,往早上烧的那堆火跑去。那火此刻早熄了,只剩一屡若有若无的烟尘仍在细雨朦朦中低回萦绕。阿柯不顾一切跪在冰冷的泥地上,小心用手拨开湿灰,露出下面略干的一点碳。他轻轻的吹,一口接一口,直吹得脸颊发酸也不停下。
好一会儿,忽然一粒火星一跳,只晃得一晃便即消失。但阿柯心中却因这一火星重新然起希望。他继续小心的吹,待得有几块碳终于渐渐变红,他再加大力气吹,一边躬起身子,遮住这保命的火种。过了片刻,一股青烟冒了起来──火又重新然起来了。阿柯小心地用碳灰将微弱的火苗围起来。他站起来四处打量──到处是阴湿的雨,阴湿的雾,再难找一块干的柴了。他转了两圈,忽地一拍脑袋,飞奔到车驾前,一弯身钻入车底,拿剑又捅又砍,弄下老大一堆干柴,在车底用剑细细劈了,再拿到火边支起来。
火苗婉转盘旋,时熄时燃,好象也在回避这阴沈的天。阿柯拼了命又吹又赶,前后折腾了小半个时辰,全身湿透,也不知是汗是雨,那火终于再度熊熊燃烧起来。他喜得几乎忘了寒冷,双手擎剑在火上烤。待那剑烤得一侧通红,才转身向车驾快步走去。
他刚一登上车,那少女一动,已然醒了过来,模糊中只见阿柯拿着柄红红的东西正迅速靠近,不觉一惊,再低头一看,自己胸前大片肌肤都裸露在外,只道阿柯对自己又做了什么,惊呼一声。但她伤重之下,连抬手的力气都使不出来,只觉四周事物在眼前不住旋转,泪水夺旷而出,再也看不分明,哭道:“小贼,你……你杀了我吧……啊!”突感伤口处一阵撕裂般的剧痛,跟着是一阵火烫,直烫得她五脏六府都似烧起来一般。这一下痛楚非同小可,脑中嗡的一响,几乎要炸裂开来一般。
“啊呀!”
阿柯也一声惨叫,那少女的手指死死掐住他的手臂,长长的指甲直透肉中,怎么甩也甩不掉。阿柯也没时间来扯她的手,强忍痛楚,用剑沿着她锁骨下的伤口继续剜,要把那些烂掉的肉尽数除去。少女被这撕心裂肺的痛楚折磨得几欲昏死,好在也明白过来,知道自己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她咬得下唇一片血肉模糊,手亦越掐越紧,几乎要捏断阿柯的骨头,却拼命硬挺着胸,让阿柯一剑剑切下去。阿柯咬着牙关,勉强道:“丫头……撑住啊……”下手愈来愈快,切得好几处都露出白骨来。约莫一忽儿──阿柯觉得已过了三百年──终于做完,手一扬将剑甩得老远,一把抢过归元散的药瓶,管它多少,一股脑全洒在伤口处。
阿柯沈声道:“放手!我替你裹伤!”
少女不放,一双大大的眼睛瞪得浑圆,透过车内隐约的白烟,死死盯着阿柯──那羞愤痛楚之情,若是寻常间见了,胆小一点的不定得吓死。
阿柯喝道:“放手!”用手拼命掰那只冰冷的小手。但那手似铁铸一般,纹丝不动,一丝丝的血顺着阿柯的手臂流下。
阿柯吐一口气,右手颤抖着四下里乱摸,摸到一根那少女准备打他的木头,掂一掂,一棒敲在那少女头上。
不放!
再敲!
还是不放!
那少女泪如泉涌,全身抖得似筛子一般,却怎么也放不开手。
阿柯不知为何,眼泪也一下涌出眼眶。他颤声道:“放了啊丫头,别怕死不了的……”牙关一咬,重重一棒下去,那少女眼睛一翻,终于晕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