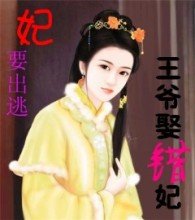你死,我活-第10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背背黑锅,也算为刘大哥报了几分仇。幸好沙老大此时不在,否则穿帮穿定了。”
司马南风瞳孔急缩,道:“铁杖老怪物?他为何又没有杀你?”
阿柯还来不及答,林芑云抢著道:“啊,铁杖老怪,我也听过的……此人生性狡诈,想来也明白这个道理,是以故意不杀阿柯,让你们跟著阿柯屁股走,还搞得江湖上人尽皆知,他自己一早跑了。”
司马南风目眶崩裂,咬牙道:“好个老怪物,老子跟你没完!”
苦真和尚一拱手道:“今日若非姑娘,和尚也不知能不能走出这楼。若有再会之日,只希望与姑娘是友非敌。告辞了。我向北走。”一转身翻出窗口,在一排青瓦屋顶上疾驰而去,转过几座楼亭不见了。
慕容荃生怕晚一刻出去就被别人抢了先,忙道:“后会有期,告辞!我走东面!”跳出窗口走了。
司马南风神情古怪地看看尹萱,又看看阿柯,道:“今日老夫给林姑娘面子,管她是救你们也好杀你们也好,总之以后不要叫老夫再看到你们!林姑娘,告辞!我走西面。”他讲究的是从容,当下昂然从楼梯下楼,径直去了。
梅雨村道:“还是苦真秃头说的好,林姑娘算无遗策,见识过人,下次见面,真的希望是友非敌。我们几个一走了之,若姑娘落在最后,嫌疑总是最大,可不大好。不如姑娘先行一步,在下殿后。”
林芑云嫣然一笑,道:“梅公子果然艺高胆大。这份心意,小女子著实感激不尽。不过小女子自有脱身之法,倒是梅公子身在异地,总不太方便,还是先行一步罢。”
梅雨村仰天大笑,道:“今日识得林姑娘,平生无憾!不知以后姑娘到江南来玩,在下可否一尽地主之谊?”
林芑云笑道:“江南梅庄的霜雪玉梅酒天下一绝,小女子又怎肯错过?”
梅雨村道:“好!在下必定请姑娘尝最好的藏酒。家兄不干,在下就偷出来,哈哈哈哈!”说到最后一句,豪气干云,长笑声中,身子翩然飞下楼去,却直落入河里早已等候的一叶扁舟内。只听桨声阵阵,和著他的吟唱传上楼来:
“岱北鸾骖至,辽西鹤骑旋。
终希脱尘网,连翼下芝田。”——
第二章只言惑青衣
不一会儿,山南西道道府刘大人并利州州台李大人,以及五位骑著高头大马的五品军爷,领著二百多号人,浩浩荡荡自城门开来,一声令下,赶得围在舞凤楼旁的一干江湖人士鸡飞狗跳,连沿街所有店铺都被勒令关门闭户,船只停航,小贩收摊,行人回避。总之,顷刻之间,舞凤楼周围几里之内外人畜不留,杂草不生。这个时候若有胆大妄为的人从门缝里偷看——只看得到一群群一排排面目狰狞的大兵;但若从远处的山上偷看,便可看见几乘大轿被抬进门里,为此还砸了舞凤楼的金装门框。不一会儿,那些轿子又被抬了出来,道府大人在前开道,州台大人殿后压阵,两百多士卒举著长枪护驾,锣鼓喧天,大摇大摆的抬进了道府大院。
对于普通老百姓们来说,这种事根本不值一提。或者说,这些高高在上的事,本就不是该他们管的。只有江湖侠客们一个个摇头叹息不已——最后出来的人居然有如此官府背景,哪还有什么指望?也有胆大包天深夜前去打探的,天一亮,一根铁链串了十七、八个鼻青脸肿、脚断手折的汉子,发到军前劳役。其情之惨,让观者心惊,闻者胆寒。于是乎骑马北上者有之,坐船南下者有之,东进有之,西去亦有之。此是后话。
却说林芑云等人从舞凤楼下来时,尹萱兀自不信已经死里逃生,再见到大群气势汹汹的官兵,吓得不知所措,拉著阿柯的衣袖不放。林芑云笑得无比欢畅,说是好久没这么痛快过了。但是,她又煞有其事的补充说,善后的事要做好了才行。于是硬拉了李洛与她同坐一轿。阿柯看她几眼,欲言又止,只得与尹萱坐了另一轿。
待得轿子一起,外面的锣鼓一响,刚才还唧唧喳喳的林芑云立时不说话了。她拿了丝巾掩住嘴,将窗帘拉开一条逢,百无聊赖地往外面看。窗外的光线照进来,在她脸上映出极亮的一道线,这亮线划过她的眼睛时,那瞳孔就一缩,幻化出猫眼一般的琉璃色。她这个沉默的样子让人想起闺隽里的薄胎细纹碎玉花瓶,沾不得分毫浮尘,经不起任何颠簸,只能小心地放在几上,浸一支檀香,默默地在远处观赏。
李洛盯视良久,终于忍不住道:“其实如果你想……”
林芑云一口截断他道:“是,我是想。我早想到江南去玩玩了。这里天气太坏,十几天见不到阳光,城镇又小又冷清,哎,憋都憋死了。我有……十年没品过君山的茶了罢?”
李洛咽了口气,道:“其实我是想……”
“我知道你想什么。”林芑云一本正经地坐直,严肃地道:“那晚皇室宴会,我回来得很晚,你记得么?就是那次,我一个人走啊走啊,迷了路,却遇见皇上在亭中观雪,这才认识的。”
“我不是问这个,我只是想说你……”
“啊,是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皇上呢。他说他叫雪月明,哼,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名字呢?还说什么雪似胡抄暗,冰如汉月明——分明是哄我罢了。于是我也说我是凤来仪——凤皇佳可食,一去一来仪——很合我的品位嘛,对不对?”
“我是说阿柯!”李洛终于吼出来,道:“你不是很想……”
但是他说不下去。因为林芑云一双冰冷的手已掩上他的嘴唇,她神情自若,但脸色白得几乎透明,有一种绷紧的感觉通过她的手迅速传到李洛身上。绷紧,那是种把一切都死死压紧,封住,不留出一丝一毫的空间,连念头都逃不出生天的紧迫。
她只是淡淡地道:“别说。”
李洛慢慢伸出手,轻轻握住她的小手。林芑云浑身颤了一下,却没有挣脱。良久,只听见李洛也淡淡地道:“若是有人欺负你,我就要他的命。”
一行人回到府中,林芑云早瞧出尹萱体虚病弱,问明原由,自将她带到屋中治疗。阿柯呆坐在厅中,脑袋里尚是一片混乱,只觉今日之事实在太过奇怪。本来自己好好的进城,突然间就一步踏入陷阱;正在四面楚歌之时,那多日不见却无时或忘的林芑云从天而降,也不知使了什么手段,居然将冤家对头李洛收服,更添几位高手,好整以暇的凭栏而依,临风而笑,顷刻间,围追自己的众多江湖高手们就在自己面前土崩瓦解,打得血流成河;待得最后几个人正要发威,林芑云恩威并施,晓以厉害,竟然人人口中称善,施施然而去。面对从未有过的困境,自己却一剑未出,一人未杀就此脱险,实在是平生仅见。这之后,自己这“图谋行刺朝廷重臣”的通缉要犯,大摇大摆的坐上官府大轿,前涌后呼地抬进道府大院内,坐的是安南都护府(今越南)进贡的盘虎根雕朱漆大座,喝的是离此两百里的双角山中绿珠泉水泡的金井枫,陪坐的是面无表情的当今御前红人左飞卫将军李洛。阿柯只感到全身每一个毛孔都似被胶封住了一般,浑身不自在,屁股在椅子磨来磨去,也不敢抬头随便张望,屏息静气,并膝垂手,生怕有一丝不规矩的地方,让人给看扁了。
铜滴漏慢慢的漏著,阿柯的心七上八下。也不知坐了多久,已觉得腰背酸痛难忍,偷眼看一旁的李洛,却见他仍是挺胸抬头的正襟危坐,好似尊泥塑。阿柯暗自纳罕,想:“难道当官的先得过坐功这一关?我又不想做官,那么歪一下大概也无妨罢?”便略歇著坐一点,过一会儿又再歪一点,再靠一下扶手,再蜷一下腿……到后来乾脆缩进大座里,全身放软了,舒服得几乎呻吟出来。
李洛有一口没一口的喝著茶,对旁边偷偷乱动的阿柯视而不见。过了好一阵,他放了杯子,对著空旷的屋顶道:“十日之内,我听林姑娘的吩咐,绝不动这小子一根头发。若有违背,天可罚之。”
阿柯小心脏扑通一跳,坐直了身子,却仍有些将信将疑地问:“是、是么?”
李洛哼了一声,傲然道:“我李洛对林姑娘素来报之以诚,不象有些人,生在福中,却狠心辜负人家一片心意!”
阿柯茫然道:“啊……哪些人?”
李洛大怒,一摔手飞过一只茶杯,来势极猛,阿柯“啊哟”一声,抱头躲避,然而仍被四溅的茶水湿了一身。他跳起身来,就要飞奔出门,有多远逃多远,却见李洛一闪身已站到门边,冷冷地道:“你想到哪里去?林姑娘还未准许,你要出这门,只有横著抬出去!”右手伸出,食指向他胸前穴位戳来。阿柯见他动手,亦不多言,以手为剑,切他手腕。
两人刚要交手,忽听门厅处有人大叫道:“住手!”正是林芑云的声音。
李洛闻言,说停便停。阿柯收扎不住,险些冲进他怀里去。只听林芑云怒道:“叫你在外好好坐著也不行么,非要动手!李公子,麻烦你先出去吧,我有话与阿柯说。”
李洛对阿柯怒目而视,眼神几可杀人,向他传达一个“千万别犯在我手里”的意思后,转身出门,反手关上房门。
阿柯最怕林芑云发怒,呆站在门前,耳边听见林芑云缓缓步到桌前坐下,良久,方柔声道:“过来坐罢,我不生气了。”
阿柯小心翼翼坐回座位,不敢看林芑云的脸色,问道:“你……你脚怎么好了?”
林芑云无声的一笑,道:“难为你还记得。这是道大师替我运功治疗的。”
阿柯道:“啊,道亦僧……原来你、你找到他了,那就好了。”
林芑云道:“是。这些日子来多亏有他和铛铛妹妹陪著我,否则……我一个人在洛阳,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阿柯摇头晃脑地道:“原来道大师真会医术。那日在林中,怎么反被你驳倒?”
林芑云白他一眼,道:“这治疗之法我早就知道了,只是需要一位既通医术又内力淳厚的人协助我打通封闭的脉络而已。道大师人看起来随随便便,但一身正宗内力确是非同小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能这么快恢复。只是中毒已久,要想完全治愈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现在多走一会儿就不行了。”
阿柯被林芑云白了一眼,顿觉通体舒坦,顺手把弄著白玉茶杯,又道:“武约没难为你吧?那一天他们设下埋伏,要杀、杀我灭口,我就猜到他们是想留住你了。”
林芑云深深看他一眼,见他的侧面比以前又消瘦了许多,但也刚毅了几分;唇上短短的胡碴浓密了许多,头发更显凌乱,像是多日未有打理;眼神依旧飘忽不定,但忽而的一凝,便很有些慑人的气势。心中那个懵懂稚气的少年,忽忽数月,骤然间仿佛已长大了几岁,林芑云心中不知是喜是悲,低声道:“是我连累了你。”
阿柯啊了一声,跳起来双手乱挥,叫道:“不、不、不……不是这么回事!我、我……我并不是说……不是连累不连累,我是说……哎,怎么说呢?”一个劲的搔脑袋。
林芑云见到他那熟悉的焦急尴尬的神情,那段共同经过的难忘岁月仿佛一瞬间又回到眼前,心中一暖,浅浅笑道:“你别急啊。我……我知道你的心思。”
阿柯一拍手,指著她道:“啊!是吧。我就说你能明白的……你明白就好。”
林芑云点头道:“我明白的。哎,你的毒没有再犯么?你又是在哪里惹上这么多麻烦的?”
阿柯舔舔嘴唇,缩回椅子,长叹一声——居然也透著些许似模似样的沧桑,长话短说,将当日怎样与可可逃出洛阳,如何在林中与段念夫妇相遇,又如何见到辩机和尚,最后辩机又是如何教他《海若经络》内功心法的。他口齿不清,语焉不详,记得又颠三倒四,常常说到后面,忽然说到之前;又或猛的记起忘了什么,费力解释。好在林芑云早熟知他的这些毛病,一边听,一边指正他的毛病,帮他纠正错误,理清思路。若是李洛在此,多半听得莫名其妙,林芑云却听得津津有味,时而紧张,时而释然,时而扼腕叹息段念与段夫人的不幸,时而又对沙老大的狼狈大笑不已。她听到《海若经络》四个字时,不觉凛然,道:“我听爷爷也提到过此书,据传里面记载的内容极之深奥,非常人能洞悉,确是一部奇书。只不过百多年前即已失传,这位辩机和尚竟能习到这门内功,不知是哪里的高人。你把手伸来我瞧瞧。”
阿柯挽起袖子,让她探脉。林芑云闭著眼,把了半天脉,又让阿柯伸头过来看。她一边看一边道:“你的听宫穴倒是不再颤动,颧鹘穴略有温火,不过也许只是体内温寒所致。后溪、阳谷、小海这一路看起来是被那股内力压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