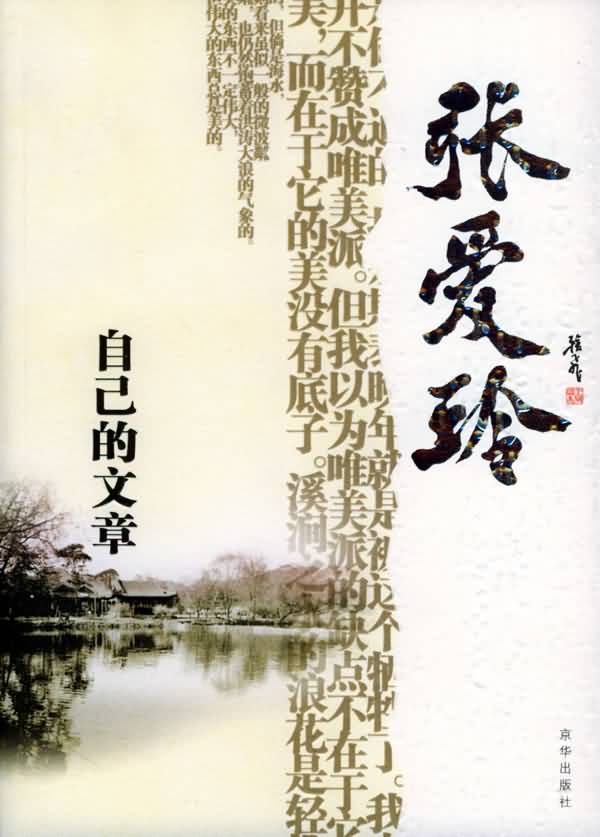叶紫文集-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还脱不下袍儿。这,莫非是又要和去年一样吗?”云普婶没有回答,在忙着给怀中的四喜儿喂奶。天气也真太使人着急了,立春后一连下了三十多天雨没有停住过,人们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往常都是这样;春分奇冷,一定又是一个大水年岁。“天啦!要又是一样,……”云普叔又掉头望着天,将手中的一根旱烟管,不住地在石阶级上磕动。“该不会吧!”云普婶歇了半天功夫,随便地说着,脸还是朝着怀中的孩子。“怎么不会呢?春分过了,还有这样的寒!庚午年,甲子年,丙寅年的春天,不都是有这样冷吗?况且,今年的天老爷是要大收人的!”云普叔反对妻子的那种随便的答复,好象今年的命运,已经早在这儿卜定了一般。关帝爷爷的灵签上曾明白地说过了:今年的人,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的!烙印地云普叔脑筋中的许多痛苦的印象,凑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他记得:甲子年他吃过野菜拌山芋,一天只能捞到一顿。乙丑年刚刚好一点,丙寅年又喊吃树根。庚午辛未年他还年少,好象并不十分痛苦。只有去年,我的天呀!云普叔简直是不能作想啊!去年,云普叔一家有八口人吃茶饭,今年就只剩了六个:除了云普婶外,大儿子立秋二十岁,这是云普叔的左右手!二儿子少普十四岁,也已经开始在田里和云普叔帮忙。女儿英英十岁,她能跟着妈妈打斗笠。最小的一个便是四喜儿,还在吃奶。云普爷爷和一个六岁的虎儿,是去年八月吃观音粉①吃死的。这样一个热闹的家庭中,吃呆饭的人一个也没有,谁不说云普叔会发财呢?是的,云普叔原是应该发财的人,就因为运气太不好了,连年的兵灾水旱,才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示弱于人哩!①观音粉:一种白色的细泥土。——原注。去年,这可怕的去年啦!云普叔自己也如同过着梦境一样。为了连年的兵灾水旱,他不得不拼命地加种了何八爷七亩田,希图有个转运。自己家里有人手,多种一亩田,就多一亩田的好处;除纳去何八爷的租谷以外,多少总还有几粒好捞的。能吃一两年饱饭,还怕弄不发财吗?主意打定后,云普叔就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所屋子,来租何八爷的田种。二月里,云普叔全家搬进到这祠堂里来了,替祖宗打扫灵牌,春秋二祭还有一串钱的赏格。自家的屋子,也是由何八爷承受的。七亩田的租谷仍照旧规,三七开,云普叔能有三成好到手,便算很不错的。起先,真使云普叔欢喜。虽然和儿子费了很多力气,然而禾苗很好,雨水也极调和,只要照拂得法,收获下来,便什么都不成问题了。看看他,禾苗都发了根,涨了苞,很快地便标线①了,再刮二三日老南风,就可以看到黄金色的谷子摆在眼前。云普叔真是喜欢啊!这不是他日夜辛劳的代价吗?①标线:即稻的穗子从禾苞中长出来。——原注。他几乎欢喜得发跳起来,就在他将要发跳的第二天哩,天老爷忽然翻了脸。蛋大的雨点由西南方直向这垄上扑来,只有半天功夫,池塘里的水都起膨胀。云普叔立刻就感受着有些不安似的,恐怕这好好的稻花,都要被雨点打落,而影响到收成的不丰。午后,雨渐渐地停住了,云普叔的心中,象放落一副千斤担子般的轻快。半晚上,天上忽然黑得伸手看不见自家的拳头,四面的锣声,象雷一般地轰着,人声一片一片地喧嚷奔驰,风刮得呼呼地叫吼。云普叔知道又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变,急急忙忙地叫起了立秋儿,由黑暗中向着锣声的响处飞跑。路上,云普叔到了小二疤子,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齐暴涨了三丈多,曹家垄四围的堤口,都危险得厉害,锣声是喊动大家去挡堤的。云普叔吃了一惊,黑夜里陡涨几支水,是四五十年来少见的怪事。他慌了张,锣声越响越厉害,他的脚步也越加乱了。天黑路滑,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是立秋扶住他跑的,还不到三步,就听到一声天崩地裂的震响,云普叔的脚象弹棉花絮一般战动起来。很快地,如万马奔驰般的浪涛向他们扑来了。立秋急急地背起云普叔返身就逃。刚才回奔到自己的头门口,水已经流到了阶下。新渡口的堤溃开了三十几丈宽一个角,曹家垄满烷子的黄金都化成了水。于是云普叔发了疯。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一家生命的泉源,都在这一刹那间被水冲毁得干干净净了。他终天的狂呼着:“天哪!我粒粒的黄金都化成了水!”现在,云普叔又见到了这样希奇的征兆,他怎么不心急呢?去年五月到现在,他还没有吃饱过一顿干饭。六月初水就退了,垄上的饥民想联合出门去讨米,刚刚走到宁乡就被认作了乱党赶出境来,以后就半步大门都不许出。县城里据说领了三万洋钱的赈款,乡下没有看见发下一颗米花儿。何八爷从省里贩了七十担大豆子回垄济急,云普叔只借到五斗,价钱是六块三,月息四分五。一家有八口人,后来连青草都吃光了,实在不能再挨下去,才跪在何八爷面前加借了三斗豆子。八月里华家堤掘出了观音粉,垄上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跑去挖来吃,云普叔带着立秋挖了两三担回来,吃不到两天,云普爷爷升天了,临走还带去了一个六岁的虎儿。后来,垄上的饥民都走到死亡线上了,才由何八爷代替饥民向县太爷担保不会变乱党,再三地求了几张护照,分途逃出境来。云普叔一家被送到一个热闹的城里,过了四个月的饥民生活,年底才回家来。这都是去年啦!苦,又有谁能知道呢?这时候,垄上的人都靠着临时编些斗笠过活。下雨,一天每人能编十只斗笠,就可以捞到两顿稀饭钱。云普叔和立秋剖蔑;少普、云普婶和英英日夜不停地赶着编。编呀,尽量地编呀!不编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是有命挨到秋收。春雨一连下了三十多天了,天气又寒冷得这么厉害,满垄上的人,都怀着一种同样恐怖的心境。“天啦!今年难道又要和去年一样吗?……”二天毕竟是睛和了,人们从蛰伏了三十多天的阴郁底屋子里爬出来。菜青色的脸膛,都挂上了欣欢的微笑。孩子们一件一伴地跑来跑去,赤着脚在太阳底下踏着软泥儿耍着。水全是那样满满的,无论池塘里、田中或是湖上。遍地都长满了嫩草,没有晒干的雨点挂在草叶上,象一颗一颗的小银珠。杨柳发芽了,在久雨初晴的春色中,这垄上,是一切都有了欣欣开展的气象。人们立时开始喧嚷着,活跃着。展眼望去,田畦上时常有赤脚来往的人群,徘徊观望;三个五个一伙的,指指池塘又查查决口,谈这谈那,都准备着,计划着,应该如何动手做他们在这个时节里的功夫。斗笠的销路突然地阻塞了,为了到处都天晴。男子们白天不能在家里刮蔑,妇人和孩子的工作,也无形中松散下来,生活的紧箍咒,随即把这整个的农村牢牢地套住。努力地下田去工作吧,工作时原不能不吃饭啊!镇日祈祷着天晴的云普叔,他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然而微笑是很吝啬地只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拂了一下,便随着紧蹙的眉尖消逝了。棉袍还是不能脱下,太阳晒在他的身上,只有那么一点儿辣辣的难熬,他没有放在心上。他只是担心着,怎样地才能够渡过这紧急的难关——饱饱地捞两餐白米饭吃了,补一补精神,好到田中去。斗笠的销路没有了,眼前的稀饭就起了巨大的恐慌,于是云普叔更加焦急。他知道他的命苦,生下来就没有过过一时舒服的生涯。今年五十岁了,苦头总算吃过不少,好的日子却还没有看见过。算八字的先生都说:他的老晚景很好;然而那是五十五岁以后的事情,他总不能十分相信。两个儿子又都不懂事,处在这样大劫数的年头,要独立支持这么一家六口,那是如何困难的事情啊!“总得想个办法啦!”云普叔从来没有自馁过,每每到了这样的难关,他就把这句话不住地在自己的脑际里打磨旋,有时竟能想到一些很好的办法。今天,他知道这个难关更紧了,于是又把这句话儿运用到脑里去旋转。“何八爷,李三爷,陈老爷……”他一步一步地在戏台下踱来踱去,这些人的影子,一个个地浮上他的脑中。然而那都是一些极难看的面孔,每一个都会使他感受到异样的不安和恐惧。他只好摇头叹气地把这些人统统丢开,将念头转向另一方面去。猛然地,他却想到了一个例外的人:“立秋,他现在就跑到玉五叔家中去看看好吗?”“去做什么呢,爹?”立秋坐在门槛边剖蔑,漫无意识地反问他。“明天的日脚很好啦!人家都准备下田了,我们也应当跟着动手。头一天做功夫,总得饱饱吃一餐,兆头来能好一些,做起功夫来也比较起劲。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了米,所以……”“我看玉五叔也不见得有办法吧!”“那末,你去看看也不要紧的娄!”“这又何必空跑一趟呢?我看他们的情形,也并不见得比我们要好!”“你总欢喜和老子对来!你能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我是叫你去一趟呀!”“这是实在的事实啊!爹,他们恐怕比我们还要困难哩!”“废话!”近来云普叔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儿子变差了,什么事情都欢喜和他抬杠。为了家中的一些琐事,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龃龉。儿子总是那样懒懒地不肯做事,有时候简直是个忤逆的,不孝的东西!玉五叔的家中并不见得会和自己一般地没有办法。因为除了玉五婶以外,玉五叔的家中没有第三个要吃闲饭的人。去年全垄上的灾民都出去逃难了,王五叔就没有同去,独自不动地支持了一家两口的生存。而且,也从来没有看见他向人家借贷过。大前天在渡口上曹炳生生肉铺门前,还看见了他提着一只篮子,买了一点酒肉,摇头晃脑地过身。他怎么会没有办法呢?于是云普叔知道了,这一定又是儿子发了懒筋,不肯听信自己的吩咐,不由的心头冒出火来:“你到底去不去呢?狗养的东西,你总喜欢和老子对来!”“去也是没有办法啦!”“老子要你去就去,不许你说这些废话,狗入的!”立秋抬起头来,将蔑刀轻轻放下,年轻人的一颗心里蕴藏着深沉的隐痛。他不忍多看父亲焦急的面容,回转身子来就走。“你说:我爹爹叫我来的,多少请玉五叔帮忙一点,过了这一个难关之后,随即就替五叔送还来。”“唔!……”月亮刚从树桠里钻出了半边面孔来,一霎儿又被乌云吞没。没有一颗星,四周黑得象一块漆板。“玉五叔怎样回答你的呢?”“他没有说多的话。他只说:请你致意你的爹爹,真是对不住得很,昨天我们还是吃的老南瓜。今天,娄!就只有这一点点儿稀饭了!”“你没有说过我不久就还他吗?”“说过了的,他还把他的米桶给我看了。空空的!”“那么,他的女人哩?”“没有说话,笑着。”“妈妈的!”云普叔在小桌子上用力地击了一拳。随即愤愤地说道:“大前天我还看见了他买肉吃,妈妈的!今天就说没有米了,鬼才相信他!”大家都没有声息。云普婶也围了拢来,孩子们都竖着耳朵,听爹爹和哥哥说话,偌大的一所祠堂中,连一颗豆大的灯光都没有。黑暗把大家的心绪,胁迫得一阵一阵地往下沉落……“那么明天下田又怎么办呢?”云普婶也非常耽心地问。“妈妈的,只有大家都饿死!这杂种出外跑了这么大半天,连一颗米花儿都弄不到。”“叫我又怎么办呢,爹?”“死!狗入的东西!”云普叔狠狠的骂了这句之后,心中立刻就后悔起来:“死!”啊,认真地要儿子死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心中只感到一阵阵酸楚,扑扑地不觉吊下两颗老泪!“妈妈的!”他顺手摸着了旱烟管儿,返身朝外就走。“到哪儿去呢,老头子?”“妈妈的!不出去明天吃土!”大家用了沉痛的眼光,注视着云普叔的背影,渐渐被黑暗吞蚀。孩子们渐次地和睡魔接吻了,在后房中象猎狗一般地横七竖八地倒着。堂屋中只剩了云普婶和立秋,在严厉的恐怖中,张大那失去了神光的眼睛,期待着云普叔的好消息回来。心上的弦,已经重重地扣紧了。深夜,云普叔带着哭丧的脸色跑回来,从背上卸下来一个小小的包袱:“妈妈的,这是三块六角钱的蚕豆!”六条视线,一齐投射在这小小的包袱上,发出了几许饥饿的光芒!云普叔的眶儿里,还饱藏着一包满满的眼泪。三在田角的决口边,立秋举着无力的锄头,懒洋洋的挥动。田中过多的水,随着锄头的起落,渐渐地由决口溢入池塘。他浑身都觉得酥软,手腕也那样没有力量,往常的勇气,现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一切都渺茫哟!他怅望着原野。他觉得:现在已经不全是要下死力做功夫的时候了;谁也没有方法能够保证这种工作,会有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