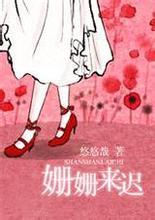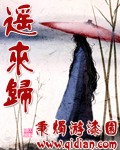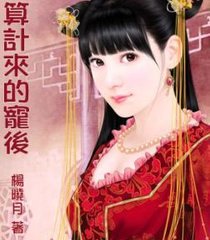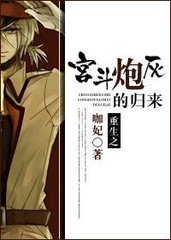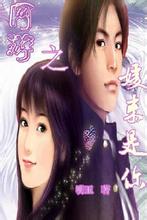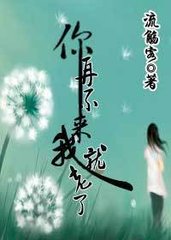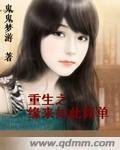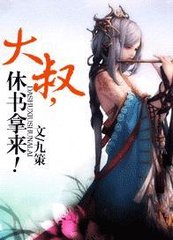灵魂的归来-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我们的家乡又多了一个名字:“秣陵”。
自从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以后,我的家乡的名字就不断的被人一改再改。继秣陵之后,曾改称建业、建康,后来又改称江宁。
秣陵改称建康,是三国时代的事。陈寿《三国志》《孙权传》说,建康十六年,孙徙治秣陵,筑石头城,改秣陵为建康,又称建业。建业的业字,有一时期还规定要写成“邺”字。
三国以后,到了晋初,又改称江宁。《宋书·地理志》说:晋太康元年,分袜陵置临江,二年更名江宁。“临江”之名,大约是由于临大江,由临江再改成“江宁”的原因,据《太平寰字记》引《晋书》说:“晋永嘉中,帝初通江南,以江外无事宁静,于此因置江宁县。”
不过,江宁不是南京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直到清末为止,南京或金陵,是由两个县组成的,除了江宁之外,还有一个“上元”。
这样,到了唐朝,我的家乡又多了一个新名字,改称“白下”,又称“白门”。后来的诗人有句:“白下有山皆绕郭”,又云:“白门杨柳好藏鸦”,都是指此。我觉得“白下”和“白门”两字很漂亮,一向很喜欢。可是,据史书的记载,曾经有一个皇帝因“白”色是不祥之色,不喜欢这个名字。这个迷信的小故事很有趣。
宋人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编类》曾记载了这个笑话,又考证白下得名之由。他说:
两汉《地理志》未有白下县。按《南史》,宋明帝时,闻人谓宣阳为白门,以为不祥,甚讳之。右丞江谧误犯,帝变色曰:白汝家门!
按《唐会要》及《地理志》,武德二年,更江宁曰归化,八年又更归化曰金陵,九年更金陵曰白下,正观九年又更白下曰江宁,则白下县始于此,然未知其得名之因。
据他的考证,白下的得名有几种说法,而且不始于唐。他说:“春秋时,楚使子木之子胜,处吴邑为白公。金陵,吴邑也,恐白之得名自此始。一说谓本江乘县之白石垒,以其地带江山之胜,故为城于此,曰自下城,东门谓之白下门,正其往路也。”
自下门的驿亭,当时就称为白下亭。李白有《金陵白下亭留别》诗,有句云:“驿亭三杨树,正当白下亭。”但我觉得关于“白门”这名字,最有趣的是:那个迷信忌讳白色的宋明帝,因臣下偶不小心提到了白门,竟狠狠的骂道:“白汝家门!”简直是泼妇骂街的口吻。
在南京不曾被称为“南京”以前,即在唐朝以后,明朝以前,我的家乡就在金陵、秣陵、建康、建业、江宁这些名称上打转,改来改去,同时还将辖境分成新县,时而隶属甲地,时而又隶属乙地,但是主要的名称不外上述那几个。直到明初,出现了“南京”,这才稳定下来了。同时除了本身以外,所辖的县份,也固定下来了,这就是江宁和上元两县。
到了清朝,南京在行政区划上的正式名称是江宁府,南京是府治的所在地,辖下有两县,即江宁县和上元县。因此一个南京人,他若是世居城内的,他就是真正的南京人,若是住在城外的,在籍贯的填写上就应该称为江宁人或上元人。从前应考时就要这么严格的区分。
在地方志乘的编纂上,有金陵志,建康志,江宁府志,江宁上元两县志,却始终没有南京志。上江两县的辖境,满清同治年修的《上江两县志》上说:
上元县,江宁府附郭首邑,境辖城东一面,北宽南狭……江宁为省城附郭,与上元同城,境辖城之西南一面,统计积地三千四百十四方里。
不过,南京虽有上元江宁的区分,过去除了在官式的履历籍贯上要这么填写以外,一般都是同称南京。
除了上述的这些名称以外,由于历代在行政统辖上不时有合并创新的措施,南京过去的面积范围和隶属问题,也非常复杂。上面已经说过,在隋唐以前,南京这一带的地方,始终是属于“扬州”的范围。直到唐朝以后,“扬州”才成为江北的江都县专用名字,这就是今日的扬州,不再管辖到江南了。
还有,江乘、胡孰、丹杨、濑渚、平陵、归化以及其他上十个少见的名字,在过去都曾经是南京,或南京一部分区域使用过的。濑渚、平陵是吴越时代这一带的旧城名称。江乘是秦朝的。《史记》说秦始皇三十六年东巡,“自江乘渡”,就是说他自江乘县渡江。
还有“丹杨”,这个古县也是设在今日南京境内的,“杨”字从木,不同于后来的“丹阳”。直到清朝,在江宁县境内还有古“丹杨”县城,俗称“小丹阳”,以别于今日镇江附近的另一个丹阳。
“丹杨”的得名,据《晋书·地理志》说,是由于附近的山上多赤柳,所以称为“丹杨”,与镇江的“丹阳”,全然是另一回事。
我看,很少别的地方,在名称的沿革上,会像我们的家乡这么多变革和不易弄得清楚的
读枝巢回忆篇
前些时候,诗人一峰先生惠寄一册《枝巢九十回忆篇》,翻了一下,见是一首述怀的古体长诗,我也不知道这位枝巢先生是谁,就放在一边。昨日读高伯雨先生的一篇记夏仁虎的文章,知道枝巢是夏仁虎先生的别号,是江宁人,去年秋天才去世的,享了九十高寿。那么,是一位乡先贤人,这才又取出来在灯下细读一遍。
以年岁来说,枝巢先生的辈分,该是我的祖父辈了。我生得晚,不及见到点过翰林,又放过学政的祖父,但是却见过母亲的王家外祖父和继母的吕家外祖父。吕家外祖父也是官京曹的,与潘复、郑洪年、誉虎先生都有来往,一定与这位“藏身百僚底,舣艇惊涛上”的同乡是相识的。
读了这首长诗,才知道这位前辈对于家乡的著述已经有过不少。“京市既成书,省志补耆献”,他除了主修过《北京市志》以外,还重修《江苏通志》,补耆献传三百篇。“秦淮与玄武,水利俱条贯”,据自注说,作《秦淮志稿》,由金陵文献馆印行。又作《玄武志》,已先刊行。“岁华书可读,遣民表邦彦”。自注说:“作岁华忆语,述南京风习”,又作《南京明遗民录》,为修志资料。
枝巢先生诗中所提起的这些有关家乡著作,我简直一种也未曾读过,这真是说来惭愧。尤其是叙述家乡风习的《岁华忆语》,该是我最爱读的,可惜不知道曾经刊行过否?
我又从这篇回忆诗中,知道作者在晚年曾将自己藏书中有关乡里者,献之公家,“有关乡里书,举向南京献”。将来有机会回乡,一定要到图书馆去看一看。
《枝巢九十回忆篇》,是一首五言二百二十二韵的长诗。作者以韵文叙述了他一生九十年的经历,旁及世变和国家大事,起于满清同治,近迄一九六三年在北京的生活:“生在新社会,应学好模范,公益先完成,私利戒单干,一家无闲人,举室少懒汉”,诚如他自己所说:“予作此篇,叙述生平,纬以时事。告语家人,但期易读易解,近代名词,时亦羼人,此难以昌黎南山诸名作相绳检也”。老人能这样通达,乃是最难得的。
枝巢先生活了九十岁,这首长诗就是一九六三年在他九十诞辰完成的,他自以为“百龄须臾耳”。哪知就在这年秋天谢世了。他在作回忆篇之后,曾自题七绝四首,第一首云:“居然生见九州同,东亚堂堂大国风,我较剑南情绪好,不烦家祭告而翁。”老而能作此语,可见胸襟的旷达,此翁实在是吾乡的人才也
顾二娘制砚诗话
这一次中华书局举办的书法文玩展览,陈列砚石甚多,其中有一方款为顾二娘制,石作灰绿色,砚底镌一佛像,真伪虽不可知,然颇可玩赏,顾二娘为清初吴门人,以善于制砚著名,非端溪老坑佳石不肯动手,因此虽以制砚著名,然亲手所制者不及百方,余多伪作。相传她辨别砚材,只须以脚尖点石,即能知道石质的好坏新旧,此殆好事者故神其说,于是顾二娘砚遂更为人所重,袁子才《随园诗话》载杭州何春巢得顾二娘砚,背上镌刘慈七绝一首,因题“一剪梅”一阕纪其事云云。据今人考证,砚上所镌七绝乃黄革田诗,见黄著《香草斋诗集》,并非刘慈所作,其为作伪可知。《随园诗话》的内容,所收多互相吹捧及应酬之作,市侩气甚重,久为识者所诟病,所记何春巢《题顾二娘砚词》一事,也可作证。袁氏云:
何春巢在金陵得端砚,背有刘总绝句云:一寸干将割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破云:吴门顾二娘为制斯砚,赠之以诗。顾家于专诸旧里,时康熙戊戌秋日。春巢困调《一剪梅》一阕镌其旁云:“玉指金莲为底忙,昔赠刘郎,今遇何郎。墨花犹带粉花香,制自兰房,佐我文房。片石摩挲古色苍,顾也茫茫,刘也茫茫,何时携取过吴阊,唤起情郎,吊尔秋娘。”
何春巢这首词,可说很肉麻。据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云:“按此诗黄宰田所作,刻在《香草斋诗》卷二,注云,余此石出入怀袖将十年,今春携入吴门,顾二娘见而悦焉,为制斯砚。余喜其艺之精,而感其意之笃,为诗以赠,并勒于砚阴,俾后之传者有所考焉……然则非刘慈窃取黄诗,即作伪者托名无疑矣。独怪子才与莘田相去不远,何以未及详考。春巢何郎刘郎之词,更属梦梦。”
邓说极是。按黄氏集中,尚有《题陶舫砚铭册杂诗》,也是题顾二娘制砚的,诗云:古款遗凹积墨香,纤纤女手带干将,谁倾几滴梨花雨,一洒泉台顾二娘。原注云:余田生蕉白砚,陈德泉井田砚,十砚翁青花砚,皆吴门顾二娘制,时顾没矣,陈句山太仆和韵云:淡淡梨花黯黯香,芳名谁遣勒词场,明珠七字端溪吏,乐府千秋顾二娘。
据《骨董琐记》说:顾二娘制砚,多无款识,不易辨别,凡细书八分款吴门顾二娘制六字者,大抵皆伪
平山堂与鉴真和尚
这几天报上一连读了好几篇文章,都是关于鉴真和尚的,因为今年正是这位了不起的僧人圆寂一千二百周年纪念,才使我知道他在扬州所住的大明寺,就是后来的法净寺,就是有名的平山堂所在地。
平山堂在瘦西湖的尽头,游湖的乘了小船来到这里,上岸步行上山,就到了平山堂。我在扬州玩的日子不多,但是平山堂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那一座小山并不高,站在宽阔的平山堂的坪台上,遥看来时所经过的一片湖水和远处的绿杨城郭,使人顿有胸襟开拓舒畅之感,我想平山堂迷人之处,大约就在这里。
平山堂,这个堂名就已经迷人。当时年纪太轻,也不知道那座小山名为蜀岗,更不知道这里就是唐朝有名的鉴真和尚修行之地,只知道这里是欧阳修最喜欢的地方,他在这里修筑了这座平山堂:不高不矮,恰可平山,这个堂名就已经够迷人了。
我去的时候,正是春末夏初。心里有一点年轻人的苦闷,便接纳了朋友的好意,从上海又回到曾经住过多年的镇江,再渡江到扬州去,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是消磨在平山堂上的。
记不起是谁的两句诗了:“竹床高枕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这就是在平山堂可以享受到的情调,也就是在平山堂可以见到的令人神往的景色。因为扬州地处大江北岸,从南岸的镇江望过去,我们见惯的是“两三星火是瓜州”,现在置身江北,这才有机会“卧看江南雨后山”。
平山堂后面有一大片沼泽,像是瘦西湖的尽头,或是污积了的湖址,草丛中有些地方是软泥,有些地方还有积水,到处是小树丛,没有半个人影,地方十分幽静。有一个下午,我到那里去作画,可是被那一派幽静的景色迷住了,站在那里只顾欣赏这种如画的景色,根本忘记了作画,直到晚潮使得积水向脚下的草丛中涨过来,浸湿了我的双脚,我才瞿然一惊,赶紧收拾了画具避开。
这时从树丛中传来春末那种不知名的山鸟的啼声,暮色渐渐的从山头上合过来。我拖着湿了水的双脚,绕过平山堂下面向湖边走去的时候,心里虽然有一点凄寂之感,但是知道这是人生中难得有的一种感受,是一时不会令人忘记的。
果然,事隔三十年了,在我读到报上所载的纪念鉴真和尚的文章,不觉仍想起了令我着迷的平山堂的景色
乡邦文献
前些时候,托人到上海去买一部《金陵丛书》,信已经去了很久,至今还没有回复。也许这样整部的地方掌故丛书,只有零本还不难买,要想得一部完整的,怕已经不容易了。
近年时时想读一些有关乡邦文献的著作,可是自己手边所有的实在太少,借又无处可借,买又不易买,徒呼奈何。自己虽然备有好多种广东的地方志,可是自己家乡的反而没有。这种可笑的情形,实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