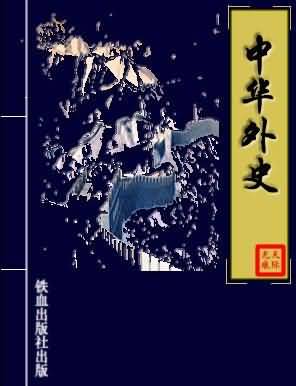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厨子,拿着一只托盘进来收碗。对洪俊生道:“四爷今天怎样?”洪俊生道:“我没有动手。”厨子道:“今天好热闹的场面!听说有一万多的输赢。刚才齐子雪捡了一个便宜,一句话,得了一千块钱,这不是点得着火的运气吗?难怪人家新升局长哩?”洪俊生道:“怎么一句话捡一干块钱呢?”厨子道:“今天来了一位新冤桶,不知道是哪部一个佥事,带来了三千块钱,一定要作庄,不到几宝就输了两千。他急了,说:‘还有一千块钱,我要双,作一宝卖了出去。’齐子雪正背着两只手,站在桌子横头看宝路,正在等机会啦。听了他这句话,随口答应一句,说:‘我买。’这位佥事不等人家说第二句话,往上一跳,抬起手来,使力叫了一句双,一下就把宝盒揭开,低头一看,却是一个单。他摇了两摇头,叹了一口气,把面前堆的十叠钞票,双手往齐子雪面前一推,说道:‘你拿去,你拿去。’一声不响,红着脸,就走。你想齐子雪的话,是随嘴说的,本来成心讨他的巧,揭开来是个双,他掉转身就走,你奈他怎样?这位佥事当时就是不叫他拿出钱来比一比,至少也应该重问一句,问他算话不算话呀?等到自己一揭开,你输了,你的钱摆在桌上,还收得转去吗?”厨子指手画脚,正说得高,兴,外面有人喊道:“老刘,你收碗怎样收这半天?还不快来。”厨子听见叫,便将碗收着走了。杨杏园问洪俊生道:“这样说来,你们这里,竟是一座很大的赌局了。”洪俊生道:“也不算大,不过有人保险,办得很热闹。”杨杏园道:“不赌钱,也可以去观场吗?”洪俊生道:“可以,赌场上,是没有阶级的。”
说着洪俊生就把他引进一重院子,上面正房里面,电灯通亮,人声吵得一塌糊涂。揭开帘子进去一看,只看屋子中间,有两张大餐桌子,并拢在一处,足有三丈来长,围桌子四周,坐了一排人,座的后面又站了一层人。桌子正面,有一个人将宝盒摇了一摇,放了下来,袖着两只手,在那里抽烟卷。这四围的人,就都拿出银元钞票来,也有放在里面的,也有放在外面的。杨杏园看见有些人,拿出钞票来,摇了几摇头。有些人拿出钱来,使力的在桌上一丢,骂了一句之后,接上又说道:“我偏要押者宝。”有些人拿钱在手上数来数去,却回过头同旁边的人说话。有些人把钱放在面前,却抽着烟卷,在那里想心事。一会儿,那人把宝盒子一揭开,就是人声大哗:也有乱骂的,也有叹气的,也有冷笑的,也有哈哈大笑的,也有笑着和旁观人说话的,也有埋怨人的,闹成一片。那开宝的对面,就有一个人,把一边的银元钞票,留着不动,把一边的银元钞票,拢在一处,就往怀里一扫,再拿出钱来,照着那边存留钱的数目,一份一份赔了出去。顿时满桌子都是人手,许多长袍马褂的阔老,也是一样。里面闹的这个时候,只见外面走进来一个人,歪戴着皮帽,穿着哔叽皮袍,外套青缎子坎肩,口袋上挂了一串金链子,左手胳膊上搭着一件大衣,右手拿着一根手杖,七溯八掷,口里衔着半截雪茄,挺着胸脯于走了进来。那边赌场上的人,看见这人进来,纷纷的对他打招呼,早有人过来,和他接了大衣和帽子,围着看的人,也就闪开了一条路,让出一张椅子来,请他坐下。他就将衫袖一卷,用只手按着桌子,对桌面上的钱,望了一望,笑道:“今天的局面,也不算大,我歇一会儿再来。”杨杏园看这人架子这样大,好像有点来头,便轻轻问洪俊生道:“这是个什么人?”洪俊生道:“是个木匠。”杨杏园道:“你瞎说,天下哪有这样的木匠?”洪俊生道:“你不信吗?我再指两个人给你看看。”便私下问道:“这桌上有两个议员,你认识不认识?”杨杏园道:“有一个小胡子穿蓝缎袍子的,我认得,他是众议员宋秋风。”洪俊生道:“你再瞧瞧他身边坐的两个人。”杨杏园看时,上手坐一个胖子,漆黑的一张脸,一张阔嘴,露出四五粒黄灿灿的金牙齿,一颗冬瓜似的大脑袋,额角上直冒黄豆大的汗珠子。身上穿一件灰缎袍子,胸襟上几个钮扣全没有扣上,敞着半边胸脯,露出一卷狐皮来。看他面前,倒摆了许多的银钱。下手坐的一个人,白净的脸皮,养着两撒胡子,穿着青呢马褂,架着玳瑁细边眼镜,左手上还带着一只钻石戒指,那钻石足有蚕豆那样大。洪俊生道:“你看这两人,像什么角色?”杨杏园道:“也无非小官僚、小政客之流。”洪俊生听了这话,对他笑了一笑,便把他拉到一边说道:“你这个人,难道也是一副势利眼吗?”杨杏园道:“这话怎说?”洪俊生道:“这两个人,胖子是开窑子的龟奴,胡子是私贩烟上的小流氓。你看见他穿得很阔,你说他是官僚政客。你专凭衣衫取人,还不是一副势利眼吗?”杨杏园听了他的话,想了一想,却也有些像。便道:“既然有这些人在内,为什么议员也坐在一处?”洪俊生道:“我不是说了么,赌博场上是没有社会阶级的。”杨杏园道:“只顾看赌博,正事都忘了。白天你不是约我来看宋版书吗,书呢?”洪俊生道:“这个卖主,刚才还在这里,怎样一刻儿会不见了。大概是过瘾去了,我带你上里面去找他。”说着,引着杨杏园又进了一个院子。那鸦片烟的气味,十分浓厚。上面屋子,挂了一层厚厚的青布棉帘子,洪俊生将帘子一掀,只觉一阵热气,夹着汗臭、油味、鸦片烟香,由里面直窜出来。杨杏园猛然的冲着这一阵热气,一阵恶心,由不得要吐出来。一看洪俊生已经钻进里面去了,他犹豫一阵,心想:“外面已经站不住,里面还去得吗?”便站在院子里,没有进去。这时洪俊生掀起半截帘子,探出脑袋来,直和他招呼。他心想,进去看看也好,看里面到底是怎么个样子,便鼓着勇气走了进去。
一看,这屋子是三个大上房打通了,成一个大敞间。房门边摆了一张小条桌,桌上也放了几样笔墨帐簿之类。有一个老头儿,戴着一顶放油光的小瓜皮帽,戴着一副单脚的大眼镜,那只断了的脚,却是用一根粗线来替它,绊在耳朵上,满嘴的花白胡子,沾满稀鼻涕。他把眼镜搁在额顶,坐在桌子旁,正在打瞌睡呢。屋子的四周,沿墙搭着二十来张小铺,铺上只有一床灰白的毯子,两个油腻的蓝布枕头,正中放一个洋磁盘子,里面放着一盏小烟灯,旁边放着一支烟枪。这些小铺,头尾相接,一大半躺着有人。那些人,有在抽烟的,也有对着那只绿豆似的烟灯,睡着了的。抽烟声,打呼声,咳嗽声,摔鼻涕声,喁喁细语声,倒很热闹。杨杏园刚走进来,便觉得脚底下又湿又粘,鞋子很不自在。低头一看,原来满地都是鼻涕浓痰,此外还有许多瓜子壳,烟卷头,一片一片的水,简直没有可以下脚的地方。杨杏园看见这个样子,连脚也不敢移,抽身便走了出去。洪俊生跟着出来问道:“你怎样就走?”杨杏园道:“罢了,罢了。我站在里面,直翻恶心,实在禁不住。夜深了,我也要回去了。宋版书,你明天送到我家里来罢。”说毕,仍旧转到前面院子来。一看天上,夜黑如漆,院子上面的一块天,布满了青光闪闪的繁星,一阵霜风,从屋上吹下来,脸上冻得生痛。远远却听见几声鸡叫,不是五更大,也是四更天了。匆匆的便回家去了。
这晚睡得太晏,次日一直到十二点钟还没有醒。正睡得很甜的时候,只觉有一个人摇他的身体,睁开眼来一看,却是吴碧波。杨杏园道:“怎么你一清早就来了。”吴碧波道:“快到一点钟了,还是清早吗?”说着便催杨杏园起来。杨杏园一面起床洗脸,一面和吴碧波谈话。吴碧波笑道:“我昨天留在镜报馆的信,你收到了吗?”杨杏园淡淡地答道:“收到了。”吴碧波道:“好好的,怎样闹起风波来了。”杨杏园道:“一千年也是要散的宴席,就此散了,倒也干净。”吴碧波笑道:“你这话,好像是解脱话,其实不然,你正是解脱不得。愿散不愿散,我都不管。我问你,到底为什么原由而起?”这时,杨杏园坐在临窗的一张安乐椅上,窗外的太阳,正有一道阳光,射在他的面前,照着飞尘,凭空好像一条白练。他手上端着一杯热茶,热腾腾的出气,那气绕着小圈儿由杯子里腾空而上。杨杏园端着杯子,眼睛望了茶杯的热气,穿过那道阳光,越上去越淡,就没有了。心里想着吴碧波说的话,拿着茶杯只出神。吴碧波道:“你心里打算些什么?”杨杏园听见他问,方醒了过来,笑着呷了一口茶,说道:“你昨日见她,她对你怎么说?”吴碧波笑道:“你既然丢开了,还问她做什么?”杨杏园道:“我没有别的意思,看她还怎样措词。”吴碧波笑道:“管她怎样措词呢,反正没有关系了,不是多此一问吗?”杨杏园道:“你告诉我,她到底怎样说?’误碧波道:“告诉你可以,你先说为什么和她恼了。”杨杏园叹了一口气道:“这事说起来太长,也不能完全怪她,不过我很灰心罢了。”吴碧波道:“你且说一个大概。”杨杏园道:“我在老七那里,虽不能多花钱,但是小应酬,决不躲避,想你也是知道的。那无锡老三,却处处以不屑之心待我,我要坐在屋子里,无论如何,她抵着面前,死人也不肯离开一步,简直比防贼犯还要厉害。”吴碧波笑道:“你这句话,就居心叵测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她抵在你面前?”杨杏园道:“我们逢场作戏,原是寻点乐趣,这些恶鸨,已经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偏偏她老是借题发挥,想大大敲我一笔,我真不高兴。最近索性有两回梨云不见面,全是老三陪着道些不相干的话,我便猜出了二三分,但是我还疑心是偶然的事情。这次冬至,我到她那里去,碰见有人做花头,场面很大,内容可知,梨云含含糊糊,拿话一味敷衍我,我就完全看出来了。”吴碧波用手指着杨杏园鼻子笑道:“嗤!你就为了这个事啊!你真不自量,她又不是你的什么人,你管得着吗?”杨杏园道:“我自然管不着。但是我也并不是为这桩事怪她。”吴碧波道:“你既不怪她,那又说什么?”杨杏园道:“自冬至以后,那无锡老三,就专门在我面前哭穷,说年关不得过,我已经听得有些烦了。有一天,我到何剑尘那里去,他不在家,是他的太太出来招呼。”吴碧波插口道:“花君当真换一个人了。前几天我曾到何剑尘家里去,只见她穿着灰布皮袄,黑布裙子,很像个当家人,剑尘正在教她读千字课哩。”杨杏园道:“可不是吗,就是有一层,熟人来了,喜欢留着说闲话。这天蒙她的盛意,亲自煮了一碗年糕留着我吃,她坐在一边打毛绳衣服,就说起闲话来了。她笑着问我:‘老七那里,还常去吗?’我说:‘久不去了。’花君笑着摇头说:‘我不相信。’我便将近来的话,略略告诉她一点。花君笑说:‘你还听见别的话没有?’我说:‘没有。’说着,我看花君低头在那里结绳子,却微微一笑,我料这里面,一定还有文章,便问她听见什么没有?花君说:‘我久已不和她们见面了,我知道什么呢?’我说:‘也许剑尘听见,转告诉嫂子了。’花君说,这些话,哪会传到她耳朵里去。我越听她的话越有意思,便说反正不去了,告诉我也不要紧。花君说:‘告诉你,你还要气死呢!回头剑尘知道了,又说我多事。我还是不告诉你。’我想请她说既然不肯,不如用激将法激她一激。便说:‘我知道了,你们总有点姊妹的交情,慢说我没有吃亏,就是吃了亏,还要说应该,哪能把话告诉我呢。’花君说:‘岂有此理,存着这样的心眼,那还是什么人呢。’我说:‘那末,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她才说,有一天去逛游艺园,碰见梨云同班子的白海棠,说起生意上,因问梨云老七,还是卖清倌人吗?白海棠说,是的。她说有一个姓杨的还去不去?白海棠说是常去,不过他去了,完全是面子帐,梨云的娘是不高兴敷衍他。有一天姓杨的坐得晏一点才走,老七的娘,抹下面皮来,就把老七一顿臭骂,说仔细一点,当心挨打。老七是胆小不过的,吓得哪里敢做声。从此以后,对姓杨的也就常给他冰吃了。只是姓杨的,倒好寿头码子,一点儿不知道。花君学着说到这里,又笑着对我说:‘不要见怪,这是她说的,不是我骂体寿头。’我说一我本来有些像寿头,说的很对。就追问后来的事,她又不肯告诉我。经我再三地问,她才说,老七的娘指明我是个穷客人,丢了也算不了什么,以后决不用好脸待我,免得提心吊胆来防备。以前

![(武林外史同人)[武林外史]落花有情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18/1878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