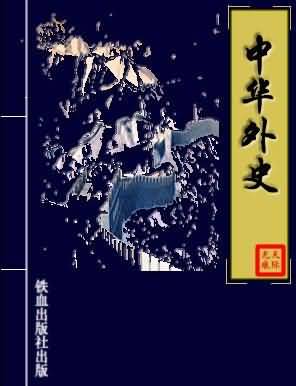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去收了。”杨杏园道:“‘中百诗绪已苍茫。’”舒九成道:“收得韵脚太生硬,要改一句才好。”杨杏园道:“姑存之,我们再望下联罢。”两人复又联成两首,共是三首。联完了,杨杏园掏出日记本子,把它记上。那诗道:
碧天遇递夜方长,(杨)月影随人过草塘。
树外市声风后定,(舒)水边院落晚来凉。
看花无酒能医俗,(杨)对客高歌未改狂。
不用悲秋兴别恨,(舒)中宵诗绪已苍茫。(杨)
野塘人静更清幽,(杨)一院虫声两岸秋。
浅水芦花怜月冷,(舒)西风落木为诗愁。
不堪薄醉消良夜,(杨)终把残篇记浪游。
莫厌频过歌舞地,(舒)等闲白了少年头。(杨)
强把秋光当作春,(杨)登临转觉悔风尘。
却输花月能千古,(舒)愿约云霞作四邻。
酣饮英谈天下事,(杨)苦吟都是个中人。
归来今夜江南梦,(舒)。憔悴京华病后身。(杨)
杨杏园写完,低低吟了一遍,笑道:“通体顺话,竟可以说得过去。”舒九成低下头,对瓜棚外头一望,只见月亮已照在头顶上,衣服碰着瓜棚边的深草,湿了一大块。不觉失声道:“这正是月华满天,露下沾襟了。时候不早,我要先回东城了。”杨杏园道:“你若有事,就请先走。今晚的月色很好,我还要在这里玩玩。舒九成道:“你新病初好,你也少坐一会儿罢。”杨杏园道:“我知道,你只管请罢。”舒九成听了这话,只得先走了。
杨杏园会了茶钱,渡过平桥顺着河岸,慢慢的走去。只见柳阴底下露椅上,一对一对的男女,坐在这里谈话,唧唧喁喁,真是男欢女爱,大会无遮。信步走去,又过了一道大桥,只见花木参差,月影满地。那边戏园子里面,正在演游园惊梦,笛声从水面上,被风吹了过来,格外悠扬好听,便走进亭子来,靠下风头坐着,那个笛声里面,“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曲词,仿佛还听得出来。杨杏园正听得出神的时候,隔壁亭子里忽有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猛然间倒吓了一跳。只听见一个人说道:“你且不要快活,这事成功不成功,现在还拿不稳。”又有一个人道:“我看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能长久不能长久,就在乎你的手段了。”那人道:“就怕不能成功。只要上了手,我相信决不会拆伙,我们的话,就是这样说。请你告诉刘老板,我们明日还在原地方会面。至于你自己的话,暂不要提。”又有一个人道:“那是自然。”说毕,两个人中,就走了一个。还有一个人在亭子里面。杨杏园听了他们的话,觉得这里面很有文章,便跨过亭子的栏杆,在竹丛子里面,对隔壁亭子张望。这一张望不打紧,越发引动了杨杏园好奇心。要知道他看出什么来了。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事出有因双妹通谜语 客来不速一笑蹴帘波
却说杨杏园隔着竹丛,对那边亭子一看,不是别人,是他一位老同学洪俊生。便走出竹丛,在亭子外绕了一个弯,走进亭子去。这亭子里面,本来安了一盏小电灯,洪俊生看见杨杏园走了进来,便嚷起来道:“呵呀!好久不见,你好哇?”杨杏园笑道:“一场病,几乎病得要死,还有什么好?”洪俊生道:“我仿佛听见你害了病了,总想来看你,无奈我被私债逼得厉害,日夜不安,闹得丧魂失魄。这半个来月,我实在连自己都闹糊涂了,没有来看你,请你原谅。”杨杏园道:“那过去的事不要提。但是你一不供家,二不养口,一二百块钱一个月的薪水,按月现拿,怎么还会借上许多债?”洪俊生道:“一言难尽,无非是嫖赌鸦片烟。”杨杏园道:“你又吃上鸦片烟了吗?年纪轻轻的,那是何必。”洪俊生嘴不留神,一口说了出来,收不回去,未免脸上一红。便道:“倒也没有上瘾,不过每天和同事的在一处,躺躺灯。”杨杏园道:“吃烟的人,都无非是由躺灯而起。我劝你,连灯也不要躺。”洪俊生道:“嗳,你有所不知,我们银行里的同事,十个有九个是抽烟的。天天和他们在一处,他们抽烟的时候,我少不得歪在床上谈话。他们有时将烟烧好,顺过枪来,老要我尝一口,自然不能回回都拒绝,尝得多了,就每天习以为惯。后来想者吃人家的烟,很不好意思,自己私下也买一点儿土,煮出来请客,就这样糊里糊涂抽上了。”杨杏园道:“现在讲应酬,都少不了这东西,年轻人上瘾却也难怪。”他明知杨杏园这种恕词言外有意,却又不好再把话来分辩,便把别的话来搪塞道:“我有一段很好的社会新闻告诉你,你愿意听不愿意听?”杨杏园笑道:“请问,我是干什么的?自然愿意听呀。”洪俊生踌躇了一会,笑着说道:“我新闻是告诉你,并不是供给你报上的材料,我可不许登报。”杨杏园明知他所说的,不外乎刚才他和人谈话里面的问题,正想考察他们闹些什么鬼,便道:“新闻原有可登不可登之别,你且把详情告诉我,若是与你有妨碍,我自然不发表。”洪俊生道:“那末,我可以放心告诉你了。你想我一个人坐在这亭子里做什么?难道好像你们书呆子一样,玩什么月,寻什么诗吗?老实告诉你……”说到这里,他把头伸出亭子外面,四处望望,然后把杨杏园一拉,同坐在亭子栏杆上,轻轻的说道:“不客气一句话,就是拆白。”杨杏园故意说道:“你不要瞎扯,又来骗我。”洪俊生道:“我骗你干吗?不过这拆白的,并不是我。”杨杏园笑道:“幸亏你有这句转笔,要不然,我的朋友都有拆白党,我还成什么人啦。”洪俊生笑道:“你不要当面骂人。你没有拆白的朋友,我却有拆白的朋友呀。”杨杏园道:“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你且把新闻告诉我。”洪俊生道:“我有个朋友,他是华国大学的学生,人虽长得不算十分漂亮,他是江苏人,衣帽鞋袜却十分时髦,学堂里有整个月不去,倒是游艺园每天少不了来一回。他来了又不正正经经的听戏看电影,东处站一会,西处跑一会,只在男女混杂的地方乱钻。”杨杏园道:“这种事很多,也不算什么新闻。”洪俊生道:“还有啦,好的在后面呢。他一年到头,专在这里面鬼混,认识的妇女确是不少。他现在又想出新鲜办法来了,说是在外头胡闹,身体很是吃亏,若再花钱,未免太冤。就此改的宗旨,专门注意有钱的姨太太,只要能给他钱,年纪虽老一点,姿色差一点,都不讲究。俗言道的好,物以类聚,他们也居然有这一党,这就是社会上所叫的拆白党了。前几天,我无意中和他在一处玩,忽然碰见同双饭店的刘掌柜c他疑惑我是他们一党,第二天他就特地找到我,问我怎样认识那华国大学的学生。我说不过是在一处看戏认识的,没有什么深交情。刘掌柜说:‘那就好办了。老实告诉你,现在有个很好的姨太太,托我在外头找一个人。提出三个条件,一要是学生,二要年纪轻,身体结实,三要是江苏人。这第二第三两条,我都有法子办,学生我却一个也不认识,实在不容易找。我看那天和你先生在一处的那位学生,倒样样可以对付。’我起初还说:‘人家是规规矩矩的大学学生,不做这样的事,你不要瞎说。’他笑说:‘洪先生,我们一双眼睛,也不知道看过多少把戏。他是个什么人,我还看不出来吗?’我说:‘猜是被你猜着了,不过他也是一个大滑头,他愿意不愿意,他必定要自己审度一番。等我探探他的口气再说。’刘掌柜说:‘你只管去说,我包他愿意。’我听了这话,当真代他转达,居然一拍就合。今天晚上,是他约双方在这里会面的日子。谁知道刘掌柜临时变卦,要男的方面,现拿出一百块钱来,作介绍费,另外还要写一张二百元的借字,限定三个月以内还清。你想男的方面,还没见着女的是老是少,是长是短,哪里会肯拿出这一笔钱?我听了搁在肚里,就没有去,所以还没有见面。那位学生,痴心妄思,还指望在这里面发一笔财,你说好笑不好笑?”杨杏园道:“他既然索这一大笔介绍费,必定成功以后,有些油水,你何不替他办成呢?”洪俊生摇摇头道:“你哪里知道,这一班青年猎艳家,和窑子里的妓女一样,外面风流儒雅,见了妇女十二分温存体贴,实在他的心比毒蛇还恶,你不给他钱,他先不愿意,他哪里还能拿钱出来呢?”杨杏园只管和他说话,不觉得夜已很深,回头望望那边戏场,锣鼓无声,戏早散了。花园里面,万籁俱寂,抬头望树顶上的月亮,亮晶晶地,那些染了露水的花枝,被月亮照着,叶子上都放出一种光彩。说话的时候不觉得,这时风从树里头钻来,吹在身上,很有些冷。再听听远处,一阵阵的人声如潮水一般,正是大门口游人和车马喧阗的声浪,破空而来。这时杨杏园和洪俊生的谈话,虽然没有说完,时候不早,只得各自回家。
洪俊生一走出大门口,就碰见两个同事,一个叫胡调仁,一个叫吴卜微,两个人站在门洞子里边,并排立着。那些从游艺园出去的人,恰好男男女女,一个个都从他们面前过去。洪俊生在人丛里挤了过去,将胡调仁的衣服一拉,说道:“喂!又在这里排班吗?等谁呀?’湖调仁对他丢了一个眼色,把他也是一拉,没有说什么。洪俊生知道他们又有什么把戏,也就站在一处看他们闹些什么。果然,不到一会的工夫,有两个十多岁的女学生来了。一个梳了两个辫子头,一个打了一根辫子,前面额顶上,都卷了一束烫发,身上一例白竹布褂,蓝羽毛纱短裙。梳辫子的胸面前,还插上一管自来水笔,虽然不是十分美貌,到也雪白的皮肤。内中那个梳头的,年纪大一点,走到胡调仁面前,故意停了一停。他们这三个人,六只眼睛的光线,不由得就全射在这两人身上。那个梳辫子的女学生,好像知道有人注意,低了头,扯扯那梳头女学生的衣服。那梳头的女学生,就低下眼睛皮,似看不看的,对胡调仁望了一眼,就挨身走了过去。三个人哪里肯放,赶紧就在后面跟上。四面的车夫,只管兜拢过来,这两位女学生,却不雇车,只是走了过去。走到大森里的后面,那个梳辫子的女学生,向那个梳头的女学生道:“姐姐,我们雇车罢。”那个就提高嗓子喊道:“洋车,阎王庙街。”胡调仁三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时就有几个车夫,拉拢过来,问南头北头,那女学生道:“横胡同里,门牌零号。”吴卜微听了这话,就把洪俊生和胡调仁两个人,往后拉着就跑。他两个人不知道什么事,怕是那女学生的家里人追来了,也只好跟着走。心里反而十分惊慌,怕惹出事来。吴卜微等那女学生离得远了,才站住了脚。吐了一口吐沫道:“呸!倒霉!倒霉!”胡凋仁连忙问道:“你这样鬼鬼祟祟的,什么事?”吴卜微道:“还说呢,天天在外头逛,这样内行,那样也内行,今天在阳沟里翻了船了。”洪俊生听见他话里有话,便问道:“怎么样?这两位不是正路货吗?”吴卜微道:“你们难道还看不出来?’湖调仁道:“我真看不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看她有什么破绽吗?”吴卜微道:“什么破绽不破绽,这是南城的土货,冒充女学生在外骗人,亏你还当作奇宝,钉了她一夜的消。人家背后一定要笑掉牙齿,骂我们是傻瓜呢。”洪俊生道:“你怎么知道她是土货,难道她还有什么记号不成?”吴卜微道:“记号虽然没有,倒是这种人,很可以看得出来的。第一,女学生她总大方些,不会像这样鬼鬼祟祟的。第二,女学生吊膀子,她不能和我们这样公开。”胡调仁道:“算了,你这些话毫无理由,我不爱听。”吴卜微道:“我知道,你看中了她,所以你不愿意我糟蹋她。告诉你,我实在另外有一个真凭实据,知道她是土货”。胡凋仁道:“你且说出来听听。”吴卜微道:“她刚才不是给我们打了个无线电话,说是住在阎王庙街横胡同零号吗?这个零号,就是土货公司,她住在那里面,你想是土货不是?”洪俊生道:“你何以知道那里就是这种地方呢?”吴卜微正要回话,有一个警察,拿着指挥刀,乱砍洋车夫赶了过来,看见他们三个人,站在路旁边唧唧哝哝的说话,很为诧异,站着打量了一番。吴卜微轻轻的道:“走罢,警察都在注意我们了。”三个人便一面走,一面说。胡调仁又提起刚才的话,吴卜微道:“你不要问,这是很容易证明的,你要真是看中了那两位女学生,你花两块钱,我可以带你去会会她。”洪俊生便凑起趣来,说道:“调仁,你就花几块钱,看他这话真不真。”胡调仁道:

![(武林外史同人)[武林外史]落花有情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18/1878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