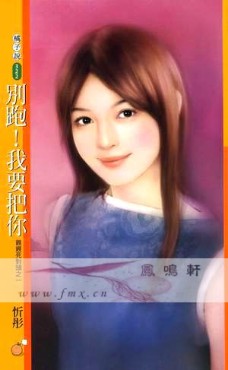要把金针度与人-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所谓书目指导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纪允前一三四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例如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
帛书也出现了
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能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它显示出来的病名,在内科方面、有肌肉痉挛、精神异常、往来寒热、小便不利、小便异常、阴囊肿大、肠道寄生虫和中蛊毒;在外科方面,有外伤、化脓、体表溃疡、动物咬螫、肛门、皮肤、肿瘤;在妇科方面,有产时子痫;在儿科方面,有小儿惊风;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医学材料,-看这些早于《内经》等现有医书的材料,它们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又如同时出土的《相马经》,这是中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己从车战演变到骑兵,马的身价,也就愈来愈高。传说中的相马专家是伯乐,事实上,这种专家是很多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就提到十个相马家;《史记》(日者列传)也提到“以相马立名天下”的人氏,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这部《相马经》竟用来给死人陪葬,它在当时,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读了这部书,我们不得不惊讶:古人对马,原来是这样不马虎!
搜寻亡佚
另一个现代的观点是被埋没的古书的广为流传。中国历代的战乱不断,图书上的损失,早已无法细计,不论无意的被焚于兵祸,还是有意的聚毁于七塔,对文化而言,自属有害无益。今天我们得现代印刷术之便,实在应该把这些被埋没了的古书,尽量予以亮相,以免及身而绝〔注二〕。过去有心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出版“丛书”。
“丛书”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这部书成于宋宁宗嘉泰元年(一二○一),距离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
七百八十多年来,从事文化出版的人,辑印丛书的种类很多,但是专辑近著搜寻亡佚的,除了光绪年间潘祖荫的《功顺堂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实不多见。尤其赵之谦的丛书中,收有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未》一卷,更可看出辑刊者的历史眼光。
宋朝以来,因为受印刷技术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只能影刻,直到清末,还是如此。陈三立的《黄山谷集》、端方的《东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但因影刻太贵,且产生窜易首尾节略翻刻的缺点,给了人们不良的印象。现在印刷术进步了,并且超过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古逸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水准,所以现在为被埋没了的古书,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寻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责无旁贷了。
现代分类
由于过去的通病是儒家挂帅下的四部分类,古书所遭遇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这种挂帅和分类不打破,中国的古书情况必将永远陷在不均衡的畸形里、陷在比例不对的悬殊里。所以,用现代的观点处理古书,必须首先把儒家挂帅四部分类的错误予以矫正,把所有古书,重新估定,该拉平的拉平、该扶起的扶起、该缩小的缩小、该放大的放大、该恢复的补足该重视的给它地位〔注三〕。这种重新估定之下,整个中国文化遗产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再用现代方法去“新瓶装旧酒”,古书才不止是古书,才有现代的意义〔注四〕。在现代意义的光照下:许多古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许多古书,古人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余味无穷。如今我们处理古书,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
解决难读的问题
除了现代分类外,如何解决读得懂古书的问题〔注五〕,也是现代的观点中不能忽视的事。中国古今语文上的变化,差距很大,《尚书》中的文告,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难的文言了;《论语》中的对话,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书的文字语言,对现代的中国人说来,有时比外国文还恐怖。这一现象,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提出来讨论了。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写《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就指出:
诸君对于中国旧书,不可因“无用”或“难读”这两个观念,便废止不读。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准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至于难读易读的问题呢,不错,未经整理之书,确是难读,读起来没有兴味或不得要领,像是枉费我们的时光。但是,从别方面看,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功夫,拔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
所以我希望好学的青年们最好找一两部自己认为难读的书,偏要拼命一读,而且应用最新的方法去读它,读通之后,所得益处,在本书以内的不算,在本书以外的还多着哩。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读古书的能力更不如前,时间也不如前了。所以,有心人处理古书给现代的中国人,必须兼顾到现代人的读书能力,精挑细选之后,必要的解题、注释、翻译,也该尽量齐备〔注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