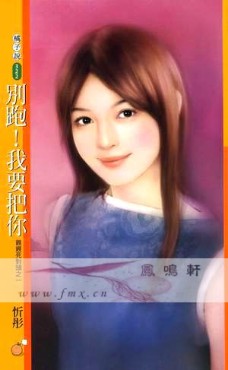要把金针度与人-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魏源的著作里,影响最大的是《海国图志》。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七年,魏源根据林则徐的《四洲志》稿,增补成为一百卷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以制夷”的理论,呼吁变法图强。日本人首先受了这部书的影响,促进了维新。中国人反倒慢吞吞的,但总算从这部书里,了解了不少世界大势。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沈藻祯、李鸿章等的洋务运动:都是顺着这一思路下来的。
魏源是清朝中衰时代,首先能觉悟的知识分子。他和龚定盦一样,都在这种觉悟下,走向经世致用的方向。他比龚定盦小两岁,但多活了十六年,所以实际的成绩就更好了。
范成大:《石湖大全集》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江苏吴县人。他是宋朝进士。做官时,很有见识,论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国力,曰人力,今尽以虚文耗之。”皇帝很赞许他。后来派他使金,他义正辞严,一度惹得金朝满朝文武大怒,甚至金太子都要杀他,但他不怕,“致书北庭,几于见杀,幸不辱命”,“竟得全节而归”。
《宋史》说:“成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上尝命陈俊卿择文士掌内制,俊卿以成大及张震对。自号石湖,有《石湖集》、《揽辔录》、《桂海虞衡志》行于世。”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说:“成大有《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别集》二十九卷,今皆未见。”《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明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自然是他的全集的应有名目,可惜失传了,所以连纪昀都看不到了。
范成大的诗、词、梅谱、菊谱都有单行本问世。他的《吴船录》、《吴郡志》、《桂海虞衡志》也都各有专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收有《石湖纪行三录》,是一种好版本。《吴船录》是范成大在一一七七年(宋孝宗淳熙四年)五个月的游记,写他自四川到浙江的见闻,内容颇为详赡,是游记中的上品。
徐宏祖:《徐霞客游记》
徐宏祖(一五八六~一六四一),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他少年时候,就“特好奇书,喜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复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这种神游名山大川的抱负,早就藏在心中了。
徐宏祖十九岁时候,父亲死了。办完丧事,他“愈复厌弃尘俗,欲问奇于名山大川”。他的母亲赞成他出去跑跑,他就出发了。他二十二岁到四十岁间的跑法,和四十三岁后不一样。四十岁前母亲在世,他多少要受“不远游,游必有方”的约束。母亲既死,他就大游特游起来,从此不计程也不计年,大过他“万里遐征”的瘾了。
丁文江《徐霞客游记序》中说:
当明之未,学者病世儒之陋,舍章句而求实学,故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辈,奋然兴起,各自成家,遂开有清朴学之门。然霞客先生,生于顾、黄、王诸公之前,而其工作之忠勤,求知之真挚,殆有过之无不及焉,然则先生者,其为朴学之真祖欤?
徐宏祖在乱世中足遍天下以知苍生,独往孤行,死而后己,这样脚踏实地的人,值得我们怀念他。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字灵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是清朝进士。四十三岁时候,发生了文字狱,他被牵连。《清史稿》说:
五十年(一七一一),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一七一三),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嶧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此后他在朝里做官,后来因为刚正敢言,被人整冤枉,乾隆时-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词,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稗风化为任。尤严子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桐城派”的文章,游记每被人忽视,我特别提出来,做为样板。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
谈中国名著,得先谈中国书;谈中国书,得先谈中国的文字历史。
中国历史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纪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纪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从何处说起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轰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古书有多少呢?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着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
《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好坏标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缄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阎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