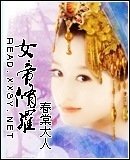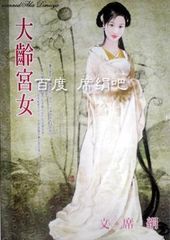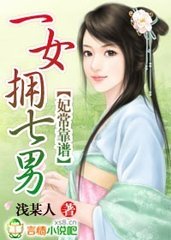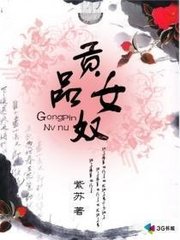大浴女-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高于眼前的城市,让她镇静地、不事矫情地面对所有的城巾和生活。而当她想到镇静这个词的时候,她才明白坐在出租车里的她也许不是那么镇静的,她大概要结婚了。
她从来也没结过婚——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儿毛病,好像其他准备结婚的人都结过许多次婚似的。但是,她从来也没结过婚——她仍然这么想。她这样想自己,谈不上褒意,也谈不上贬义,有时候显得自傲,有时候又有几分哀怨。她知道自己不像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人,她的眼神儿里常有一种突然不知所向的湿润的蒙胧;她的体态呈现出一种没有婚姻、没有生育过的女性的成熟的矫捷、利落而又警醒。她办公室的抽屉里总是塞着一些零食:话梅、鳗鱼干、果仁巧克力;她是福安一家儿童出版社的副社长,不过她的同事没有叫她尹社长的,他们直呼其名:尹小跳。很多时候她显得春风得意,她知道,最受不了她春风得意的就是她的妹妹尹小帆了,特别是在尹小帆远走美国之后,这一切变得更加清晰明朗。长期以来她总是害怕把自己的恋爱告诉尹小帆,可越是害怕,她越是非要把每一次恋爱告诉尹小帆不可。就好像以此证明她不怕尹小帆,她经得起尹小帆在她的恋爱中所做的一切。眼下她仍然有点儿鬼祟、又有点儿逞能似的这么想着,她仿佛已经拿起了电话,已经看见越洋电话的那一头,芝加哥的尹小帆听到这消息之后那张略带懊恼的审视的脸。还有她那搀着鼻音的一串串语言。她们,尹小跳和尹小帆,她们曾经共过患难她们同心同德,是什么让尹小帆如此激烈地蔑视尹小跳的生活——那的确是一种蔑视,连同她的服装,她的发式,她生活中的男人,无一不遭到尹小帆的讽刺和抨击,以至于尹小跳卫牛间的淋浴器也使尹小帆产生过不满。那年她回国探亲,在引小跳家里住了几天,她抱怨姐姐家热水器喷头的出水量小,弄得她洗头之后冲不干净头发——她那一头宝贵的长发。她绷着脸抱怨着,一点儿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而尹小跳只能压抑着心中的不快,不自然地笑着,她永远记住了自己那不自然的笑。
没准儿她不应该告诉她。
出租车把尹小跳送到亿客隆超市,她采购了足够一星期吃的东西,然后乘车回家。
家里停了暖气,房间里有些阴凉,但这阴凉显然不同于冬天的寒冷,它不是充满空间的密集的生硬,它是不确定的,带着几丝幽幽的落寞之气。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的晚上,尹小跳喜欢打开所有的灯,从走廊开始,到厨房,到书房,到客厅,到卧室,到卫生间,所有的灯,顶灯,壁灯,台灯,落地灯,镜前灯,床头灯……她的手依次“啪啪”地按着这些开关,只有房子的主人才可能这么熟络而又准确。
第2页
二
尹小跳是这房子的主人,她用开灯的方式和她的房子打着招呼,她的这些灯照亮了她的房子,又仿佛是灯们自己点亮自己欢迎着尹小跳的回家。于是,灯光照亮的每一件家具,灯影里每一片柔暗的朦胧,都使她觉得可靠、踏实。她就这样把每一个房问行走完毕,最后将自己逼进一个小小的角落:
客厅里那张灰蓝色的织贡缎面料的单人沙发,那似乎是她在人睡觉时最喜欢的一个角落。每当她从外边回来,下班或是出差,她都要在这张小沙发上坐着愣那么一会儿,喝一杯白开水,缓缓神儿,直到身心安生下来,松弛下来。她从来不坐那张三人沙发,即使当陈在把她抱在怀里,要求更舒适地躺在那张三人沙发上时,她也表示了坚决的不配合。情急之中她干脆对他说:“咱们上床吧!”
这是一句让陈在难忘的话,因为在那之前他们从未上过床,尽管他们认识了几十年,他们深明彼此。后来,有时候当他们有些烧包地打着嘴仗,嚼清是谁先“勾引了”谁时,陈在就会举出尹小跳的这句话:“咱们上床吧!”这话是如此的坦荡,率真,如此令人猝不及防,以至于缺少了它固有的色情成分,使陈在一万遍地想着,此时此刻被他捧在手中的这个柔若无骨的女人,真是他一生的至爱,从来就是。也似乎正因为那句话,那个晚上他们什么也没做成。
今晚陈在不在,他到南方出差。尹小跳吃过晚饭,又坐回到小沙发上看了一部书稿,就洗澡上床。她愿意早点儿钻被窝儿,她愿意钻在被窝儿里等陈在的电话。她尤其喜欢“钻被窝儿”这几个字,有点儿土,穷穷气气的不开眼,可她就是喜欢那“钻”和那“被窝儿”。她一直不能习惯宾馆、饭店和外国人的睡法:把被脚(或毯子脚)连同被单紧紧绷在床垫上,腿脚伸进去,一种四边不靠、没着没落的感觉。
她也不冉欢羽绒被和蓬松棉、透气棉之类,轻飘飘地浮在身上反倒让人累得慌。她一直盖真正棉花絮成的被子,她喜欢棉被叠成的被窝儿的千般好处,喜欢它覆盖在身上那稍显重量的温柔的压迫感,喜欢被窝儿的旮旮旯旯隐藏着的不同温度,当她因为热而睡不着觉时,她就用她的脚寻找被窝儿底下那些柔软褶缝儿里的阴凉儿。她需要蜷缩的时候,被窝儿也会妥帖地簇拥起她的身体,不像那些被床垫压紧的棉毯毛毯,你简直不要妄想扯动它,你得服从它的霸道,因而你得保持得体的睡姿——凭什么呀!尹小跳想。每次她出差或者出国都故意把那些毯子、被单掀得乱七八糟。棉被使尹小跳的睡眠一直挺好,她的不愉快大都是半夜醒来袭上心头的。当她打开台灯,脚步不稳地去卫牛间撒尿回来,关掉台灯复又躺在床上时,只有这时,她才会突然感到一种伸手抓得到的孤独甚至无聊。她开始胡里胡涂地想一些事儿,而人在半夜醒来想起的事儿大半是不愉快的。她是多么不愿意在半夜醒过来啊!当她真正有了陈在之后,她才不再惧怕半夜的苏醒了,她将不再是她一个人。
她蜷缩在被窝儿里等来了陈在的电话,他在电话里亲着她,他们说了很长时间。当尹小跳挂断电话时,她发现自己还不想睡觉。就在这个晚上,陈在远离福安的晚上,她特别特别想看一看封存在书柜多年的那些情书。那不是陈在写给她的,她也早就不再爱恋那给她写情书的人。她此时的欲念谈不上是怀旧,或者有几分查看和检点的意思,也许她珍惜的是那些用人手书写在纸上的字。在今天,已经没有太多的人用手把握着笔在纸上写字了,特别是情书一类。
2
一共六十八封信,每封信都被尹小跳按时间顺序编了号。她打开第一号,展开一张边缘已经发黄的白纸:“小跳同志,在京匆匆一面,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有一种预感,我们肯定还会冉见面的。现在我在飞机上给你写信,今日到上海,明日飞旧金山。你约我写童年自传的事我会认真考虑——因为是你约。”署名“方兢”,时间是1982年3月。
与其说这是一封信,不如说这是一张便条。字很大,歪歪斜斜地铺排在十六开白纸上,就显得稀疏,字们像是瞪着傻眼在看读信的人。严格来讲,它也算不上情书,但它当年给尹小跳灵魂的震撼,却比日后她接到的他那些真正的情书要强烈得多。
写信人方兢在当年的电影界人红大紫: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美丽生命》在全国各大影院不厌其烦地上映之后,还连获了几个大奖。那近一部描写中年知识分于在过去的年代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却乐观地存活下来的电影,方兢就在电影中扮演那个被关押在边疆劳改农场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劳改使他再也无缘和这种乐器见面。
电影中有个情节:主人公在食不果腹的超常劳动之后,当他从莜麦田里直起腰,看见远方迷人的晚霞时,还是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他以右臂当琴脖,用左手按在右臂上,手指跳动着,就像在按动提琴的柔弦。电影在这时有个特写,即主人公那条瘦骨磷峋、伤痕累累的胳膊和他那只已经变形的古怪的手。那条模拟着提琴的胳膊和模拟着演奏的手让人心碎,尹小跳每次看到这里都禁不住流下热泪。她坚信那不是表演,而是方兢本人就有那样的经历。这样的电影情节在今天看来也许稍显矫情,但在当年,在人心被压抑了太久的时代,它轻而易举就能呼唤出观众奔涌的泪水。
尹小跳从来就没有设想过她会认识方兢。那时她大学毕业不久,通过关系进人福安市儿童出版社当编辑。像所有崇敬名人的年轻人一样,她和她的同学、同事热心地议论《美丽生命》这部电影和方兢本人,阅读报纸上、杂忐上一切关于方兢的介绍并且争相转告: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爱好,他正在进行的创作,他带着影片赴某国参加某个电影分又获一个什么奖,甚至他的身高他的体重尹小跳都一清二楚。她和他认识是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组稿,遇到一个大学同学,这同学的父亲在电影家协会工作,因此消息特别灵通。同学告诉尹小跳,电影家协会要给方兢的作品开研讨会,她有办法带尹小跳溜进会场。
研讨会那天,尹小跳被同学带着溜进了会场,她们坐在角落里。那会上说了些什么尹小跳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方兢比电影上显得年轻,说一口略带南方味儿的普通话。他嗓音洪亮,笑起来身子频频向后仰,显得很随便。还记得他手握木烟斗,话到激动之处他就把烟斗在半空挥来挥去,有人称之为潇洒。他的四周,围满了俊男靓女。当研讨会结束时,这些人一拥而上,举着本子请方兢签名。同学一把拉住尹小跳的手,想随着人流冲上前。尹小跳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却本能地向后退着。同学只好放开尹小跳,单枪匹马往前挤去。其实在尹小跳手里,那笔记本已被翻到了新的一页,翻到了准备让方兢签名的那个空白。可她还是摸着本子向后退着,也许是有些胆怯,也许是骨子里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合时宜的傲气扼制了她的狂热。尽管在他面前她是如此地微不足道,那她也不愿意充当一个只会追着名人签名的傻瓜。她后退着,义在心中惋惜着这白白失掉的机会。这时,处在人的旋涡中的方兢突然伸出他那长臂猿一般的胳膊,指着人群之外的尹小跳说:“喂,你!”他说着,拨开人丛走到尹小跳跟前。
他来到了她的跟前,小由分说夺过她手中的本子,在上面签下了他的大名。
“现在你满意了吧?”他似乎屈尊地直视着尹小跳的眼睛说。
“我更愿意说非常感谢您,方兢先生!”尹小跳意外而又激动,并忘乎所以地胆大起来:“不过,您怎么知道我是想让您签名呢?”她也试着直观他的眼睛。
“那你想干什么?”他不明白。
第3页
三
“我想……是这样,我想向您约稿。”尹小跳到底把自己和那些单纯的请求签名者区分了开来,她怀着满心幼稚的郑重,即兴式地、又带点儿挑衅性地对方兢说。
“我看咱们俩得颠倒一下了。”方兢边说边从衣兜里摸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我请你给我签个名可以吧?”他把信封伸到尹小跳眼前。
这倒使尹小跳不好意思了,但她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在方兢的提醒下,留了出版社的地址、电话。接着,她不失时机地、趁热打铁地对方兢说了她的约稿计划,尽管这计划是几分钟之前她才瞎编出来的。她说,她报了一个选题,社里已经通过了,她准备出一套名家童年丛书,包括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学者、导演、教授等人,面向小学四年级至初中的孩子,方兢先生的作品和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人反响,假如从童年角度切入写一本自传,肯定会受到孩子们的欢迎,问时也能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尹小跳一边飞快地说着,一边为自己这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感到惭愧。越是惭愧,她便越要煞有介事、一板一眼地说下去。就这样,越说越跟真的似的,是啊,就跟真的似的;她多么希望方兢在她们滔滔不绝的时候拒绝她啊,那样她就解脱了,那样一切就跟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了。本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啊,一个人名人和一个外省出版社的普通编辑。可是方兢没有打断她也没有拒绝她,是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打断了他们,簇拥着他作现场采访去了。
那次研讨会后不久,卢小跳就接到了方兢从飞机上写给她的这第一封信。她无数遍地读着信,研究着、玩味着、琢磨着那些似有意、似无意的字字句句。为什么他一定要在飞机上给我写信呢?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行踪比如上海比如旧金山什么的,随便告诉一个陌生人呢?在尹小跳的概念里,名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神秘的,包括他的行踪。又为什么因为是她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