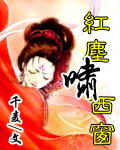西窗烛话-第9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了。您们吃吧,我的东西搬走了,具体他会给您们一个说法的。
2006…6…1718:33文文
您们不用等我了。上周我在家休假,您应该还记得吧,那是我为他做第二次人流。可我术后第二天,他出去和别的女孩开房,别人没同意,他回来了,我用他的手机和那女孩聊,她什么都给我讲了,我原谅了她,最后一次。
今天又冒出一个女孩,对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她还痴痴的等他年底带回家,明年结婚。我不知道我还能用怎样的胸怀来包容他,我实在做不到了。
2006…6…1718:45
文文:你说的是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问他,他又不给我们说,还是问你是否还有可能回家?
我们还是喜欢你的,只不过看你的意见了。两人还是有感情的,你还是多考虑再作决定。
2006…6…1719:19文文
我也在一次次的接受晴天霹雳。这些都是实情。两个女孩自己亲口告诉我的。今天的那女孩还和他保持每周见面两次的频率,最多一天打十一个电话,这是我查的他的话费清单。
我们确实有感情,可我受不了他和别人也很有感情。我可以跟别人分享很多东西,但爱情不能分享。阿姨,您也是女人,换个角度您会怎么做呢?
2006…6…1719:28
文文:下午我以为你们在闹着玩就没在意,谁知你们真的是在吵架。我已经把他赶出去了,我对他说:我没有他这个儿子,除了你,我不准别的女孩进我家的门。你能回家来吗?我们还是等你吃饭。
2006…6…1720:29
文文:看了你的短信我泪如泉涌,我给你的第三个短信你也没回,我就知道这次你恐怕真的是要离我们远去了。我只是不明白,中午吃饭时还在讨论下午去看房,几个小时后一切都变了。
你是知道你是我和你伯伯最满意的儿媳的人选,也越来越把你当作一家人了。突然的变故叫我无法承受。但也许我这次得承认事实了。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多考虑一下,但我们会同意你最后的抉择的。
备注
2006…11…0916:29
文文:把你放走,我们是挺舍不得的,我曾经告诉过你,你几乎符合我们选择儿媳的全部条件和要求,所以我们才忙着给你们买房,筹备来年的婚事;你对他、对我们也是真心实意的,而且在他情绪最低沉的时候,一直陪伴着他,为他吃了不少的苦,我们都是知道的。他是一个一旦失去才知道珍惜的人,我们看得出他也是很后悔的,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耐心的等了你整整半年,终于知道你是真的离我们而去了。
我们会记得你这个圆脸大眼镜的姑娘,祝你以后象鲜花一样绽放,有一首歌唱得好:“只要你勇敢的抬起你的头,苦水就能换美酒。”
2006…11…09文文
谢谢阿姨、伯伯这么长时间对我的关心照顾,说实话我也是很舍不得的。
当初我搬过去是认真考虑过的,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也是准备跟他结婚的。也许以后我才能更深刻的体会到两次人流和从一个男人的家里搬进来又搬出去对一个未婚女孩的影响,可是…
可能是我和他缘分不够吧,最终我们没能走到一起。希望这次以后,我和他都能成熟一些,好好珍惜下一个女孩。
最后真诚的祝福你们全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新号码我记住了,有空常联系,有任何需要我帮忙或照顾的地方就尽管说,我肯定会乐意帮助的。
2006…11…12誊写
一地鸡毛 环保之争
随着刘家大堰社区3A花园和华龙嘉树施工进展加快,外来的施工建筑工人更多地聚集到了这里。不经意之间,沿街一带的铺面的生意也好了许多。我们二单元楼下的早点面馆也摇身变成了一家露天餐馆,罩着塑料布的圆桌,高靠背座椅,火锅,炒菜,吃饭的时候还可以坐上两三桌。
原来的那家面馆就这样被赶到我们楼下了,就在我们卧室的下面。用角铁架起长长的遮阳篷,在篷下架起三两大孔煤炉,摆上几张简易桌,放上几把方便筷,竖起一块“重庆红油面馆”的招牌,就这样不声不响的重又开张了。牛肉,排骨,三鲜面条,还有凉面。我没有去看过,也许还有些其它品种吧。
问题就接踵而来了。清早五点,面馆的伙计就哗哗啦啦的打开卷闸门,掏火,烧水,切东西,接着就是消毒公司的货车运来消毒碗筷,乒乒乓乓的,粗人粗话多,声音大,笑声多,在寂静的清晨显得很刺耳,就把人吵醒了。接着就有呛人的煤烟味从篷下钻上来,夹杂在那么些辛辣的佐料味里一齐扑进我们的窗户里,不一会儿就弥漫了整座房间,再过一会儿,我们的嗅觉就开始麻痹,呛人而辛辣的味道也就慢慢习惯了。
我睡在靠窗的床边,气味的变化首先影响了我,就睡意朦胧的爬起来,逐一关上玻璃窗,然后重新上床睡觉,可那时再也睡不着的。楼下小学生的叽叽喳喳,食客们的天南海北,民工们的大嗓门,汽车的喇叭声交织在一起,热闹的就如同集贸市场。唯一值得宽慰的是,面馆的生意主要集中在早上,煤烟和油污在中午就结束了,只是每天清晨,就被呛人的气味欢欣,的确是很煞风景的。
妻子开始与面馆的女老板交涉,没几天,女老板就提着一壶油登门拜访,说的倒是客气,楼上楼下,小本生意,尽量避免干扰,有不对之处,希望能得到谅解,但对油烟扰民却只字不提。妻子自然是不认可,两人就站在我家门口唠唠叨叨说了好久,根本没有共同点,妻子要求面馆搬走,或者赔偿我家一台空调,这是女老板无法接受的,争执了半天,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冲突开始升级,妻子经常在下午或者晚上到楼下与面馆的女老板面对面地展开谩骂。两人都是泼妇类的佼佼者,就这样站着,隔着一段距离,互不相让,破口大骂,竞显河东狮吼的本质,所有能想起的咒骂词语都被用来当作武器,语言之肮脏,形容之低级,咒骂之恶毒,都可以称作是登峰造极。只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妻子还鼓动儿子下楼交涉,他哪是女老板的对手,几句话就败下阵来。
妻子决定上告。先去找刘家大堰居委会,那些干部推得一干二净,口口声声说同情,还透露说,刘家大堰小学也来反映过,但他们没有执法权,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是找西陵城监支队。电话打过去,被推到市城管110,反映了,却没有了下文;妻子再打电话到卫生执法,状告重庆红油面馆无证经营,卫生条件极差,接电话的人回答得很干脆,他们就是管这个的。妻子怀信心地等待了好久,到最后连个人影都没见。
我有些忍不住了,我告诉妻子,这是极普通的现象,政府部门只管主要街道上的违法经营和卫生状况,那样既有影响力,又有罚款可收,一举两得的事才有人做,对小区内的餐馆,面馆向来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向来就是视而不见,放任自流的。我启发妻子,所谓“打蛇打七寸”,做生意的向来就不怕与人吵架,对他而言毫发无损,最关键的就是想法让面馆没人光顾,没人上门就没有生意,没有生意面馆就只有关门大吉。
妻子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每天清晨七点到八点之间,她都会爬上我们三单元的楼顶平台,把烧过的蜂窝煤狠狠的砸了下去,面馆长长的遮阳篷就会发出一声巨响,巨大的震动会使得正在吃面的食客个个惊慌失措,人人躲避不及。一阵惊呼,一阵骚动,正是面馆生意最好的时段,女老板只得忍气吞声,极力做食客们的安抚工作。到了中午,才开始破口大骂,发誓就是生意不做了,也不会放过妻子。妻子就尝到了甜头,听从我的劝阻,不再与其对骂,只是每天清晨就穿戴整齐,雄赳赳,气昂昂的提着烧过的蜂窝煤,爬上楼顶平台去继续从事“恐怖活动”。
效果是明显的,虽然不能说这一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房地产工程的相继完工,外来的民工已经转移工地,加之刘家大堰小学开始放暑假,送学生而光顾面馆的家长不见了踪影,还有妻子每天造成的巨大震动,每次食客都作鸟兽散,面馆的生意终于做不下去了。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宜昌第二次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重庆红油面馆无声无息的搬走了,连遮阳篷都折走了,只有满地的油污,一些用过的筷子和狼藉的煤灰,还能看出这里曾经有个面馆存在过。
起码这是环保的胜利,所以记下了这一过程。
2006…7…3
一地鸡毛 老父八十
老父说他老人家今年八十,这样的说法叫人有些诧异。他老人家是1929年生人,按照北方风俗,“男做进、女做满”,也应该是明年,但老爷子的话谁也不敢违抗,今年就今年,他老人家可是我们家里的绝对权威。
老父是河北省保定地区易县大磐石村人。老家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三:其一,易县是清西陵所在地,说明风水好;其二,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故事发生于此,说明这里的男人全是铮铮铁骨;其三,走出了我老父他老人家。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所以才有了我们宜昌的王家。
我没有回过老家,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带着弟弟回去过,留下很多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的印象。我就从他们无数次的回忆之中,勉强拼凑起老家的写意图:村口的老槐树的书也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家是简陋的土坯房,人很多,除了奶奶,全是男性,很热闹的。吃饭的时候,一人一碗小米粥,一张煎饼;晚上,热炕上齐刷刷躺着四个半大的小伙子,门前的拒马河清澄见底,不远处,太行山巍然耸立。
老爷爷家有四个儿子,大伯一生务农,据说身体一直很硬朗;二伯是参军走的,从解放军到志愿军,从东三省到朝鲜半岛,已经是师长的他没能胜利凯旋,成了为国捐躯的烈士;父亲在家排行老四,从小心灵手巧,读书成绩好,又是儿童团长,还编得一手好凉席,后来就跟着干部工作团南下了;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我们称为六叔。
老父的前半生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从通讯员、干事开始,没几年就平步青云,先后当上了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有些老人告诉我,肃清**的枪毙犯人的布告上就是我父亲签署的大名。反右运动是老父的第一次挫折,他被罢官免职,发配到东山苗圃劳动改造,在那里,他的一条腿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被马车压断过。
我的记忆完全是只零破碎的,父亲的形象几乎看不太清楚。最大的可能就是他那时很忙,我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家出门了,然后是母亲,我也要上幼儿园;我晚上玩累了,躺在外婆被窝里呼呼睡着了,他还没回家。我只记得母亲把我们兄弟俩领到一条街上,路灯闪烁着,她指着一个瘦高的男人对我们说:“叫爸爸。”
那时,老父已经被平了反,正在等待重新安排工作。我记得那时我们度过的一段最温馨的家庭生活。放学了,背起书包就飞奔回家,父亲已经把窝窝头蒸好了,玉米面的,黄橙橙的,甜滋滋的,楼梯的转弯处有一个老人在唱:“小燕子,穿花衣”,那是在南正街的事;后来是解放路,父亲绘声绘色的给我们念那本小说《智取华山》。
第二次对老父的打击不是来自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批斗,不是来自那些挥舞着枪支冲进我家抓人的造反派,而是由于我的不幸给他带来的痛苦和悲哀。他不得不在宜昌和武汉之间来回奔波,那个时候,我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父亲得照顾我的全部的吃喝拉撒,还得应付造反派的责难,说实话,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父亲身上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和困难,那是可想而知的。
老父是坚强的。一次又一次的被困难打倒,一次又一次的从挫折中站起来,那是一种百折不回的刚强和坚持到底的韧劲。文革期间,他老人家主持了工交办的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主持公检法,直到改革开放的副市长、人大副主任。老父带着北方汉子特有的直爽与倔强,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在当今这种社会里,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就显得有些孤芳自赏。
母亲患病瘫痪以后时很痛苦而又无奈的,一个以精干强悍而组成的女强人的内心的确很伤心的。这时就显现出老父温情脉脉的另一面了。无论在医院还是在家里,都能看见他老人家握着母亲消瘦的手,喃喃地对她说些琐碎的家常话,那种温馨是感人至深的,也是真挚情感的流露,很令人羡慕的。
老父是伟大的。他老人家首先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在他面前,我们兄弟俩人至少在表面上是服服帖帖的,而且试图把这种威严继承发扬光大,弟弟成功了,我失败了;他老人家有些独往独来的气质,对于自己认定的目的,一定力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