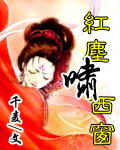西窗烛话-第1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仙桃在江汉平原中部,318国道横贯东西,在这条路上走车是很惬意的,路况良好,视线开阔,路旁的行道树树大叶茂,车跑起来一溜烟。唐老鸭就经常嘲笑开天津130双排货车的小郭是“开飞机的”,就是指的这段路。夏天的正午时分,将车停在树荫下,路旁摊贩卖的西瓜又大又甜;冬季,平原上的风刮得厉害,无论车停在哪家餐馆门前,都会有女孩子为你拉开车门,殷勤的笑脸相迎:“欢迎光临”。
当时在公司里,我与继华好的穿一条裤子。他是红安人,军队转业去的宜昌,他的父母兄妹都在仙桃的汉江造船厂工作,我便经常与继华在出差的途中到此停留。早上,已经退休的他家的父母在一条小街的路边摆上小吃摊,油饼,油条,面窝,油香,还有豆浆。我们就坐下来,饱饱的吃顿早餐;晚上,我们会来到棚户区的低矮的平房里,抽着烟,望着门前那棵枝叶茂密的大树和竖着篱笆的小菜园,与他的父亲,弟弟拉家常,而他的母亲会领着他的大妹妹忙着给我们做饭。
后来,我单独到武汉,也顺道去仙桃他家,带点东西去,带点东西回,就与他家的关系更熟悉了,大妹妹也会与我说说笑话了,她已经有了男朋友,也是汉江造船厂的。再后来,继华当上了公司经理,一天晚上,我们两人还从宜昌专程去过仙桃,乘的是长途班车,第二天中午就回来了,悄悄的去,悄悄的回,谁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为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陪同而已。
从武汉回宜,过了仙桃就是潜江市。那是一个优雅的城镇,街道四通八达,建筑错落有致,一些杉树直挺挺的,也叫亭亭玉立,随便走进一家餐馆,女服务员都会极力推荐当地的名酒《园林青》,果酒乎,白酒乎,保健酒乎?三不像,于是以后拒绝喝这种酒,但个个餐馆还是会不遗余力地继续推荐。
318国道也是从潜江横贯而过,又平又直。曾经当过宜昌市副市长的崔传理以前也当过五中的校长,花白的头发,慈祥的笑容,他有一大堆孩子,三个男孩与我很熟悉。崔校长后来凭着民主人士的身份当上副市长,一家人就搬到我家的楼上,很热闹的,每天上下楼彼此都乐呵呵的打招呼。可惜好景不长,崔副市长在带领政协一帮人到武汉去的路上,就是在潜江遇车祸身亡,一辆面包车,偏偏就死了他,真是遗憾。他的那一家子人也很快地从政府机关大院里消失了,这就是规律。
从武汉回宜,我还走过一条奇怪的线路。那是从汉口斜斜的擦着云梦,再从盛产纯碱,食盐和石膏的应城经过,过了汉宜路口,就是天门县的皂市镇,那是由无数占道经营的摊贩和密密麻麻的人群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集贸市场。我们乘坐的班车一下子陷进了人流,噪声,塞车之中动弹不得,进退两难。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警察,几声喝斥,几个手势,混乱奇迹般地消失了,交通又恢复了秩序,人群全都上了人行道,车辆鱼贯而行,完全不相信刚才的一幕曾经存在过。
再向前走,又窜到京山县境内了,过了钱场镇,就是五三农场了。那里有成片的良田,整齐划一的灌溉沟渠,一排排高大的树木,就连农场职工的孩子都似乎比农村的小孩多了几分天真无邪,多了几分童趣。有人骑着自行车,但大多数人则挤在手扶拖拉机的车斗里,蹦蹦跳跳的前进。班车从钟祥县向西,就是沙洋了。江汉平原结束了,丘陵开始了,再向前,就是鄂西山区,就是荆门,就是宜昌了。
六六大顺 29.鄂西三弄(上)
我是鄂西的常客,细细数来,除了宣恩和咸丰,其他的县市都去过。那高耸入云的大山,清澈见底的溪流,朴实无华的乡亲,贫穷落后的事实和沿途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从宜昌出发,走过三条到鄂西的路。一条从长阳经过,在八字岭进入巴东县境,班车在一个劲的上坡,马达轰鸣,车身都在颤抖,一点点向上挪动。夏天,路旁树荫下有加水站,但凡到鄂西,不加做一个水箱,不加满水,下坡路时就会刹车失灵,崎岖山路上,那可是车毁人亡的惨案;冬天,路边的木板房里有人叫卖或者租借防滑链,如果不把轮胎带上这些稀里哗啦的铁链,失去了抓力的轮胎就会径直滑下万丈深渊,曾经有武汉的司机来到这里,权衡再三,毅然原路返回。
将漫长的山坡上到一大半的时候,就到了杨岔坝,那里有一座庄严耸立的筑路纪念碑,一栋外墙粉刷得雪白的两层楼,楼下是农资商店,楼上是旅社,胡耀邦在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乘车从此路过,执意住过一夜。我们也住过,房间陈旧,灯光昏暗,上下楼走的声响很大,得用手电筒照路,夜里很安静,守夜人的咳嗽声,还有狗在不耐烦的吠叫。从小窗户望出去,黑洞洞一片。
向里走四公里就是野三关,我们真的是走去的,不过比起志坚自称曾经走到清太坪而言,还是自愧不如。那是一个繁华的农村集镇,晚饭吃得不太好,夜幕低垂,有录像厅,棋牌室,一家小型舞厅闪烁着暧昧的灯光,我们就住在汽车站对面的一家旅社,被褥潮湿,还有些霉味,很不舒服,第二天我们就走了,乘车返回杨岔坝,坐在公路拐弯处的一家小店吃面,味道不错,暖和极了。路边有山民卖柿子,通红的小山柿,好看得很,一抬头,光秃秃的树枝上还挂着山核桃。
继续前行,在高店子驶入了建始地界。途经的最大的集镇无疑是红岩寺,但怎么也没看见寺庙的影子,倒是沿公路用石块砌成高高的护坎,一些衣着简陋,脸上布满皱纹的山民就呆呆的站在与我们汽车顶棚一般高的护坎上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车上的每一个人,是在与他们之间的一个人说话,那个人在笑,皱纹在眼角跳动,露出一口的黄斑牙,手舞足蹈的,鄂西话尾音很难听。
过了崔坝,就进入了恩施的地盘。已是大山深处,汽车在一些不大的山间盘旋,有时还驶过一片沉寂的森林,太阳升起来了,景致很美,农田越来越多,有些还是不大的水田,阳光下晃动着水的反光。一过龙凤镇,路旁也变得越来越热闹了。翻开恩施地图,很容易就发现那里的山民很喜欢“坪”,“坝”之类的地名,也许在山上呆惯了,想到平地走走,平地也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恩施市的地名就叫七里坪。
恩施市在疯狂的扩张,一条清江将城区分出新旧。新区是很大气的,水泥路,人行道边还有刚刚栽下不久的小树苗,两边耸立着一些崭新的建筑,无非是银行,电力,工商,医院之类的,还有一些商铺,规模都不大,但林林总总,从时髦的吊灯到白事的花圈,相安勿躁,班车愉快地在整洁的新区行驶,只是人气不足。过了清江就是老城区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在所有城市都能看见的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里依然存在:住宅楼晾晒的衣物就像万国旗;音像店将最新单曲放得震耳欲聋;几个菜贩蹲在街头墙角满怀希望的望着每一个经过这里的行人;警察吹着口哨将一辆货车拦住,示意司机停到路旁接受处理;一家店里有女人吵架,看热闹的立刻挤了个水泄不通;乞讨的在地上摆着诉说自己悲惨命运的纸板,胡琴声如歌如诉。
我们总是行程匆匆,好像只在恩施住过一晚,那是从建始过来,天已经很晚了,就在老城区汽车站前胡乱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了。夜里热闹得很,音响就在楼下拼命的歌唱,汽车喇叭响个不停。我们信步走进一家饭馆,努力想吃特色菜,一个满脸横肉的女人向我们介绍了半天,没一样瞧得上眼,只得胡乱点了几个菜。苞谷酒是红岩寺的,度数很高,进口很辣,喝得人直皱眉头。我们带着一些酒意走到清江大桥上,在宜都已经汇成浩浩荡荡的清江在这里只是一条小溪罢了,俯身向下望,很深,看不清楚,夜里的清江就只是一条黑色的水带,听得见水流哗哗。感觉旁边有人,回头望去,原来是个算命占卜的盲人,没等他开口我就走开了,我一向怀疑他们能否理解《周易》的真谛。
从恩施到利川,过了鸭松溪就一个劲的上坡。山区的班车大同小异,外表陈旧,沾满斑斑泥巴和点点柏油,还有乘客晕车呕吐后留下的痕迹,有些地方还破出了裂缝,但发动机是强劲的,轰鸣着翻越一个个山头,刚刚擦过一座1600米高山,没等喘过气,就又开始上山。班车很费力的在Z字型的盘山道上扭来扭去,发动机燃烧不充分,整个车厢里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山区公路总是石渣路,有些地方是在笔直的悬崖上开凿出来的,窄的仅仅只能通过一辆车,于是下坡的车辆总是得先找个一个宽点的地方停住,让已经精疲力倦的上坡车先过。这是一段足有二十公里长的上坡山路,偶尔不经意地朝下望,着实吓人一跳,已经车行了几十分钟过去,我们曾经在上山前加过水的道班和那家卖烟和汽水的商店依然还在山下晃动,只是变小了许多,变得只有火柴盒大小了。我多次经过这里,每一次都心惊胆颤,也为那些不知名的筑路工人肃然起敬。
过了石板岭就属于利川地界了,这里基本上已经没有大山,一些小山包稀稀落落的长着一些不大的松树,道路变宽了,路边开始出现一些简陋的两层的木屋,底层又臭又脏,喂养着一些个头不大的土猪,上层住人,黑洞洞的窗户里什么也看不见。车过了团堡,这是一个很小的镇子,每次当我们从利川乘车离开,途中经过团堡时,都会有山民气冲冲的拦停班车,上车找人,因为是第一班离开利川的班车,他们检查得很仔细,每个乘客都被端详再三,真的还被他们找到过,有男有女,拖下车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班车赶紧关门,加大油门溜之大吉,车上的人议论纷纷,是私奔,还是拐卖?或者是擅自出门打工?司机也在插话:“他们买的是到宜昌的车票。”
利川到了,真的是一马平川。中心城区从十字街头潇洒地向东西南北延伸,楼都不太高,修得结实极了,街上店铺林立,人多也就热闹,似乎比恩施还繁华一些。我们糊里糊涂选中了汽车站附近的一家旅社,高高的楼梯,就住在二楼,旅客不多,冷冷清清的,跑到街上风光了一番,晚上蒙头就睡,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被噪音吵醒了,叫卖声,谈笑声,马达声,喇叭声,咒骂声,甚至还有人喊劳动号子。朦朦胧胧的爬起来,推窗一看就自认倒霉了,原来我们的楼下就是一个集贸市场。
十字街头有一家电影院,高高的蓝色玻璃幕墙,大幅的电影海报,放映厅不太大,白天看电影的人总是不多,木靠椅上最多也就三成的上座率,看的什么不记得了,反正是混时间,反正是流行片,不是外国的爱情片就是港台的武打片;从电影院出来,就到一家饭馆吃饭,人真多,送水的服务员是个小女孩,未成年,忙得团团转,从老板兴奋得满面红光就知道生意好得出奇,这是家重庆人开的火锅店,叫了个牛肉火锅,吃了一口,差点没把眼泪给辣出来,吹吹火锅上热气腾腾的蒸汽,一层红辣椒,一层油亮亮的红油,看上去叫人心惊肉跳;饭后逛商店,利川最有名的就是棕垫,铺在床上的那种,当时嫌土气而放弃,等到琢磨出棕垫的好处后我又再没去过利川。
六六大顺 30。 鄂西三弄(中)
从宜昌到鄂西的第二条路是乘船到巴东,据说除了乘飞机飞来飞去以外,恩施的官员出出进进大都选择从巴东而行。我很喜欢那个贴在长江边上的,也悬在半山腰之上的小县城,高高的上岸台阶从江边一直向上延伸,而从船上看更是显得古老,奇特,有一种威严感。喘着气爬上岸,那么朴实而热闹的街道就会隆重的在游客面前展开,每每乘船路过,总爱在趸船上买些柚子,柿饼,香干之类的。有次在秭归(也就是如今的归州)等回宜的船,一时兴起,居然跳上上行的客轮跑到巴东,逛逛街,吃吃饭,买上几串柿饼,再心满意足的离去,想想也是匪夷所思的。
巴东县城不大,信陵镇仅有俩条并行的街道,临江的是商业街,人来人往,从早到晚喧哗得很,政府机关在上面一条街,银行,医院,学校也在那条街上,两条街之间有无数狭窄的小巷和高低不平的卵石阶梯相连接,还有巨大的背篓,一些精瘦,黝黑的汉子就凭那巨大的背篓居然将一栋小楼所需的全部建筑材料,包括砂石,红砖,水泥一起从江边运上来,那是何等的壮举!当时巴东县城已决定搬迁到山后加油站那一片斜坡上,已经动工后尴尬的发现那里原来是滑坡危险区,只得再择县址。,
我在信陵镇住过两次,一次是在汽车站旁边那栋五层建筑楼上的旅社,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