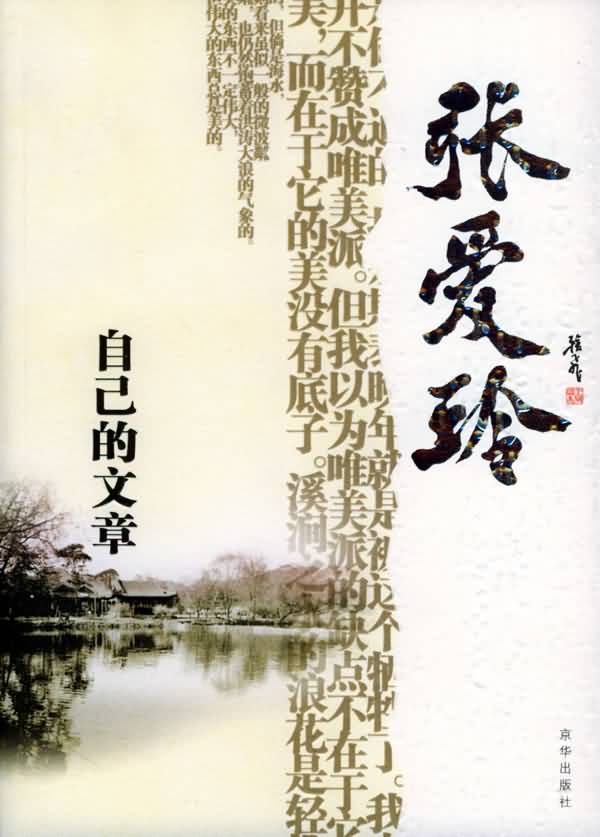三毛文集-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选自三毛散文集《高原的百合花》
我的写作生活
——谈话记录之二
晚上七点半。外头是倾盆大雨。
在耕莘文教院的讲堂里,原只安排两百个的座位,却挤了不下六百人,大门口是怎么都挤不进去了。文教院的陆达诚神父陪着主讲人三毛女士在前头领路,嘴里一迭声嚷着:
“对不起,请让路!请让路!”
三毛依然长发披肩,黑色的套头毛衣下是件米色长裙,脸上有着淡淡的妆,素净中更透着几分灵秀。瞧着讲堂中拥挤的情况,三毛紧张了,直问人:“我要不要带卫生纸上台?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我怕我自己会先‘下雨’。”三毛是担心面对这么多人演讲时,说着说着会控制不了情绪而流泪,她却说成“自己先下雨”,倒教旁人先笑开了。
站在讲台上,三毛用一贯低低柔缓的声调,对满堂或坐、或站、或席地的朋友说:“没想到我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朋友,尤其今晚外头的雨这么大。”然后三毛就开始演说今晚的讲题:我的写作生活。
下雨天看到这么多朋友真好
各位朋友:
很抱歉今天晚了一刻钟才开始,我是很守时的人,刚刚我一直在等陆神父来带我。
最近我的日子过得很糊涂,一直记不清是哪一天要演讲,直到前天有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后天在耕莘文教院见。
我吓了一跳,不过,我那时想,没关系,大概只有二十个人。
可以随便说说,可是没想到我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朋友。
今天又在下雨,听说这一阵台北不是雨季,可是我回来以后,发觉总是在下雨。我以为今天不会有那么多朋友来,看见你们,我很怕,一直想逃走。
希望我的话对各位不会有不好的影响过去我教过书,常上讲台,但教书的时候有课本,现在跟各位说话没有课本,我担心今天随口所说的,对各位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我特别要提出一位年轻读者的来信,做为今天这个谈话的开始。刚回台湾时,我收到一位高中女生的来信,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这位读者说她在初三的时候,因为升学压力太重而想自杀,在那个时候,她看了我的书,因而有了改变,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改变,可是她一直说是我的书救了她。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笨”,因为,任何一本我的书都救不了你,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别人不能救你的。她说她现在已是高中生了,而最近我丈夫的去世,她说她觉得人生还是假的,她还是要死。我收到这封信好几个月了,一直不知怎么回信,可是我很挂念这位朋友,因为她的信写得很真诚。希望她还是把我忘记吧,因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不知道这位朋友今天有没有在场,或是有她的朋友,请转告她,信收到了,并请她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别人的遭遇毕竟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从未立志做作家,倒曾下过决心要当画家的妻子今天的讲题是“我的写作生活”,我实在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把我当作家看,这种改变,使我很不习惯,而且觉得当不起。作家应该是很有学问或是很有才华的人,我呢,做了六年的家庭主妇,不曾是专业作家,以后也不会是。
我从来没有立志要做作家。小时候,父母会问,师长会问,或者自己也会问自己:长大了要做什么?我说就要做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太太。“有没有对象呢?”他们会问,我说:
“有的。”“是谁呢?”“就是那个西班牙画家毕卡索!”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美术。以后,写作文的时候,我总说要做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妻子,并没有说自己要成为艺术家。我的功课不行,数学考零分,唯一能做得好的只有国文,班上同学大约有十个人的作文是我“捉刀”的小时候,数学成绩很不好,常常考零分,有一次考得最高分是五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应该也是零分才对。我的作文好,小学五年级时参加演讲的演讲稿是自己写的,每次壁报上一定有我的作品,我的家庭很幸福,可是有一次,我把老师感动得流泪了,因为我告诉他我是孤儿,还写了大约有五千字的《苦儿流浪记》。
进了初中以后,班上同学大约有十个人的作文是我写的。
因为他们写不出来,我就说拿来拿来,我替你写。后来,又学写唐诗,在作文本上写了十几首。我发觉自己虽然别的事做不好,但还可以动笔,这是一条投机取巧的路。
初二时,不喜欢学校生活,离开学校自己念书。到了大学,我跟许多高中毕业的同学一起念哲学系,发现我的国文比不上他们,大一的国文考试,《春秋》是什么时候,谁写的作品之类的题目,我都不晓得,所以国文就不及格了。后来我去找老师,我说:“老师,我是少年失学,不知道《春秋》是什么时代修的,我觉得这是文学史的问题。”老师说:“你应该晓得的呀!”我说:“对!我知道的也是国文类的,可是并不是这一类的。”后来他说:“那你要补考罗。”我说:“补考还是不会及格的,只有一个方法,我可不可以补给你六篇作文。”他问我要写多少字,我说随我写吧。
瞎编的故事竟把老师感动哭了后来,我写了一篇三万多字,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童年生活,从我的祖父开始讲起,中间还有恋爱故事,其中我伯父并没有恋爱,是我编的。
老师要求我用毛笔写,我写不来,就用签字笔写成毛笔字的味道。这篇写得非常好,故事有真有假,还有情节,老师看了,把我叫过去,说:“你是我的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你写的关于上一代的事,都是真的吗?”我就说:“真假你还是别管吧,这篇作品你还喜欢吗?”他说:“老师看了很感动,一夜没有睡觉,老师都流泪了。”
我很幸运,打小学到现在投稿没被退过这件事以后,我发现自己从小做什么事都不对劲,不顺利,最顺利的事就是写文章,因此,在大学里我就开始写文章,但也不是很勤的。我有一个很光荣的纪录是从小学开始投稿,到现在还没有被退过稿。
我的青少年时代出了一本书《雨季不再来》,这本书是被强迫出版的,因为如果我不出书,别人也可以把那些文章辑成一个集子出书,而我连版税都拿不到。其实那些东西都很不成熟,都不应该发表,是我在二十二岁以前发表的文章,文字非常生涩,感情非常空灵,我不喜欢空灵这两个字,但那是那个时期我写时所不能伪装的一些感情,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写作在我生活中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它是蛋糕上面的樱桃然后,我离开台湾到西班牙去,生活的改变以及其他一些事,使我停笔了。有位朋友每回写信总说,你不写实在太可惜了,因为你才刚刚开始写。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正在改变中,这时候不想写东西,免得将来后悔。这位朋友是个编辑,他说,好的,我等你,我要等你几个月呢?我说:你慢慢的等。这一等,等了十年。
有一天,我坐在沙漠的家里,发觉我又可以写作了。所以,我觉得等待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不要太急。现在又有朋友在问我:三毛,你又不写了,要多久才会再写呢?我说,你别急,等我。他说:要等多久呢?我说:大概要另外一个十年。他一听,马上说:那不是等死了吗?我说:这究竟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如果硬逼着我写,反而写不好,而十年以后,我也许又是另一个面目出现了。
我认为写作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有人问我:你可知道你在台湾是很有名的人吗?我说不知道,因为我一直是在国外。他又问:你在乎名吗?我回答说,好像不痛也不痒,没有感觉。他就又问我,你的书畅销,你幸福吗?我说,我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福,这些都是不相干的事。又有别人问我,写作在你的生活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吗?我说:它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他又问:如果以切蛋糕的比例来看,写作占多少呢?我说:就是蛋糕上面的樱桃嘛!
生活比写作重要;我重视生活,远甚写作也许,各位会认为写作是人生的一种成就,我很真诚的说一句:人生有太多值得追求的事了,固然写出一本好书也可以留给后世很多好的影响。至于我自己的书呢,那还要经过多少年的考验。我的文字很浅,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就可以看,一直看到老先生,可是这并不代表文学上的价值,这绝对是两回事。
有一年,我正在恋爱,跟我的荷西走在马德里的一个大公园,清早六点半,那时我替《实业世界》写稿,那天已到交稿的最后一天了,我烦得不得了。我对荷西说:明天不跟你见面了,因为我一定要交稿了。荷西说:这样好了,明天清早我再带你来公园走,走到后来,你的文章就会出来了。我继续跟他在公园里走,可是脑子一直在想文章的事,这时,看到公园的园丁,在冬天那么冷的清早,爬到好高的树上锯树。
我看了锯树的人,就对荷西说:他们好可怜,这么冷,还要待在树上。荷西却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那些被关在方盒子里办公,对着数目字的人,才是天下最可怜的。如果让我选择,我一定要做那树上的人,不做那银行上班的人。
听了荷西的这番话,我回家就写了封信给杂志编辑说,对不起,下个月的专栏要开天窗了,我不写了。
写作只是我的游戏之一
所以我是一个很重视生活的人,远甚于写作,写作只是我的游戏之一。别人也许会问:你是不是游戏人生呢?我要说:我是游戏人生。来到这个世界本就是来玩的,孔子就说“游于艺”,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意义,用最白话的字来说就是玩。我说的玩不是舞厅的玩,也不是玩电动玩具的玩,或者抽大麻的那种,不是,我的人生一定要玩得痛快才走,当然走不走不在我,但起码我的人生哲学是做任何事一定要觉得好玩地才去做,绝不会为了达成一个目的,而勉强自己。我说这话是非常紧张的,这句话说出来很不好,但这只是对我自己,不是对别人,而且我的人生观是任何事情都是玩,不过要玩得高明,譬如说,画画是一种,种菜是一种,种花是一种,做丈夫是一种,做妻子也是一种,做父母更是一种,人生就是一个游戏,但要把它当真的来玩,是很有趣的。
很多人看了我的书,都说:三毛,你的东西看了真是好玩。我最喜欢听朋友说“真是好玩”这句话,要是朋友说:你的东西有很深的意义,或是说——,我也不知怎么说,因为很少朋友对我说这个,一般朋友都说,看你的东西很愉快,很好玩。我就会问:我写的东西是不是都在玩?他们说:是啊。
一个小朋友告诉我:“你写的东西好好玩!”我觉得这是一种前不久我碰到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朋友,他说:你的东西很好玩。我觉得这是一种赞美,过去写的东西不好玩,像《雨季不再来》,因为年纪轻不知道怎么游戏人间,过了好苦闷的青少年时代。后来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时间,过一天就短一天,我一定要享受人生。怎么享受呢?像我的《沙漠中的故事》,对不起,又提我的书。第一篇《沙漠中的饭店》就是玩做菜,第二篇《结婚记》是如何结婚,扮家家酒,第三篇写在沙漠里替人看病,也是玩,还有一篇很好玩的叫《沙漠观浴记》,看当地的人如何洗澡。这些东西都是在心情很好时,发现自己的生活这么美丽,为什么不把它写出来呢?不知不觉就写出来了,并没有所谓的“使命感”或是“文以载道”,我都没有。
虽然我写的都是些平淡的家庭生活,很平淡,但有一点不得不说,很多生活枯燥的朋友给我来信说我的文章带给他们快乐,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文章。我是基督徒,我要感谢天地的主宰——我们称为神,因为它使我的生活曾经多彩多姿过,至于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
为什么我的笔名叫“三毛”?停笔十年后第一次投稿被刊出的我来说说停笔十年后,第一次投搞到《联合报》,刊出来的感觉。写稿的时候还不知道该用什么名字,我从来不叫三毛,文章写好后,就想:我已不是十年前的我了,改变了很多,我不喜欢再用一个文诌诌的笔名,我觉得那太做作,想了很久,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干脆就叫三毛好了。后来又要跟荷西解释三毛是什么意思,结果他听懂了,他画了一个人头,头上三根毛,说:三毛就是这个吗?我说:是呀!
荷西说:哎呀,这一向是我的商标嘛!
这篇文章寄出以后,一直患得患失,心理负担很重,我知道这不是一篇很有内容的文章,只是比较俏皮一点而已。结果,十天后,我接到寄至撒哈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