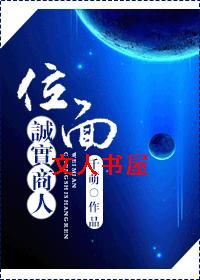红顶商人胡雪岩-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家都叫我老何。”
“老何,我姓萧,跟你老人家老实说吧,我是来救杭州百姓的——也不是我,是你们杭州城里鼎鼎大名的一位善人做好事;带了大批粮食,由上海赶来。教我到城里见王抚台送信。”萧家骥略停一下,摆出一切都豁出去的神态说:“老何,我把我心里的话都告诉你,你如果是长毛一伙,算我命该如此,今年今月今日今时,要死在这里。如果不是,请你指点我条路子。”
老何听他说完,沉思不语,好久,才抬起头来;萧家骥发觉他的眼神不同了,不再是那黯然无光,近乎垂死的人的神色,是闪耀着坚毅的光芒,仿佛一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那方寸眸子中似的。
他将手一伸:“信呢?”
萧家骥愕然:“什么信?”
“你不是说,那位大善人托你送信给王抚台吗?”“是的。是口信。”萧家骥说,“白纸写黑字,万一落在长毛手里,岂不糟糕?”
“口信?”老何踌躇着,“口信倒不大好带。”“怎么?老何,”萧家骥了解了他的意思:“你是预备代我去送信?”
“是啊?我去比你去总多几分把握。不过,凭我这副样子,说要带口信给王抚台,没有人肯相信的。”
“那这样,“萧家骥一揖到地,“请老何你带我进城。”“不容易。我一个人还好混;象你这样子,混不进去。”“那末,要怎样才混得进去?”
“第一、你这副脸色,又红又白,就象天天吃大鱼大肉的样子,混进城里,就是麻烦。如果,你真想进城,要好好受点委屈。”
“不要紧!什么委屈,我都受。”
“那好!”老何点点头,“反正我也半截入土的了,能做这么一件事,也值!先看看外头。”
于是静心细看,人声依旧相当嘈杂,但枪声却稀了。“官军打败了。”老何很有把握地说,“这时走,正好。”
萧家骥觉得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听一听声音,就能判断胜负,未免过于神奇。眼前是重要关头,一步走错不得,所以忍不住问了一句:“老何,你怎么知道?”
“我早就知道了。”老何答道:“官军饿得两眼发黑,哪里还打得动仗?无非冲一阵而已。”
这就是枪声所以稀下来的缘故了。萧家骥想想也有道理,便放心大胆地跟着老何从边门出了长毛的公馆。
果然,长毛已经收队,满街如蚁,且行且谈且笑,一副打了胜仗的样子。幸好长毛走的是大街,而老何路径甚熟,尽从小巷子里穿来穿去,最后到了一处破败的财神庙,里面是七八个乞儿,正围在一起掷骰子赌钱。
“老何,”其中有一个说,“你到没有死!”
老何不理他,向一个衣衫略为整齐些的人说:“阿毛,把你的破棉袄脱下来。”
“干什么?”
“借给这位朋友穿一穿。”
“借了给他,我穿啥?”
“他把他的衣服换给你。”
这一说便有好些人争着要换,“我来,我来!”乱糟糟地喊着。
老何打定主意,只要跟阿毛换;他的一件破棉袄虽说略为整齐些,但厚厚一层垢腻,如屠夫的作裙,已经让萧家骥要作呕了。
“没有办法。”老何说道:’不如此就叫不成功。不但不成功,走出去还有危险。不要说你,我也要换。”听这一说,萧家骥无奈,只好咬紧牙关,换上那件棉袄,还有破鞋破袜。萧家骥只觉满身虫行蚁走般肉麻,自出娘胎,不曾吃过这样的苦头,只是已穿上身,就决没有脱下来的道理。再看老何也找人换了一身衣服,比自己的更破更脏,别人没来由也受这样一分罪,所为何来?这样想着,便觉得容易忍受了。
“阿毛!”老何又说:“今天是啥口令?”
“我不晓得。”
“我晓得。”有人响亮地回答,“老何,你问它做啥?”“自然有用处。”老何回头问萧家骥:“你有没有大洋钱,摸一块出来。”
萧家骥如言照办;老何用那块银洋买得了一个口令。但是,“这是什么口令呢?”萧家骥问。
“进城的口令。”老何答道,“城虽闭了,城里还是弄些要饭的出来打探军情,一点用处都没有。”
在萧家骥却太有用了;同时也恍然大悟,为何非受这样的罪不可?
走不多远,遥遥发现一道木城;萧家骥知道离城门还有一半路程。他听胡雪岩谈过杭州十城被围以后,王有龄全力企图打开一条江路,但兵力众寡悬殊,有心无力。正好张玉良自富阳撤退;王有龄立即派人跟他联络,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张玉良从江干往城里扎营;城里往江干扎营,扎住一座,坚守一座,不求速效而稳扎稳打,总有水到渠成,联成一气打开一线生路的时候。
由于王有龄的亲笔信,写得极其恳切,说“杭城存亡,视此一举,不可失机误事,”所以张玉良不敢怠慢,从江干外堤塘一面打、一面扎营,扎了十几座,遭到一条河,成了障碍,张玉良派人夺围进城,要求王有龄派兵夹击;同时将他扎营的位置,画成明明白白的图,一并送上。王有龄即时通知饶廷选调派大队进城;谁知饶廷选一夜耽误,泄潜心机密,李秀成连夜兴工,在半路上筑成一座木城,城上架炮。城外又筑土墙,墙上凿眼架枪,隔绝了张玉良与饶廷选的两支人马;而且张玉良因此中炮阵亡。
这是胡雪岩离开杭州的情形,如今木城依旧,自然无法通过;老何带着萧着骥,避开长毛,远远绕过木城,终于见了城门。
“这是候潮门。”
“我晓得。”萧家骥念道:“‘候潮’听得‘清波’响,‘涌金’‘钱塘’定‘太平’。”
这两句诗中,嵌着杭州五个城门的名称,只有本地人才知道;所以老何听他一念,浮起异常亲切之感,枯干瘦皱,望之不似人形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笑容,“你倒懂!”他说,“哪里听来的?”
萧家骥笑笑答道:“杭州我虽第一次来,杭州的典故我倒晓得很多。”
“你跟杭州有缘。”老何很欣慰地说,“一定顺利。”
说着话,已走近壕沟;沟内有些巡逻,沟外却有人伏地贴耳,不知在干什事?萧家骥不免诧异却步。
“这些是什么人?”
“是瞎子。”老何答道,“瞎子的耳朵特别灵;地下再埋着酒坛子,如有啥声音听得格外清楚。”
“噢!我懂了。”萧家骥恍然大悟,“这就是所谓‘瓮器’,是怕长毛挖地道,埋炸药。”
“对了!快走吧,那面的兵在端枪了。”
说着,老何双手高举急步而行;萧家骥如法而施,走到壕沟边才住脚。
“口令!”对面的兵喝问。
“日月光明。”
那个兵不作声了,走向一座轴驴,摇动把手,将一条矗立着的跳板放了下来,横搁在壕沟上,算是一道吊桥。
萧家骥觉得这个士兵,虽然形容憔悴,有气无力,仿佛连话也懒得说似的,但依然忠于职守,也就很可敬了;由此便想:官军的纪律,并不如传说中那样糟不可言。既然如此,何必自找麻烦,要混进城去。
想到就说:“老何!我看我说明来意,请这里驻守的军官,派弟兄送我进去,岂不省事?”
老何沉吟了一下答道:“守候潮门的曾副将,大家都说他不错的;不妨试一试。不过,“老何提出警告:“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也是实话。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晓得;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自讨苦吃。”
“不会,不会!我的话,货真价实;那许多白米停在江心里,这是假得来的吗?”
听这一说,老何翻然改计,跟守卫的兵士略说经过,求见官长;于是由把总到千总,到守备,一层层带上去,终于候潮门见到了饶廷选的副将曾得胜。
“胡道台到上海买米,我们是晓得的。”曾得胜得知缘由以后,这样问道:“不过你既没有书信,又是外路口音,到底怎么回事,倒弄不明白;怎么领你去见王抚台?”萧家骥懂他的意思,叫声:“曾老爷!请你搜我身子,我不是刺客;公然求见,当然也不是奸细。只为穿越敌阵,实在不能带什么书信,见了王抚台,我有话说,自然会让他相信我是胡道台派来的。如果王抚台不相信,请曾老爷杀我的头。我立一张军令状在你这里。”
“立什么军令状?这是小说书上的话。我带你去就是。”曾得胜被萧家骥逗得笑了;不过他的笑容比哭还难看。“是!”萧家骥响亮地答应一声,立即提出一个要求,“请曾老爷给我一身弟兄的棉军服穿!”
他急于脱卸那身又破又脏的衣服;但轻快不过片刻,一进了城,尸臭蒸熏,几乎让他昏倒。
王有龄已经绝望了!一清早,杰纯冲过一阵——就是萧家骥听到枪声的那时刻;十几船活命的白米等着去运,这样的彭励,还不能激出士兵的力量来,又还有什么人能开粮通道,求得一线生路?
因此,他决定要写遗折了:窃臣有龄前将杭城四面被围,江路阻绝,城中兵民受困各情形,托江苏抚臣薛焕,据情代奏,不识能否达到?现在十门围紧,贼众愈聚愈多,迭次督同饥军,并密约江干各营会合夹击,计大小昼夜数十战,竟不能开通一线饷道。城内粮食净尽,杀马饷军,继以猫鼠,食草根树皮,饿殍载道,日多一日,兵弁忍饥固守,无力操戈。初虞粮尽内变,经臣等涕泣拊循,均效死相从,绝无二志,臣等奉职无状,致军民坐以待毙,久已痛不欲生。
写到这里,王有龄眼痛如割,不能不停下笔来。他这眼疾已经整一年了,先是“心血过亏,肝肠上逼,脾经受克,肺气不好”,转为“风火上炎”而又没有一刻能安心的时候,以致眼肿如疣,用手一按,血随泪下;见到的人,无不大骇。后来遇到一位眼科名医,刀圭与药石兼施,才有起色;但自围城以来,旧疾复发,日重一日,王有龄深以为恨,性命他倒是早已置之度外,就这双眼睛不得力,大是苦事。
如果是其他文报,可以口授给幕友子侄代笔,但这通遗折,王有龄不愿为人所见,所以强睁如针刺般疼痛的双眼,继续往下写:
第残喘尚存,总以多杀一贼,多持一日为念,泣思杭城经去年兵燹之后,户鲜盖藏,米粮一切,均由绍贩运;军饷以资该处接济为多。金、兰这法后,臣等早经筹计,须重防以固宁绍一线饷源,乃始则饬宁绍台道张景渠,继又迭饬运司庄焕文,记名道彭斯举,各带兵勇设防,均经王履廉议格不行;又复袒庇绅富,因之捐借俱穷,固执已见,诸事掣肘。臣等犹思设防堵御,查有廖守元与湖绅赵景贤,历守危城,一载有余,调署绍兴府,竭筹布置。乃违大绅不愿设防之意,诬以通贼痛殴,履谦从旁袖手;比及城陷而走,卒致廖宗元城亡与亡,从此宁绍各属,相继失陷,而杭城已为孤注,无可解救矣!
写到这里,王有龄一口怨气不出,想到王履谦携带家眷辎重,由宁波出海到福建,远走高飞,逍遥自在,而杭州全城百姓,受此亘古所无的浩劫;自己与驻防将军瑞昌,纵能拼得一死报君主,却无补于大局,因而又奋笔写道:王履谦贻误全局,臣死不瞑目。眼下饷绝援穷,危在旦夕,辜负圣恩,罪无可逭。惟求皇上简发重兵,迅图扫荡,则臣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现在折报不通,以后更难偷达,谨将杭城决裂情形,合词备兵折稿,密递上海江苏抚臣薛焕代缮具奏。仰圣瞻天,无任痛切悚惶之至。
遗折尚未写完,家人已经闻声环集:王有龄看着奶妈抱着的五岁小儿子,肤色黄黑,骨瘦如柴,越发心如刀割,一恸而绝。
等救醒过来,只见他的大儿子橘云含着泪强展笑容,“爹!”他说,“胡大叔派人来了。”
“喔,”这无论如何是个喜信,王有龄顿觉有了精神。“在哪里?”
“在花厅上等着。”橘云说道:“爹也不必出去了,就请他上房来见吧!”
“也好。”王有龄说,“这时候还谈什么体制?再说,胡大叔派的人,就是自己人。请他进来好了。”他又问:“来人姓什么?”
“姓萧!年纪很轻,他说他是古应春的学生。”
进上房,萧家骥以大礼拜见。王有龄力弱不能还礼,只叫:“萧义士,萧义士,万不敢当。”
萧家骥敬重他的孤苦忠节,依旧恭恭敬敬地一跪三叩首;只有由橘云在一旁还了礼,然后端张椅子,请他在王有龄床前坐下。
“王大人!”
萧家骥只叫得这一声,下面的话就说不出来了。这倒不是怯官,只为一路而来,所见所闻,是梦想不到的惊心惨目;特别是此一刻,王家上下,一个个半死不活,看他们有气无力地飘来飘去,真如鬼影幢幢,以致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此身究竟是在人间,还是在地狱?因而有些神志恍惚,一时竟想不起话从哪里开头?
于是反主为客,王有龄先问起古应春:“令师我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