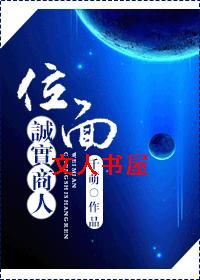红顶商人胡雪岩-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古,你肯帮我这个忙,我说感激的话,是多余的,不过,不能因为我,拖垮了你。十二万银子,到底也不是个小数目;我自己能凑多少,还不晓得,想来不过三五万。还有七八万,要现款,只怕不容易。”
“那就跟小爷叔说实话,七八万现款,我一下子也拿不出;只有暂时调动一下,希望王太太只是过一过目,仍旧交给你放出去生息。”
“嗯,嗯!”胡雪岩说,‘这个打算办得到的。不过,也要防个万一。”
“万一不成,只有硬挺。现在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胡雪岩点点头,自己觉得这件事总有八成把握,也就不再去多想;接下来谈到另一件事。
“这件事,关系王雪公的千秋。”胡雪岩说,“听大书我也听得不少,忠臣也晓得几个;死得象王雪公这样惨的,实在不多。总要想办法替他表扬表扬,留下长远的纪念,才对得起死者。”
“这又何劳你费心?朝廷表扬忠义,自然有一套恤典的。”朝廷的恤典,胡雪岩当然知道,象王有龄的这种情形,恤典必须优渥,除了照“巡抚例赐恤”,在赐谥、立传、赌祭以外,殉节的封疆大吏,照便可以入祀京师昭忠祠,子孙亦可获得云骑尉之类“世袭罔替”的“世职”。至于在本省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只要有人出面奏请,亦必可邀准,不在话下。
胡雪岩的意思,却不是指这些例行的恤典,“我心里一直在想,王雪公死得冤枉!”他说,“想起他‘死不瞑目’那句话,只怕我夜里都会睡不着觉。我要替他伸冤。至少,他生前的冤屈,要教大家晓得。”
照胡雪岩的看法,王有龄的冤屈,不止一端:第一、王履谦处处掣肘,宁绍可守而失守,以致杭州粮路断绝,陷入无可挽救的困境;第二,李元度做浙江的官,领浙江的饷,却在衡州逗留不进。如果他肯在浙西拼命猛攻,至少可以牵制浙西的长毛,杭州亦不会被重重围困得毫无生路;第三,两江总督曾国藩奉旨援浙而袖手旁观,大有见死不救之意,未免心狠。
由于交情深厚,而且身历其境,同受荼毒,所以胡雪岩提到这些,情绪相当激动。而在古应春,看法却不尽相同;他的看法是就利害着眼,比较不涉感情。
“小爷叔,”古应春很冷静地问道:“你是打算怎么样替王雪公伸冤?”
“我有两个办法,第一是要请人做一篇墓志铭,拿死者的这些冤屈都叙上去;第二是花几吊银子,到京里请一位‘都老爷’出面,狠狠参他一本。”
“参哪个?”
“参王履谦、李元度、还有两江的曾制台。”
“我看难!”古应春说,“曾制台现在正大红大紫的时候,参他不倒。再说句良心话,人家远在安庆,救江苏还没有力量,哪里又分得出兵来救浙江?”
胡雪岩心里不以为然,但不愿跟古应春争执,“那末,王履谦、李元度呢?”他说,“这两个人总是罪有应得吧?”“王履廉是一定要倒霉的;李元度就说不定了。而且,现在兵荒马乱,路又不通,朝廷要彻查也无从查起。只有等将来局势平定了再说。”
这一下惹得胡雪岩心头火发,咆哮着问:“照你这样说,莫非就让这两个人逍遥法外?”
胡雪岩从未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古应春受惊发楞,好半天说不出话。那尴尬的脸色,亦是胡雪岩从未见过的;因而象镜子一样,使得他照见了自己的失态。
“对不起,老古!”他低着头说,声音虽轻缓了许多;但仍掩不住他内心的愤慨不平。当然,这愤慨决不是对古应春。他觉得胡雪岩可怜亦可敬,然而却不愿说些胡雪岩爱听的话去安慰他。“小爷叔,我知道你跟王雪公的交情。不过,做事不能只讲感情,要讲是非利害。”
这话胡雪岩自然同意,只一时想不出,在这件事上的是非利害是什么?一个人有了冤屈,难道连诉一诉苦都不能?然则何以叫“不平则鸣”?
古应春见他不语,也就没有再说下去,其实他亦只是讲利害,未讲是非;这一阵子为了替胡雪岩打听杭州的消息,跟官场中人颇有往来,王有龄之殉节,以及各方面对杭州沦陷的感想批评,亦听了不少。大致说来,是同情王有龄的人多;但亦有人极力为曾国藩不救浙江辩护,其间党同伐异的论调,非常明显。王有龄孤军奋战,最有渊源的人,是何桂清,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什么人要为王有龄打抱不平,争论是非,当然会触犯时忌;遭致不利,岂不太傻?
古应春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庸俗卑下;但为了对胡雪岩的关切特甚,也就不能不从利害上去打算了。这些话一时说不透彻;而且最好是默喻而不必言传,他相信胡雪岩慢慢就会想明白,眼前最要紧的是筹划那十二万银子;以及替胡雪岩拟公文上闽浙总督。
从第二天起,古应春就为钱的事,全力奔走。草拟公文则不必自己动笔;他的交游亦很广,找了一个在江苏巡抚衙门当“文案委员”的候补知县雷子翰帮忙;一手包办,两天功夫连江苏巡抚薛焕批给胡雪岩的回文,都已拿到了。这时,胡雪岩才跟刘不才说明经过,“三叔,”最后他说,“事情是这样去进行。不过,我亦不打算一定要这样子办。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很难做。”
刘不才的性情,是恨人家看不起他;说他是纨绔,不能正事;因而听了胡雪岩的话,大不服气,“雪岩,”他凛然问道:“要什么人去做才容易。”
“三叔,”胡雪岩知道自己言语不检点,触犯了他的心病,引起误会,急忙答道:“这件事哪个做都难;如果你也做不成功,就没有人能做成功了。”
这无形中的一顶高帽子,才将刘不才哄得化怒为喜,“你倒说说看,怎么办法?”他的声音缓和了。
“第一、路上要当心——。”
“你看,”刘不才抢着说;回时伸手去解扎脚带;三寸宽的一条玄色丝带,其中却有花样,他指给胡雪岩看,那条带子里外两层,一端不缝,象是一个狭长的口袋,“我前两天在大马路定做的。我就晓得这以后,总少不得有啥机机密文件要带来带去,早就预备好了。”
“好的,这一点不难。”胡雪岩说,“到了杭州,怎么样向那些人开口,三叔,你想过没有?”
“你方始告诉我,我还没有想过,”刘不才略略沉吟了一下又说:“话太软了不好,硬了也不好。软了,当我怕他们;硬了又怕他心里有顾忌,不敢答应,或者索性出首。”“对了,难就难在这里。”胡雪岩说,“我有两句话,三叔记住: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第六章
一个多月以后,刘不才重回上海,他的本事很大,为胡雪岩接眷,居然成功。可是,全家将到上海,胡雪岩反倒上了心事,就为借了“小房子”住在一起的阿巧,身分不明,难以处置,只好求救七姑奶奶。
“七姐,你要替我出个主意;除你以外,我没有人好商量。”“那当然!小爷叔的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先要你自己定个宗旨。”
问到胡雪岩对阿巧姐的态度,正是他的难题所在,惟有报以苦笑:“七姐,全本西厢记,不都在你肚子里?”七姑奶奶对他们的情形,确是知之甚深,总括一句话:表面看来,恩爱异常;暗地里隔着一道极深的鸿沟。一个虽倾心于胡雪岩,但宁可居于外室,不愿位列小星,因为她畏惮胡家人多,伺候老太太以外,还要执礼于大妇,甚至看芙蓉的辞色;再有一种想法是:出自两江总督行辕,虽非嫡室,等于“署理”过掌印夫人;不管再做什么人的侧室,都觉得是一种委屈。
在胡雪岩,最大的顾虑亦正是为此。阿巧姐跟何桂清的姻缘,完全是自己一手促成;如今再接收过来,不管自己身受的感觉,还是想到旁人的批评,总有些不大对劲。在外面借“小房子”做露水夫妻,那是因为她千里相就于患难之中,因感生情,不能自己,无论对本身,对旁人,总还有句譬解的话好说;一旦接回家中,就无词自解了。
除此以外,还有个极大的障碍;胡太太曾经斩钉截铁地表示过:有出息的男人,三妻四妾,不足为奇;但大妇的名分,是他人夺不去的,所以只要胡雪岩看中了,娶回家则可,在外面另立门户则不可。同时她也表示过,凡是娶进门的,她必须姊妹看待。事实上对待芙蓉的态度,已经证明她言行如一;所以更显得她的脚步站得极隐,就连胡老太太亦不能不尊重她的话。
然而这是两回事。七姑奶奶了解胡雪岩的苦衷,却不能替他决定态度,“小爷叔,你要我帮你的忙,先要你自己拿定主意,或留或去,定了宗旨,才好想办法。不过,”她很率直地说:“我话要说在前头,不管怎么样,你要我帮着你瞒;那是办不到的。”
有此表示,胡雪岩大失所望。他的希望,正就是想请七姑奶奶设法替他在妻子面前隐瞒;所以听得这句话,作声不得。
这一下,等于心思完全显露,七姑奶奶便劝他:“小爷叔,家和万事兴!婶娘贤慧能干,是你大大的一个帮手。不过我再说一句:婶娘也很厉害,你千万别惹她恨你。如果说,你想拿阿巧姐接回去,我哪怕跑断腿,说破嘴,也替你去劝她。当然,成功不成功,不敢保险。倘或你下个决断,预备各奔东西,那包在我身上,你跟她好合好散,决不伤你们的和气。”“那,你倒说给我听听,怎么样才能跟阿巧姐好合好散?”“现在还说不出,要等我去动脑筋,不过,这一层,我有把握。”胡雪岩想了好一会,委决不下,叹口气说:“明天再说吧。”
“小爷叔,你最好今天晚上细想一想,把主意拿定了它;如果预备接回家,我要早点替你安排。”七姑奶奶指一指外面说,“我要请刘三叔先在老太太跟婶娘面前,替你下一番功夫。
胡雪岩一楞,是要下一番什么功夫?转个念头,才能领会,虽说自己妻子表示不禁良人纳妾;但却不能没有妒意。能与芙蓉相处得亲如姊妹,一方面是她本人有意要作个贤慧的榜样;一方面是芙蓉柔顺,甘于做小服低。这样因缘时会,两下凑成了一双两好的局面,是个异数;不能期望三妻四妾,人人如此。
七姑奶奶要请刘不才去下一番功夫,自然是先作疏通;果然自己有心,而阿巧姐亦不反对正式“进门”,七姑奶奶的做法是必要的。不过胡雪岩也因此被提醒了;阿巧姐亦是极厉害的脚色,远非芙蓉可比。就算眼前一切顺利,阿巧姐改变初衷,妻子亦能克践诺言,然而好景决不会长,两“雌”相遇,互持不下,明争暗斗之下,掀起醋海的万丈波澜,那时候可真是“两妇之间难为夫”了。
这样一想,忧愁烦恼,同时并生;因而胃纳越发不佳。不过他一向不肯扫人的兴;见刘不才意兴甚好,也就打点精神相陪,谈到午夜方散。
回到“小房子”,阿巧姐照例茶水点心,早有预备。卧室中重帷深垂,隔绝了料峭春寒;她只穿一件软缎夹袄,剪裁得非常贴身,越显得腰肢一捻,十分苗条。
入手相握,才知她到底穿得太少了些;“若要俏,冻得跳!”他说,“当心冻出病来。”
阿巧姐笑笑不响,倒杯热茶摆在他面前,自己捧着一把灌满热茶的乾隆五彩的小茶壶,当做手炉取暖;双眼灼灼地望着,等他开口。
每天回来,胡雪岩总要谈他在外面的情形,在哪里吃的饭;遇见了什么有趣的人;听到了哪些新闻,可是这天却一反常态,坐下来不作一声。
“你累了是不是?”阿巧姐说,“早点上床吧!”“嗯,累了。”
口中在答应她的话,眼睛却仍旧望着悬在天花板下,称为“保险灯”的煤油吊灯。这神思不属,无视眼前的态度,在阿巧姐的记忆中只有一次;就是得知王有龄殉节的那天晚上。“那哼啦!”她不知不觉地用极柔媚的苏白相依,“有啥心事?”
“老太太要来了!”
关于接眷的事,胡雪岩很少跟她谈。阿巧姐也只知道,他全家都陷在嘉兴,一时无法团圆,也就不去多想;这时突如其来地听得这一句,心里立刻就乱了。
“这是喜事!”她很勉强地笑着说。
“喜事倒是喜事,心事也是心事。阿巧,你到底怎么说?”“什么怎么说?”她明知故问。
胡雪岩想了一会,语意嗳昧地说:“我们这样子也不是个长局。”
阿巧姐颜色一变,将头低了下去,只见她睫毛闪动,却不知她眼中是何神色?于是,胡雪岩的心也乱了,站起来往床上一倒,望着帐顶发楞。
阿巧姐没有说话,但也不是灯下垂泪;放下手中的茶壶,将坐在洋油炉子上的一只瓦罐取了下来,倒出熬得极浓的鸡汤,另外又从洋铁匣子里取出七八片“盐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