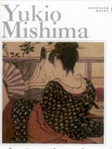北京法源寺-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激情,或两目圆睁、或破口大骂、或意气纵横、或义形于色。以慷慨态度准备处世、赴难、牺牲的人,他们在内心里,有十足的正义的理由,但在外表上,却是感情的,并且是激情、强烈的激情形式的,用人比喻,这叫“方孝孺式”。明朝的方孝孺反对明成祖篡位,明成祖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先生你不要管,你只替我们写诏书就好了。可是方孝孺连哭带骂,说要杀便杀,诏书我是不写的。明成祖说你不怕死,但杀起来不止杀你一个,要诛九族的。方孝孺说就是杀我十族,我也不怕。明成祖说,好,就杀你十族。照中国传统算法,九族是在直系方面,上下各杀四代,就是从罪人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直杀到自己的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另在旁系方面,还要横杀到三从兄弟(母族和妻族)。但并没有所谓第十族。方孝孺说他杀十族也不在乎,明成祖就要发明个十族出来,于是把朋友和学生,也都算进去。为了增加某种效果,明成祖抓来一个就给方孝孺看一个,方孝孺毫不一顾。最后统计,一共杀了八百七十三个。方孝孺自己也慷慨成仁。中国人说“慷慨成仁易”,因为慷慨成仁时候,都在事件的高潮点上,在高潮点上的人,是情绪最冲动的、最激情的,这时候的当事人,常常心一横,可以做出许许多多大勇和大牺牲的伟大行动,而不会冷静顾虑到别的利害与困难,也不会有恐惧、伤心、痛苦、孤寂等等使人沮丧、软弱的情绪。事实上,在高潮点上不久,当事人也就“成仁”了,死得没有破绽、没有拖拖拉拉,很干脆。所以说,慷慨成仁是比较容易的。正因为慷慨成仁比较容易,所以,有人相信:不给当事人慷慨成仁的机会,也许结果可能不同。于是千方百计在狱中软化他,使他屈服。但是有人却仍不屈服。像文天祥,就是最伟大的范例。不过,比对起“方孝孺式”来,这种“文天样式”却是更高境界的。多年的牢狱生活,那种牢,不是靠很强烈的激情才能坐的,而是靠一种平静的从容态度,而文天祥却正好表现了这一态度。最后他终于换得了你敌人来杀我。在柴市口,他神色自若,走到法场,从容而死……谭嗣同这首诗的第三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写得太好了、太好了,尤其好在这一“笑”字上。这一“笑”字,写尽了他的从容态度,但笑是一种激情也有点慷慨的成分。所以,谭嗣同之死,既有“慷慨成仁”之易、又有“从容就义”之难,难易双修,真是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视死如归,从容殉道。但是第四句“去留肝胆两昆仑”指什么呢?这就费解了。
“他们都死了,”八指头陀在残烛下漫想着,“谁来检定他们的往事呢?现在,清廷王朝没落了、中华民国建立了,时间愈久、时代愈变,往事就愈淹没了,但是,两昆仑的谜团,到底指谁呢?”
第十五章 古刹重逢
九年过去了。
北京的阴历七月又到了,正南正北的天河又改变了方向,天气又快凉了。
七月一日是立秋了。立秋是鬼节的前奏。鬼节总带给人一种肃杀的气氛。家家都要“供包袱”,跟死人打交道。跟死人最有肃杀关系的菜市口,更是令人注目的地方。
这天立秋正是阴天。菜市口的街道,正像北京的大部街道一样,还没铺上石板。虽然已是一九二六年,清廷玉朝已被推翻了十五年,可是时唯物主义哲学系统化了。他坚持自然是万物的本原,物质,菜市口还是前清时的老样子。街上的浮土,晴天时候就像香炉,一阵风刮来,就天昏地暗;雨天时候就像酱缸,一脚踩下去,就要吃力地拔着走。
路不好是一回事,每个人都得走。为他们的现在与未来而走。但有一个老人不这样,他在为过去而走。
十五年来,他每次来北京,都要一个人来菜市口,望着街上的浮上、望着西鹤年堂老药铺,凄然若有所思。他两脚踩的泥土,本该是他当年的刑死之地。而西鹤年堂老药铺前面,也正是监斩者坐在长桌后面、以朱笔勾决人犯的地方。但是,偶然的机遇,他死里逃生,躲过了这一劫,除了西鹤年堂的老屋和他自己的一对老眼,当年的物证人证,已全化为泥土。西太后化为泥土、监斩官化为泥土、六君子化为泥土,整个的保守与改良、倒退与进步、绝望与希望、怠情与辛勤,都已化为泥土。剩下的,只是老去的他,孤单的走上丁字路口,在生离死别间、旧恨新愁里,面对着老药铺,在泥土上印证三生。
这一次来北京、来菜市口,他已经六十九岁了。中国的时局又陷入新的混乱,北方的旧大将走马换将、南方的新军阀誓师北伐,来势汹汹,中国的一场新浩劫或几场新浩劫超”。,是指日可待的。而他自己,已来日无多,又不为人所喜,避地于域外。也不得不早为之计。他这次来北京,感觉已和过去不同,过去每次来,都有下次再来的心理,可是这次却没有了。他觉得他与北京已经缘尽,这次来,不是暂留、不是小住、不是怀旧,而是告别、永别前的告别。在菜市口,他是向二十八年前的烈士告别、向二十八年前的刑死之我告别、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离开了菜市口,他到了宣武门外大街南口,走进了南北方向的北半截胡同,胡同的南端西侧,一座地势低矮的房子出现了,那是谭嗣同住过多年的地方——浏阳会馆。会馆里的莽苍苍斋,三十年前,正是他们商讨变法维新的地方,多少个白天、多少个晚上、多少个深夜,他和谭嗣同等志士们在这里为新中国设计蓝图。三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莽苍苍斋老屋犹在,可是主人已去、客人已老,除了蛛网与劫灰,已是一片死寂。唯一活动的是照料会馆的老佣人,在收了这位陌生老先生的赏钱后,殷勤的逐屋向他介绍。老佣人一知半解的述说三十年前,这是大人物住过来过的地方。他吃力的细数莽苍苍斋主人交往的人物,他口中出现了“一位康先生”。他做梦也梦想不到,那位“康先生”,正含泪站在他的身边。
莽苍苍斋的匾额还在,旁边的门联,却己斑驳不清,但他清楚记得那门联上的原文。当时谭嗣同写的是“家无儋石,气雄万夫”,他看了,觉得口气太大,要谭嗣同改得隐晦一点,谭嗣同改成“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他大加赞赏,认为改得收敛。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谭嗣同“气雄万夫”而去,“视尔梦梦”的,正是他自己。“再见了,莽苍苍斋;再见了,复生。”这里尘封了他们早年的岁月、这里寄存了当年救国者的欢乐与哀愁、这里凝结了谭嗣同被捕前的刹那,在那从容不迫的迎接里,主人迎接捉拿钦犯的,一如迎接一批客人。在天地逆旅中,人生本是过客,只有旧屋还活现主人,而主人自己,却长眠在万里朱殷之外,在苍苍的草莽里,默然无语,“人亦有言。”
在阴天中,他又转入西砖胡同南口,沿着朱红斑驳的墙,走进了法源寺。
四十年前,他初来北京,就住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就爱上附近的这座古庙。庙里的天王殿后有大雄宝殿,在宽阔的平台前面,有台阶,左右分列六座石碑,气势雄伟。他最喜欢在旧碑前面看碑文和龟趺,从古迹中上溯过去,浑忘现在的一切。过去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过去、一种是古人的过去。自己的过去虽然不过几十年,但是因为太切身、太近,所以会带给人伤感、带给人怅惘、带给人痛苦。从菜市口到莽苍苍斋,那种痛苦都太逼近了,令人难受;但古人的过去却不如此,它带给人思古的幽情、带给人凄凉的美丽和一种令人神往的幸会与契合。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汇之中,也会令人有苍茫之情、沧桑之感,但那种情感是超然的,不滞于一己与小我,显得浩荡而恢廓。但是怀今就赶不上。智者怀古、仁者怀今,仁智双修的并不排斥任一种,不过怀今以后,益之以怀古,可以使人伤感、怅惆、痛苦之情升华,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有更达观的领悟。“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正因为结局是从今而古、从古而无,所以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来怀古,反倒不是减少而是加多。你自己生命减少,但一旦衔接上古人的,你的生命,就变得拉长、变为永恒中的一部分。即使你化为尘土,但已与古人和光同尘,你不再那样孤单,你死去的朋友也不那样孤单。你是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的一部分。那时候,你不再为他们的殉道而伤感、怅惘、痛苦,一如在法源寺中,你不会为殉道于此的谢仿得而伤感、怅惆、痛苦,你也不会跟谢枋得同仇敌忾,以他的仇敌为仇敌。你有的情感,只是一种敬佩,一种清澈的、澄明的、单纯的、不拖泥带水的敬佩。那种升华以后的苍茫与沧桑,开扩了你的视野,绵延了你的时距,你变得一方面极目千里,一方面神交古人,那是一种新的境界,奇怪的是,你只能孤单一人,独自在古庙中求之,而那古庙,对他说来;只有法源寺。
“康先生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说话声音来自背后,康有为转身一看,看到一个中年人,在对他微笑。
中年人中等身材,留着分头,但有点杂乱,圆圆的脸上,戴着圆圆的玳瑁眼镜,眼睛不大,但极有神,鼻子有点鹰勾,在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一排胡子。下巴是刮过的,可见头发有点杂乱,并非不修边幅,而是名士派的缘故。他身穿一套褐色旧西装,擦过的黑皮鞋,整齐干净,像个很像样的教授。
康有为伸出手来,和中年人握了手。好奇的问:“先生知道我姓康?”
“康先生名满天下,当然知道。”中年人笑着说,非常友善。
“你先生见过我?能认出我来?”康有为问,“你刚才说我‘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你好像看我来过?”
中年人笑起来,笑容中有点神秘。他低下了头,又抬起来。两只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康有为。慢慢他说:
“我当然认得出康先生,在报上照片看得大多了。何况,我还见过康先生,不过,那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康先生恐怕不记得了。”
“多早以前?”
“算来康先生会吓一跳,近四十年以前。准确的说,是三十八年前。”
康有为圆睁了眼睛,好奇地间:“可能吗?看你先生不过四五十岁。近四十年前你只有十多岁,你十多岁时见过我?在哪里见到的?”
“就在北京。”
“在北京哪里?”
“就在北京这里。”中年人把手指地,“就在北京这法源寺里。就在这石碑前面。”
康有为为之一震。他抓住中年人的手,仔细端详着、端详着。“你是一一”
“我是——我是当年法源寺当家和尚余和尚的小徒弟!”
康有为愣住了。他大为惊讶,仔细盯住了对方。突然间,他拥上前去,抱住中年人:“啊,我记得你!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位从河南逃荒出来、被哥哥放在庙门口的小弟弟!”
中年人不再故作神秘了,他抱住康有为,眼睛湿了。抱了一阵,两人互抱着腰,上半身都向后仰,互相端详着。中年人赞赏地摇摇头:“康先生博闻强记,真名不虚传,康先生记性真好!近四十年前的一个小和尚,你还记得。”
“也不是记性多好,而是你当年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康有为双手拉着中年人的双手:“你当时叫什么来着,你叫一一”
“普净。我叫普净。”
“对、对!你叫普净,你叫普净!”
“普净是我做小和尚的名字,我的本姓姓李,我叫李十力
“李十力?李十力是你?”康有为又一次大为惊讶,他用手指点着中年人的前胸,“你不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吗?”
李十力笑着点了点头,“教授倒是滥竿,名则未必。”
“你太客气了。”康有为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有个搞‘新唯识论’的大学者,我也一直心仪已久,并且一直想有缘一见的,原来就是你,就是我四十年前见过的小法师啊!久别重逢,并且重逢在四十年前的老地方,真大巧了、太巧了!”
“《墨子》中说‘景不徙’,《庄子》中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都是把过去的投影,给抽象的凝聚在原来地方,表示形离开了,可是影没离开。如今四十年后,康先生和我的形又重现在这儿,我们简直给古书提供了形影不离的今证了。”
康有为拍着李十力的肩膀,笑着说:“你说得是。这正是形影不离啊!可惜的是,我老了,余法师也不在了。余法师若活到现在,也八十开外了吧?”
“正好八十整寿。并且正好就是今天——今天正是余法师八十冥诞啊!”
“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