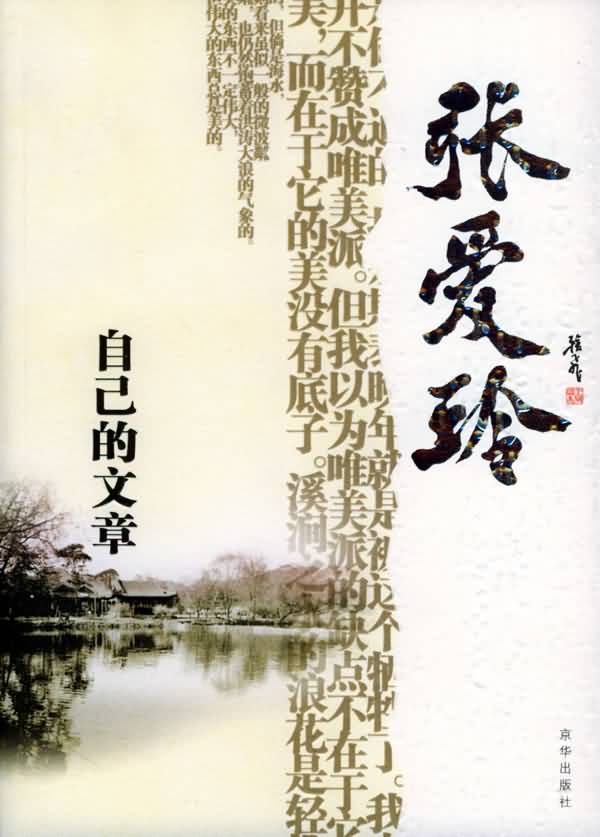废名文集-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哈哈,你看!”
细竹指着叫小林看,一个一个的球弹动得很好看。
“就因为一个最好,惹得他们跑,他们都是追那个孩子。”
“是呀,——那个我该自己留着,另外再扎一个他!”
“上帝创造万物,本也就不平均。”小林笑。
“你不要说笑话。他们争着吵起来了,真是我的不是,——我去看一看。”
细竹一跃跑了。
“草色青青送马蹄。”
小林望着她的后影信口一唱“你不要骂人!”
细竹又掉转头来,说他骂人。随又笑了,又跑。
小林这时才想一想这一句诗是讲马的,依然望着她的后影答:
“在诗国里那里会有这些分别呢?”
细竹把他一个人留在河上。
寂寞真是上帝加于人的一个最厉害的刑罚。然而上帝要赧免你也很容易,有时只须
一个脚步。小林望见三哑担了水桶下河来挑水,用了很响亮的声音道:
“三哑叔,刚才这里很好玩。”
“是的,清明时节我史家庄是热闹的,——哥儿街上也打杨柳吗?”
“一样的打,我从小就喜欢打杨柳。”
“哈哈哈。”
“三哑笑。小林“从小”这两个字,掘开了三哑无限的宝藏,现在顶天立地的小林
哥儿站在他面前,那小小的小林似乎也离开他不远。小林,他自然懂得他的三哑叔之所
以欢喜。
“三哑叔,你笑我现在长得这么大了?”
“哈——”
三哑不给一个分明的回答,他觉得那样是唐突。
“明天大家到松树脚下烧香,哥儿也去看一看。”
“那一定是去。”
三哑渐渐走近了河岸。
“哥儿,这两棵杨柳是我栽的。哥儿当初到史家庄来的时候,——哥儿怕不记得,
它大概不过载了一两年。”
三哑说,沿树根一直望到树杪,望到树杪担着水桶站住了,尽望,嘴张得那么大,
仿佛要数一数到底有几多叶子。
“记得记得。”小林连忙答。
小林突然感到可哀,三哑叔还是三哑叔,同当年并没有什么分别!他记起他第一次
看见三哑叔,三哑叔就是张那么大的嘴。在他所最有关系的人当中,他想,——史家奶
奶也还是那样!
其实,确切的说,最没有分别的只是春天,春天无今昔。
我们不能把这里栽了一棵树那里伐了一棵树归到春天的改变。
那两棵杨柳之间就是取水的地方,河岸在这里有青石砌成的几步阶级。
三哑取水。小林说:
“我住在史家庄要百岁长寿,喝三哑叔这样的好水!”
“哈哈哈。”
三哑叔栽的杨柳的露水我一定也从河水当中喝了。”
“哈哈哈。”
三哑这一笑,依然是因为小林第一句,第二句他还没有听清白。
桥 黄昏
三哑挑完了水,小林一个人还在河上。
他真应该感谢他的三哑叔。他此刻沉在深思里,游于这黄昏的美之中,——当细竹
去了,三哑未来,他是怎样的无着落呵。但他不知道感谢,只是深思,只是享受。心境
之推移,正同时间推移是一样,推移了而并不向你打一个招呼。
头上的杨柳,一丝丝下挂的杨柳——虽然是头上,到底是在树上呵,但黄昏是这么
静,静仿佛做了船,乘上这船什么也探手得到,所以小林简直是搴杨柳而喝。
“你无须乎再待明天的朝阳,那样你绿得是一棵树。”
“真的,这样的杨柳不只是一棵树,花和尚的力量也不能从黄昏里单把它拔得走,
除非一支笔一扫,——这是说“夜”。
“叫它什么一种颜色?”
他想一口说定这个颜色。可是,立刻为之怅然,要跳出眼睛来问似的。他相信他的
眼睛是与杨柳同色,他喝得醉了。
走过树行,上视到天,真是一个极好的天气的黄昏的天。
望着天笑起来了,记起今天早晨细竹厉声对琴子说的话:“绿了你的眼睛!”这是
一句成语,凡有人不知恶汉的利害,敢于惹他,他便这样说,意思是:“我你也不看清
楚!?”细竹当然是张大其词,因琴子无意的打了她一下。小林很以这话为有趣,用了
他的解释。
但此刻他的眼睛里不是绿字。
踱来踱去,又踱到树下,又昂了头——
“古人也曾说柳发。”
这样就算是满足了,一眼低下了水。
“呀!”
几条柳垂近了水面,这才看见,——还没有十分捱近,河水那么流,不能叫柳丝动
一动。
他转向河的上流望,仿佛这一望河水要长高了这一个方寸,杨柳来击水响。
天上现了几颗星。河却还不是那样的阔,叫此岸已经看见彼岸的夜,河之外——如
果真要画它,沙,树,尚得算作黄昏里的东西。山——对面是有山的,做了这个horizo
n的极限,有意的望远些,说看山……
看不见了。
想到怕看不见才去看,看不见,山倒没有在他的心上失掉。否则举头一见远远的落
在天地之间了罢。
“有多少地方,多少人物,与我同存在,而首先消灭于我?
不,在我他们根本上就没有存在过。然而,倘若是我的相识,那怕画图上的相识,
我的梦灵也会牵进他来组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梦——可以只是一棵树。”
是的,谁能指出这棵树的分际呢?
“没有梦则是什么一个光景?……”
这个使得他失了言词,我们平常一个简单的酣睡。
“……thatvividdreamingwhichmakesthemarginofourdeeperrest.”念着英国的一
位著作家的话。
“史家庄呵,我是怎样的同你相识!”
奇怪,他的眼睛里突然又是泪,——这个为他遮住了是什么时分哩。
这当然要叫做哭呵。没有细竹,恐怕也就没有这哭,——
这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呢?……
星光下这等于无有的晶莹的点滴,不可测其深,是汪洋大海。
小林站在这海的当前却不自小,他怀抱着。
“嗳呀!”
这才看见夜。
在他思念之中夜早已袭上了他。
望一望天——觉得太黑了。又笑,记起两位朋友。一年前,正是这么黑洞洞的晚,
三人在一个果树园里走路,N说:
“天上有星,地下的一切也还是有着,——试来画这么一幅图画,无边的黑而实是
无量的色相。”
T思索得很窘,说:
“那倒是很美的一幅画,苦于不可能。比如就花说,有许多颜色的花我们还没有见
过,当你着手的时候,就未免忽略了这些颜色,你的颜色就有了缺欠。”
N笑道:
“我们还不知道此时有多少狗叫。”
因为听见狗叫。
T是一个小说家。
桥 灯笼
史家奶奶琴子两人坐在灯下谈天,尽是属于传说上的。这回的清明对于史家奶奶大
大的不同了,欢欢喜喜的也说过节。
原因自然是多了小林这一个客。老人,像史家奶奶这样的老人,狂风怒涛行在大海,
恐怕不如我们害怕;同我们一路祭奠死人,站在坟场之中——青草也堆成了波呵,则其
眼睛看见的是什么,决不是我们所能够推测。往年,陪了琴子细竹去上坟,回转头来,
细竹常是埋怨琴子“不该掉眼泪,惹得奶奶几乎要哭!”她实在的觉得奶奶这么大的年
纪不哭才好。
然而奶奶有时到底哭了一哭,她也哭而已,算是“大家伤心一场,”哭就同是伤心,
掉眼泪就是哭,——本来,泪珠儿落了下来,那里还有白头与少女的标记呢?但这都不
是今年的话。今年连琴子也格外的壮观起来了,“清明是人间的事,与大地原无关。”
奶奶同她谈,她恰用得着野心二字,——这在以前是决没有的。
这时小林徘徊于河上,细竹也还在大门口没有进来。灯点在屋子里,要照见的倒不
如说是四壁以外,因为琴子的眼睛虽是牢牢的对住这一颗光,而她一忽儿站在杨柳树底
下,一忽儿又跑到屋对面的麦垅里去了。这一些稔熟的地方,谁也不知谁是最福气偏偏
赶得上这一位姑娘的想象!不然就只好在夜色之中。
“清明插杨柳,端午插菖蒲,艾,中秋个个又要到塘里摘荷叶,——这都有来历没
有?到处是不是一样?”史家奶奶说。
“不晓得。”
琴子答,眼睛依然没有离开灯火,——忽然她替史家庄唯一的一棵梅花开了一树花!
这是一棵腊梅,长在“东头”一家的院子里,花开的时候她喜欢去看。
这个新鲜的思想居然自成一幕,刚才一个一个的出现的都不知退避到哪一角落里去
了。抬头,很兴奋的对奶奶道:
“过年有什么可插呢?要插就只有梅花。但梅花太少。”
史家奶奶的眼睛闭住了,仿佛一时觉得灯光太强,而且同小孩子背书一般随口这样
一声: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话出了口,再也不听见别的什么了,眼睛还是闭着。这实在只等于打了一个呵欠,
一点意思也没有。而琴子,立时目光炯然,望着老人,那一双眼睛就真是瞎子的眼睛她
也要它重明似的,道:
“奶,过年家家贴对子,红纸上写的也就是些春风杨柳之类。”
“哈,我的孩子,——史家庄所有的春联,都是你一人的心裁,亏你记得许多。”
“细竹倒也帮了许多忙。”
琴子笑。连忙又道:
“她跑到哪里玩去了?还没有回来。”
“小林也没有回来哩,——他跑到哪里去了?外面都是漆黑的。”
没有答话,静得很。
灯光无助于祖母之爱,少女的心又不能自己燃起来——
真是“随风潜入夜”。
细竹回来了,步子是快的,慢开口,随便的歌些什么。走近这屋子的门,站住,一
眼之间,看了一看琴子,又看史家奶奶,但没有停唱。
“小林哥哥哪里去了呢?你看见他吗?”史家奶奶问。
“他还没有回来吗?”
这个声音太响,而且是那样的一个神气,碰出了所经过的一切,史家奶奶同琴子不
必再问而当知道!
“一定还在那里,我去看。”
琴子的样子是一个statue,——当然要如Hermione,那样的一个statue专候细竹说。
这个深,却不比小林的深难于推测,——她自己就分明的见到底。此后常有这样的话在
她心里讲:“我很觉得我自己的不平常处,我不胆大,但大胆的绝对的反面我又决不是,
我的灵魂里根本就无有畏缩的地位。
人家笑我慈悲——这两个字倒很像,可惜他们是一般妇人女子的意义。”想了这么
些,思想的起源反而忘记了:对了小林她总有点退缩,——此其一。这个实在无道理,
太平常。不过世间还没有那大的距离可以供爱去退缩。再者,她的爱里何以时常飞来一
个影子,恰如池塘里飞鸟的影子?这简直是一个不祥的东西——爱!这个影,如果刻出
来,要她仔细认一认,应该像一个“妒”字,她才怕哩。
听完那句话,又好像好久没有看见她的妹妹似的,而且笑——
“你去看!”
自然没有说出声。
细竹就凑近她道:
“我们两人一路去,他一定一个人还在河上。”
“你们不要去,我打灯笼去。”
史家奶奶说。
黑夜游出了一个光——小林的思想也正在一个黑夜。
“小林儿!”
“奶奶吗?嗳呀,不要下坝,我正预备回来。”
这些地方,史家奶奶就不打灯笼也不会失足的。光照一处草绿——史家奶奶的白头
发也格外照见。
桥 清明
松树脚下都是陈死人,最新的也快二十年了,绿草与石碑,宛如出于一个画家的手,
彼此是互相生长。怕也要拿一幅古画来相比才合适。这是就看官所得的印象说话,若论
实物的浓淡,虽同样不能与时间无关系,一则要经剥蚀,一则过一个春天惟有加一春之
色,——沧海桑田权且不管。
清明上坟,照例有这样的秩序:男的,挑了“香担”,尽一日之长,凡属一族的死
人所占的一块土都走到;女的就其最亲者,与最近之处。这一天小林起得很早,看天,
是一个阴天,但似不至有雨落。吃了早饭,他独自沿史家庄的坝走,已望见东边山上,
四方树林,冒烟。一片青山,不大分得出坟,这里那里的人看得见,因了穿的衣服。走
到松树脚下,琴子细竹坐在坟前,等候三哑点火。已经烧了好几阵火过去了。
他小的时候也跟他的族人一路遍走二十里路的远近,有几位好事者把那奠死人的腌
肉,或者鲤鱼,就香火烧吃。他当然耍尝一脔。那几位现在都是死人了,有一个,与小
林是兄弟辈,流落外方。
阴天,更为松树脚下生色,树深草浅,但是一个绿。绿是一面镜子,不知挂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