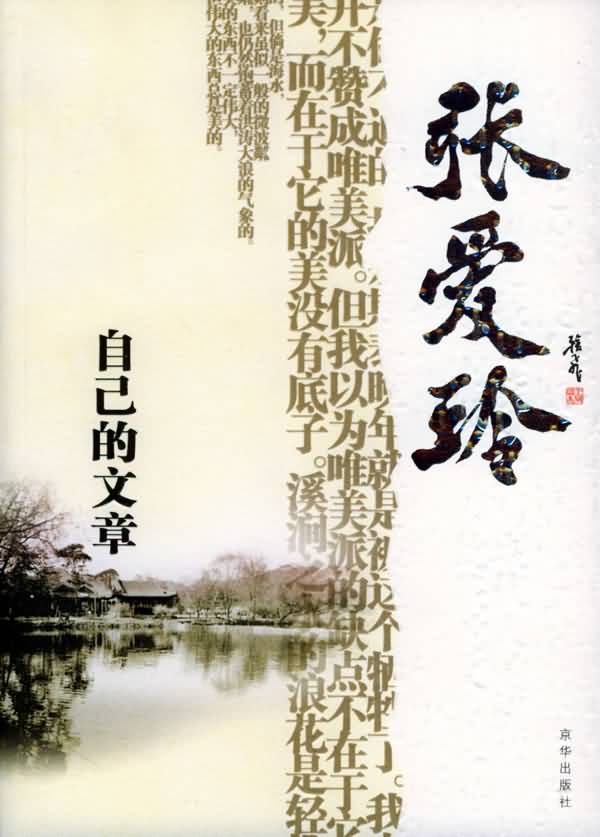废名文集-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兜去;倘若兜着了,那就不移地的转过身倒在挖就了的荡里,——三姑娘的小小
的手掌,这时跟着她的欢跃的叫声热闹起来,一直等到蹦跳蹦跳好容易给捉住了,
才又坐下草地望着爸爸。
流水潺潺,摇网从水里探起,一滴滴的水点打在水上,浸在水当中的枝条也冲
击着嚓嚓作响。三姑娘渐渐把爸爸站在那里都忘掉了,只是不住的抠土,嘴里还低
声的歌唱;头毛低到眼边,才把脑壳一扬,不觉也就瞥到那滔滔水流上的一堆白沫,
顿时兴奋起来,然而立刻不见了,偏头又给树叶子遮住了——使得眼光回复到爸爸
的身上,是突然一声“啊呀”!这回是一尾大鱼!而妈妈也沿坝走来,说盐钵里的
盐怕还够不了一飧饭。
老程由街转头,茅屋顶上正在冒烟,叱咤一声,躲在园里吃菜的猪飞奔的跑,
——三姑娘也就出来了,老程从荷包里掏出一把大红头绳:“阿三,这个打辫好吗?”
三姑娘抢在手上,一面还接下酒壶,奔向灶角里去。“留到端午扎艾蒿,别糟蹋了!”
妈妈这样答应着,随即把洒壶伸到灶孔烫。三姑娘到房里去了一会又出来,见了妈
妈抽筷子,便赶快拿出杯子——家里只有这一个,老是归三姑娘照管——踮着脚送
在桌上;然而老程终于还是要亲自朝中间挪一挪,然后又取出壶来。“爸爸喝酒,
我吃豆腐干!”老程实在用不着下酒的菜,对着三姑娘慢慢的喝了。
三姑娘八岁的时候,就能够代替妈妈洗衣。然而绿团团的坡上,从此也不见老
程的踪迹了——这只要看竹林的那边河坝倾斜成一块平坦的上面,高耸着一个不毛
的同教书先生(自然不是我们的先生)用的戒方一般模样的土堆,堆前竖着三四根
只有抄梢还没有斩去的枝桠吊着被雨粘住的纸幡残片的竹竿,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意
义。
老程家的已经是四十岁的婆婆,就在平常,穿的衣服也都是青蓝大布,现在不
过系鞋的带子也不用那水红颜色的罢了,所以并不现得十分异样。独有三姑娘的黑
地绿花鞋的尖头蒙上一层白布,虽然更显得好看,却叫人见了也同三姑娘自己一样
懒懒的没有话可说了。
然而那也并非是长久的情形。母女都是那样勤敏,家事的兴旺,正如这块小天
地,春天来了,林里的竹子,园里的菜,都一天一天的绿得可爱。老程的死却正相
反,一天比一天淡漠起来,只有鹞鹰在屋头上打圈子,妈妈呼喊女儿道,“去,去
看但里放的鸡娃。”三姑娘才走到竹林那边,知道这里睡的是爸爸了。到后来,青
草铺平了一切,连曾经有个爸爸这件事实几乎也没有了。
正二月间城里赛龙灯,大街小巷,真是人山人海。最多的还要算邻近各村上的
女人,她们像一阵旋风,大大小小牵成一串从这街冲到那街,街上的汉子也借这个
机会撞一撞她们的奶。然而能够看得见三姑娘同三姑娘的妈妈吗?不,一回也没有
看见!锣鼓喧天,惊不了她母女两个,正如惊不了栖在竹林的雀子。鸡上埘的时候,
比这里更西也是住在坝下的堂嫂子们,顺便也邀请一声“三姐”,三姑娘总是微笑
的推辞。妈妈则极力鼓励着一路去,三姑娘送客到坝上,也跟着出来,看到底攀缠
着走了不;然而别人的渐渐走得远了,自己的不还是影子一般的依在身边吗?
三姑娘的拒绝,本是很自然的,妈妈的神情反而有点莫名其妙了!用询问的眼
光朝妈妈脸上一瞧,——却也正在瞧过来,于是又掉头望着嫂子们走去的方向:
“有什么可看?成群打阵,好像是发了疯的!”
这话本来想使妈妈热闹起来,而妈妈依然是无精打采沉着面孔。河里没有水,
平沙一片,现得这坝从远远看来是蜿蜒着一条蛇,站在上面的人,更小到同一颗黑
子了。由这里望过去,半圆形的城门,也低斜得快要同地面合成了一起;木桥俨然
是画中见过的,而往来蠕动都在沙滩;在坝上分明数得清楚,及至到了沙滩,一转
眼就失了心目中的标记,只觉得一簇簇的仿佛是远山上的树林罢了。至于聒聒的喧
声,却比站在近旁更能入耳,虽然听不着说的是什么,听者的心早被他牵引了去了。
竹林里也同平常一样,雀子在奏他们的晚歌,然而对于听惯了的人只能够增加静寂。
打破这静寂的终于还是妈妈:
“阿三!我就是死了也不怕猫跳!你老这样守着我,到底……”
妈妈不作声,三姑娘抱歉似的不安,突然来了这埋怨,刚才的事倒好像给一阵
风赶跑了,增长了一番力气娇恼着:
“到底!这也什么到底不到底!我不欢喜玩!”
三姑娘同妈妈间的争吵,其原因都出在自己的过于乖巧,比如每天清早起来,
把房里的家具抹得干净,妈妈却说,“乡户人家呵,要这样?”偶然一出门做客,
只对着镜子把散在额上的头毛梳理一梳理,妈妈却硬从盒子里拿出一枝花来。现在
站在坝上,眶子里的眼泪快要迸出来了,妈妈才不作声。这时节难为的是妈妈了,
皱着眉头不转眼的望,而三姑娘老不抬头!待到点燃了案上的灯,才知道已经走进
了茅屋,这期间的时刻竞是在梦中过去了。
灯光下也立刻照见了三姑娘,拿一束稻草,一菜篮适才饭后同妈妈在园里割回
的白菜,坐下板凳三棵捆成一把。
“妈妈,这比以前大得多了!两棵怕就有一斤。”
妈妈哪想到屋里还放着明天早晨要卖的菜呢?三姑娘本不依恃妈妈的帮忙,妈
妈终于不出声的叹一口气伴着三姑娘捆了。
三姑娘不上街看灯,然而当年背在爸爸的背上是看过了多少次的,所以听了敲
在城里响在城外的锣鼓,都能够在记忆中画出是怎样的情境来。“再是上东门,再
是在衙门口领赏……”忖着声音所来的地方自言自语的这样猜。妈妈正在做嫂子的
时候,也是一样的欢喜赶热闹,那情境也许比三姑娘更记得清白,然而对于三姑娘
的仿佛亲临一般的高兴,只是无意的吐出来几声“是”——这几乎要使得三姑娘稀
奇得伸起腰来了:“刚才还催我去玩哩!”
三姑娘实在是站起来了,一二三四的点着把数,然后又一把把的摆在菜篮,以
便于明天一大早挑上街去卖。
见了三姑娘活泼泼的肩上一担菜,一定要奇怪,昨夜晚为什么那样没出息,不
在火烛之下现一现那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样的面庞的呢?不——倘若奇怪,只有自己
的妈妈。人一见了三姑娘挑菜,就只有三姑娘同三姑娘的菜,其余的什么也不记得,
因为耽误了一刻,三姑娘的莱就买不到手;三姑娘的白菜原是这样好,隔夜没有浸
水,煮起来比别人的多,吃起来比别人的甜了。
我在祠堂里足足住了六年之久,三姑娘最后留给我的印象,也就在卖菜这一件
事。
三姑娘这时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姑娘,因为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单衣,颜色淡得
同月色一般——这自然是旧的了,然而倘若是新的,怕没有这样合式,不过这也不
能够说定,因为我们从没有看见三姑娘穿过新衣:总之三姑娘是好看罢了。三姑娘
在我们的眼睛里同我们的先生一样熟,所不同的,我们一望见先生就往里跑,望见
三姑娘都不知不觉的站在那里笑。然而三姑娘是这样淑静,愈走近我们,我们的热
闹便愈是消灭下去,等到我们从她的篮里拣起菜来,又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了铜子,
简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觉得这太对不起三姑娘了。而三姑娘始终是很习惯的,接下铜
子又把菜篮肩上。
一天三姑娘是卖青椒。这时青椒出世还不久,我们大家商议买四两来煮鱼吃—
—鲜青椒煮鲜鱼,是再好吃没有的。三姑娘在用秤称,我们都高兴的了不得,有的
说买鲫鱼,有的说鲫鱼还不及鳊鱼。其中有一位是最会说笑的,向着三姑娘道:
“三姑娘,你多称一两,回头我们的饭熟了,你也来吃,好不好呢?”
三姑娘笑了:
“吃先生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
我们大家也都笑了;不提防三姑娘果然从篮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
里。
“三姑娘是不吃我们的饭的,妈妈在家里等吃饭。我们没有什么谢三姑娘,只
望三姑娘将来碰一个好姑爷。”
我这样说。然而三姑娘也就赶跑了。
从此我没有见到三姑娘。到今年,我远道回家过清明,阴雾天气,打算去郊外
看烧香,走到坝上,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波皱了。
正在徘徊,从竹林上坝的小径,走来两个妇人,一个站住了,前面的一个且走且回
应,而我即刻认定了是三姑娘!
“我的三姐,就有这样忙,端午中秋接不来,为得先人来了饭也不吃!”
那妇人的话也分明听到。
再没有别的声息:三姑娘的鞋踏着沙土。我急于要走过竹林看看,然而也暂时
面对流水,让三姑娘低头过去。
1924年10月
小说 鹧 鸪
醒来听不见桨声,从篷里伸头一望。原来东方已经发白,四五株杨柳包围两间
茅舍的船埠立在眼前了。
到家还有十五里的旱程,我跟在挑夫后面循着田膛走,两边水田里四散着隔夜
挑来的秧捆,农人也正从村里走下田来,——突然惊住我的,是远远传来的鹧鸪的
声音了!我在都会地方住了近十年,每到乡间种田的季节,便想念起鹧鸪。
我还没有动身的时候,接到弟弟的来信,说近年年岁丰收,县城里举行赛会,
最后一句是,“各亲戚都派代表来家。”到家,首先迎着我的是母亲同弟弟,我坐
下竹榻,母亲拿着芭扇站在我的身旁,我纠住弟弟坐在我前:
“怎么一个代表也不见呢?”
弟弟发气似的:“回去了不久哩!”接着数一大串,没有一个不是姐妹的称呼,
有的我仅知道名字,有的在我还是那同我拍球踢毽子的对手,现在据说也是插花傅
粉大的模样。弟弟又告诉我会是赛得怎样的热闹,我暗地里笑,而且仿佛是羡念一
种诗境:“这都是我当年见过的!”但我又好像寻觅什么而记忆不起,感到一点空
虚,突然问道:
“柚子姐姐来了没有呢?”
“柚子姐姐——正在做新娘哩!”
我不作声。弟弟莫明其妙的瞪着眼睛对我看。母亲催我到自己的卧室去躺着休
息。
我刚刚跨过门槛,芹已经站在长几旁边对了我的眼光一笑,我也一笑,而我在
路上准备的许多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芹让下她做针甫的矮竹椅叫我坐,我也就
挽住她的手坐着,这时无意间瞥到的是粉壁上悬挂的我自己画的四块画屏:
“这是从哪里说起!”
经了芹再三的摸抚,我才知道我是在掉眼泪,接着是白的绢帕拂到我的面上了。
“妻呵,刚才弟弟告诉我柚子妹妹正在做新娘。”
“是呵,做新娘,你缘何突如其来的发呆呢?”
“你该还记得!”我手指着壁。
“我不比你记得许多!——老是这样起头,要说的话多着哩!”
芹弯着身子娇媚的把嘴鼓着,我也抬头相觑,不觉间她的唇落在我的——我微
笑了:
“‘快活快活!’我适才在路上……”
我突然又觉得心伤,母亲也把芹唤去给我备早饭了。
去年冬天我曾回家一趟,母亲要我下乡给姨妈看看,而我也实在的想会一会我
的柚子妹妹;姨妈是寄住在他的族人家的,我走进堂屋,张望了一会,听得里面纺
线的车喔喔的响,左边渐渐走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婆婆,我迎上前去,“请问,我
们姨妈……”这婆婆瞠目不知所对,而我已望见从右角的板门探出了一只头来!我
猛然一奋发,堂屋的静寂也立刻打破了:
“焱儿!原来是我的焱儿!”
“哈哈!妈妈清早打喷嚏,我就知道是有客来!”柚子妹妹出来笑成一团。
“车呢?——唉唉,这是你妈妈耽心我开不起车脚,亏了我的儿,怎么走!”
纺线的就是我的姨妈,纺车脚下一条短凳,凳上是姑娘们用的柳条盒,用了红
帕子盖着。姨妈一面欢笑,一面用衣角揩眼泪,——这是我所习见的脾气;然而柚
子似乎是哭过了不久的:依然孩子似的天真烂漫的笑,却又很不自在,当我无意的
瞥见她的眼角。
姨妈说我来得正好,旅居在数千里外,归来不是容易事,而自己身体的羸弱也
正是朝不保夕。又说,柚子平常总是念芹……
“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