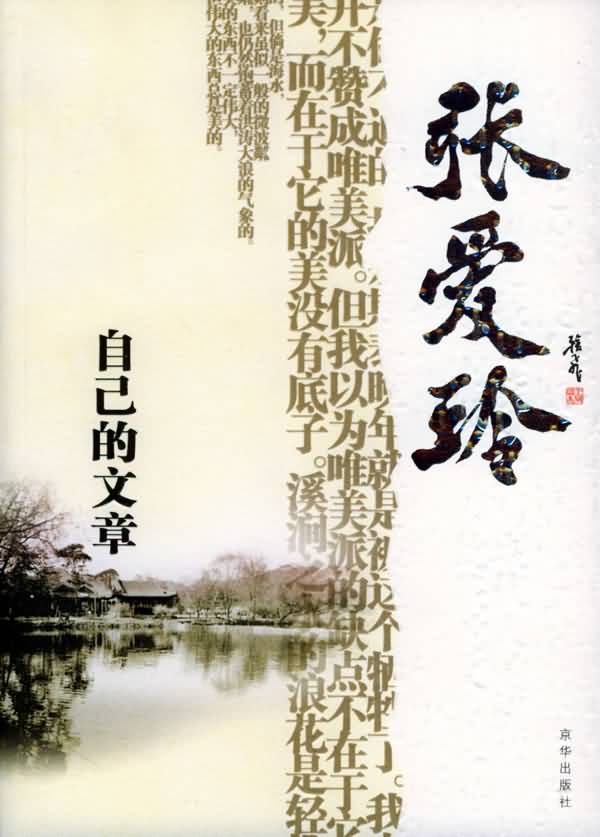方方文集-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一见他们几个就胃痉挛。金苟倒大度,笑说:“不见我们几个弟兄对胃有好处,
那也倒是一剂好药。”由此卢小波的活儿便再也没人帮忙了。
卢小波在重返仓库干第六天活儿时,觉得肩部的问题愈来愈严重了。起先一点
点疼,他未介意,到了第六天要抬一根工字钢上板车时,他才感到右边肩部一使劲
便剧烈地疼痛。站长还算客气,给了他两天假,让他去医院检查。在医院拍了片子,
才知道在公安局时,肩胛被打出了问题。医生说绝不可以再干重活,否则后果更严
重。卢小波拿了证明去找站长调换工作,而那一阵子,正好要挑一批人去公司培训
驾驶员。站长微微笑道:“你先回小队坚持一段时间,我会考虑你的。”
两月的时间在卢小波的焦虑和痛苦之中踱着方步缓缓而行。如同二十年漫漫时
光,终于到了张榜公布的这一天,然而卢小波却榜上无名。却见金苟的名字赫然在
纸上。卢小波站在榜前两眼发直,忽而他一下抓了榜纸,直冲站长办公室。
站长正呷着茶同书记两人谈着什么,见卢小波来,不等他开口,便已知来由,
站长把手一指:“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卢小波说:“慢你妈的屁!你当初红嘴白牙是怎么说的?”
站长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嘛,有些事情的发展是始料不到的。”
卢小波说:“这世上还有没有公道,金苟打人,我顶他坐牢,结果他倒成了青
工尖子,选拔去开车。我呢)”
书记说:“小卢呀小卢,不是我说你,你这么吵也没有用,关键是上面不同意
你上。”
站长说:“是呀,上面要挑一个后进变先进的典型,拨来拨去,还只有金苟合
适。过去他每隔半年都要犯点事,来我们站现已一年多了,没惹麻烦,所以只好推
了他。”
卢小波说:“上次打司机,不是他惹的麻烦?”
书记说:“在档案里是看不到的呀。上面认定他合适,我们也没办法。”
卢小波说:“上面为什么就不同意我?”
站长说:“这不明摆着,你不是刚刚从拘留所出来吗?”
卢小波说:“上面怎么知道我去了拘留所?不是说不记档案,不是说当一样特
殊的任务去完成吗?”
站长叹口气说:“所以你不了解情况的变化罗。我们是打算不记档案的,可党
支部开会一研究,觉得不记是违背党的原则的,所以还是记了。而上面,只看档案,
不听解释。”
卢小波挥起拳头在站长的桌子上猛砸下去,他吼着:“王八旦!婊子养的!”
然后吐出一串串污秽话,骂得站长书记面红耳赤。这大骂之中自然不少指向他们的
隐私的,比方书记睡了吊车班的小熊,才把小熊送去当了保管员。又比方站长叫大
维去公司汇报书记作风败坏之类情况,想自己当书记。等等等等。装卸站的站长书
记在几十年前也不过是小贩或扛散包的人物,几乎人人都有不甚光彩的历史。我们
常听老工人们编排他们,卢小波是顶职去的,想必知道得更多。卢小波骂了差不多
半小时,门口围满了闻讯而来的看客。看客们很安静地听骂,无人扯劝。卢小波骂
得没力气了,喊了声“天哪!”悲愤而去。门口自动闪开一条道,许多女孩情不自
禁在眼眶中流满了泪水。
卢小波一走,站长起来整整衣衫,说:“就凭他这样谩骂和污蔑领导,再关他
二十天也是应该的。”
书记则面色苍白,他颤抖着手指点着站长说:“你,你凭什么到公司告我和小
罗的事?你跟三八队的吴嫂的那一腿,当我不知?”
站长说:“那不一样。小罗是姑娘,吴红妹是个破鞋,她两个本质上有区别。”
门外未散的看客们哄声大笑,把适才的悲哀和眼泪又笑得退了回去。
卢小波说他在很多年后看了小说《基督山恩仇记),他说他好佩服基督山伯爵。
如果有一天,他也能像基督山伯爵那样可操纵些什么,他第一个愿望便是想把他的
站长和书记吊死,用一根女人的裤带。不过卢小波始终没有机会。在他腰缠万贯颐
指气使地行走在大街上,前后雇了两个保镖的日子里,早年的站长业已作古,他患
的是鼻癌,而书记则瘫倒在床,每日被儿媳妇喝来斥去,眼巴巴地讨一口饭水度日,
比吊死还令人觉得凄惨。他是骑自行车摔跤而中风的。卢小波为自己没有报复的机
会而叹息不止。
卢小波在那天夜晚开始了后来几乎成了一种习惯的沉思。他想这事怎么会走到
这样一步?他想究竟是他自己错了还是别人错了?他想倘若是他自己错了他又有什
么可以抱怨?而如果错在别人,那么他又有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们?一时间,他想得
双泪长流,他觉得自己何其渺小,又何其软弱无助。
那时的我正做着团支部的一个委员。我觉得如此对待卢小波显然很不公平。虽
然世上公平的事少得可怜,但这么明摆着地欺负人也未免过分。我对卢小波说不如
跟大维谈,让大维通过青年人的组织帮青年说几句话。卢小波一脸的不信任,他说
大维这个狗娘养的会帮我说话?他是他们的狗。他不咬我两口我倒感谢他了。我说
不妨试试。
卢小波那天便专门去拜访了大维。卢小波属沉默少言之人,俗话里有“不叫的
狗才咬人”一语,其意乃是不叫的狗比叫狗多一份心眼。卢小波显然也还是有心眼
的人,他居然知道大维擅奕,最喜围棋,便去友谊商店买了副云子,携带着上了大
维的家。
大维见云子自然眉开眼笑,爱不释手。及至卢小波提及正事,言需他大维帮忙
叫屈之时,大维却如烫手般将云子放了下来。大维说要得这副云子还不那么容易呀。
卢小波说我并不想要你帮我争取一个司机名额,我只想请你帮我说明我是怎么进的
拘留所,打架时我不仅没动手而且是准备扯劝的。大维作思考状,一只手又不由自
主搭在装着云子的草藤盒子上。好一会儿,大维方说:“好吧,我去试试。”
卢小波说大维的答话很聪明,那态度使他不知道说把这副云子送给他还是拿回
去。既是试试,就有可能什么都不干,送他一副云子不值。如果不送,他恐怕连试
都不试。卢小波犹豫几秒,还是放下了云子回家了。
卢小波再次去找大维时,大维正用他送的那副云子与入对奕。没等卢小波开口
说,大维便将他拉到外面。大维说晚上我来找你,这下棋的老兄是公司团委的,我
准备他下得高兴时跟他谈你的事。卢小波心里涌出几分感动。他说那你晚上来我这
吃饭?大维说好吧。
卢小波到餐馆端了几个菜,又买了些酒,红、白、啤三种都买了。不论大维喝
哪种,他都有对付的。
天擦黑时,大维来了,坐下即喝酒,白的。不等卢小波劝,便呼啦啦喝下三杯。
卢小波殷勤为之挟菜,且问怎么样?
大维长长地叹息着,嘴里塞进几块肉,方嚅嚅不清地说:“我先提的是你入团
的事,我知道你迫切想入团。可是,那老兄说不行呀。如果,没记档案,包在我身
上不成问题,可惜,入了档,我这边就没办法了。”
卢小波来了气,说:“我现在也不想要入团了,只要平这个冤。”
大维说:“你还敢提这事,你自己签了字,划了押,现在又来推翻,那么,追
问你一句,你为什么要蒙骗专政机关?让真正的坏人得不到改造的机会?故意给公
安机关多弄出个冤案,你是什么目的?什么动机?凭这,不光拘你,说不定还判上
几年,你想,这能开口么?”
卢小波两眼发直,他脑子里嗡嗡嗡地乱成一团糟。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呆
呆地望着大维喝酒吃肉,望着他佯做同情地边叹息边揩油沥沥的嘴,又望着他点着
了一根烟,无奈地摇摇头扬长而去。卢小波守着那桌残羹剩饭呆坐到半夜。后来。
他隔着窗子看到了一颗流星倏地滑落,他想又一个人死了,这个人便是我。很多年
之后,我告诉卢小波,大维其实什么也没对公司团委那老兄说,因为大维赢了那老
兄的棋,两人有些不太愉快。那时的卢小波只是冷冷一笑说:“说不说都没什么意
义。只是可惜了我那副好棋。”
卢小波在站里突然之间就换了形象,以致于初始时人们纷纷交头接耳说卢小波
的神经是不是有了点毛病。有一天站里所有的自行车胎全部消了气,而站长的车连
气门芯都被扔了。一时间站里骂声连天,都说干这事的是哪个王八羔子。在一片喧
嚣声中,卢小波大模大样站出来说:“哥儿们,别骂,是我干的。”骂人的人都怔
了怔,有个女孩问为什么这样?卢小波说要叫全站人重新认识我。所有听到卢小波
如此说的人都吃了一惊,便从那天起,人们知道原先那个沉默少言的卢小波再也不
会出现了。
大维迅速组织团支部委员开会,制订“帮救”措施,即帮助卢小波,挽救卢小
波。会上列举的卢小波的错误写了好几张纸,给人一种卢小波变化时间虽短,却已
恶贯满盈之感。比方干活偷懒,投机取巧;比方在公共茶桶里偷偷倒洗脚水;又比
方给书记的女儿打电话说书记出了车祸已送殡仪馆,而给书记打电话说他女儿被人
暗杀尸体已入冰库;还有拼命纠缠卫生员小茹,对她挑尽下流话说。(不过这事总
没第三者作证,只是小茹一个人向领导哭诉的,而这领导恰恰是她的表舅站长大人,
故而很多人认为是小茹伙同站长一起陷害卢小波。)至于卢小波在开会时故意吵闹,
跟领导唱反调,有偷办公室墨水和剪刀之嫌,等等等等。大维罗列了好几大张,然
后痛心疾首地说:“我们必须得把卢小波拉过来,不能看着他一天天滑下去而变成
人民的敌人。”
卢小波的如此之状,也极令我反感。虽然一度我曾同情过他,且帮他出主意洗
白自己,可他后来见到我也一口的油腔滑调。有一次甚至尖叫着把烟灰弹到我的脸
上,当时许多人大笑不止,令我愤怒异常。好在没多久,我便上了大学,离开了装
卸站,永远可以不见到那个卢小波。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天我乘船过江,在轮渡上遇到了卢小波。他若不喊我,我
差不多根本没认出他来。他戴了副墨镜,嘴角叼了一支烟,一脸的痞子气。我刚上
船时,没坐定就看到几个男女青年在船尾打闹着调情,类似的场面我们平日也常能
见到,这些人被我们称作“油子哥哥”和“油子姐姐”。整个城市中,他们无处不
在,所以我颇有见多不惊的派头。孰料我刚坐下,他们中一个“油子哥哥”朝我走
来。他摘下墨镜,痞着脸说:“小姐,不认识了?我吓了一跳,以为遭到流氓骚扰,
正欲躲避,忽又觉得来者面熟,定了定神,方惊叫道:“是你,卢小波?!”
便是在那一次的相遇中,我知道卢小波已经被开除了。我问他可是以干木匠活
儿为生,他说那不是太累了?他说他隔三岔五地打打麻将,赢了钱就又能过几天。
有一天赌到半夜,他赢了六百块,结果被公安局抓赌抓住了,钱被没收了不说,还
劳他又蹲了三个月拘留所。卢小波说这些话时很轻松很从容,也很诙谐。他说:
“我这是二进宫了。”他的脸上再也没有那一天警察将手铐戴到他手上时的那份惊
恐了。我说你变得好厉害呀,他说你不也变了?原来是个拉板车的,现在派头好大,
我笑了笑,觉得他说的是。
船靠岸时,卢小波的几个狐朋狗友对他打着唿哨,其中之一笑喊道:“嗨,是
你的老相好?”卢小波朝他笑笑又望着我说:“你心里只管把我们当一帮流氓你就
不会计较了。”我没作声,脸上显然也不悦。
几乎快跟卢小波分手,卢小波忽而说:“你还记得金苟不?他被毙了。”
我大惊,问:“为什么?”
卢小波说:“他拿了驾驶执照后,没多久便跑长途。路上有些乡下妇女想搭便
车,他总是很友好地让她们上来,然后找个静处把她们奸了。他干了好几十回。有
一回叫人撞上,逮住了。一审讯,金苟便屁滚尿流地交待出来了许多,这小子想着
坦白可以宽大,结果,给毙了。也可怜,我代他受过,他老婆还是没跟他,只好走
这条路,早知如此,当初岂不是送他去公安局,他不致于死,我也不致于……”
我说:“真的,人有时真是把握不住自己,稍微的一个闪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