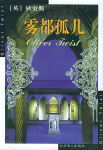守墓孤儿-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是庄仲依旧有些冰冷的手掌。
“薛大爷……薛大爷……您起来吧,”庄仲也跪在那冰冷的地面上地面上,抽咽着说,“是的,我恨你们,恨你,薛强,还有您,薛大爷。你们夺走了我整个幸福的童年,让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孤独无助的世界中,即便有很多人照顾我、关心我,但始终缺少家庭这个重要的东西……”庄仲顿了顿,又接着说道:“但是,您知道吗,我现在最深的记忆并不是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那些我早已经淡忘了。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的始终是您那慈祥的脸,还有那一次次接受您帮助的感动。我虽然现在知道,您那是在‘赎罪’,但是,我却不能把您对我做的那些事冠上‘赎罪’这个词上。我很明白,如果您当时一走了之,估计我永远都找不出撞死我父母的人。我也明白,过去的事再也无法挽回,与其怨恨你们,还不如原谅你们,既然事情能向好的方向发展,我怨恨你们能起什么作用什么用。所以说,我要谢谢您,真的……很谢谢您。”
“这是你给我的结果吗?”薛大爷抬起头看着庄仲,问道。
庄仲望了望窗外,那逐渐从圆满退变为残缺的月亮挂在那深邃的夜空中,而世间的事情何尝不是这样,圆满中带着残缺,残缺中影射着圆满。
“是的,这就是我给的结果。”庄仲微笑着回答。
“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庄仲。”薛强扶起薛大爷,说。
“我不要求别的,逢年过节多来看看我父母吧。”庄仲闭上眼睛说。
打开门,已经不算凛冽的寒风吹进屋中,将三个人脸上的眼泪一下子吹干了。看着眼前那一座座墓碑,庄仲的心里五味杂陈,不知是要为自己的宽容而轻松,还是要为自己的宽容而惭愧。而这吹拂过来的风,是在赞许着自己的宽容,还是嘲笑着自己的宽容呢?
“薛强,你带着庄仲回他的学校吧,今天我在这儿守一晚。”走出小屋很远的薛大爷突然说。
“爸,可是您的身体……”薛强担心地说。
薛大爷摆了摆手,走出门外,说:“我以后可能在没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呆一晚了,我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了,这算我最后守一次这片墓吧。”
薛强刚要开口制止,薛大爷抢过话来,说:“没事,真的,就这一个晚上,以后再也不过来了,因为我这十多年的愿望已经达成了。”
庄仲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薛大爷走回那间小屋,看着那熟悉的背影消失在那片看似恐怖的黑暗之中。
回学校的路上,庄仲和薛强没说一句话。下车的时候,庄仲撂下了一句:“谢谢您,薛叔叔。”
庄仲就这么向着宿舍楼走了,他没有看到,薛强在车里面哭了很久才离开。
这天晚上,庄仲伴着黑军的鼾声睡了一个好觉,一点梦都没有做,或许是因为他不再需要在梦境中宽慰自己了,而现在的生活才是他最想要的——能宽恕别人,能享受被宽恕的人人带来的爱与释然。
庄仲这一觉快睡到了转天的中午,要不是薛强的一个电话,他还要睡下去。
而薛强电话的内容大体是:薛大爷去世了。
薛大爷的遗体是在墓园的一座墓碑下被发现的,那座墓碑是他老伴儿的墓碑。听薛强说,薛大爷去世时,嘴角还留着一抹微笑。
挂了电话,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庄仲的脑海中不自主地幻想着昨晚自己走后的场景,那是一幅只可能出现在科幻电影里面的图景:
那位七旬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踱到庄仲父母的墓前,擦拭着那两块之前擦过无数次的墓碑,然后向他们鞠了一躬,问他们:“你们的孩子今天原谅我们了,我之前无数次地请求你们原谅,你们不能回应我,今天他给了我结果,这算不算你们的意思呢?”
老人在墓前站了一会儿,又走过那一座又一座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墓碑,用手中那块破烂的抹布轻轻地擦拭着那一张又一张凝滞着时空的脸,那张养了两个不孝子的老人的脸,那张为生活所迫从十七楼跳下的父亲的脸,那张把全身几乎所有的器官捐献出去的孩子的脸……
最后,他走到自己老伴儿的墓碑前,如释重负地对她讲述着自己和孩子被宽恕的喜悦,和那些百谈不厌老掉牙的情话。
可是,这时候,有几个恶鬼过来缠住这里的的墓碑,它们狂笑着,嚎叫着对老人说:“哈哈,我今天就要来取这些人的魂,让它们堕入十八层地狱,每天受着不同的苦难,而且永世不得超生,哈哈!”
老人的白发被恶鬼带来的风吹乱了,他一只手拽着老伴儿的墓碑,一只手挥动着,想赶走那些不速之客:“快滚,不许你们碰他们,我是这里的守墓人,快滚!”
“没用的,哈哈,你是斗不过我们的!”那些恶鬼依旧在狂笑着。
老人费力地站起身,用那单薄的身躯迎着这些黑气,任凭那阴风吹动着那衣襟和那凌乱的白发:“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不会!”他说着,举起一只手臂对着天空,鞭打着从头顶掠过的那些黑影。那些黑影发出阵阵的哀号。
“老东西,看你能撑多久!”恶灵们在天空中和他的身边打转,即便感受到彻骨的疼痛,可是依旧不愿散去。
老人就这样撑着,一直撑到了黎明的到来。那是怎样的黎明啊,只一束光,那些黑影就伴随着惨叫声与哀号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此时的老人已经是精疲力竭。
“一个平凡人能撑这么久,实属不易。”那晨光开口了。
“呵,那是当然;”老人轻笑了一声,说,“因为我是个守墓人。”
老人睡了,疲惫地睡在这一道晨光中。
庄仲赶到墓园的时候,那里一往如常,悲痛的人依旧在悲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依旧充满着希望——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地平常,没有因为这里守墓人的逝去而改变。他来到自己父母的墓前,发现那里的确有被人擦拭过的痕迹,而老人的身影仍旧在他的眼前闪现着,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然后转过身,对庄仲欣慰地笑了笑。这次,庄仲没有哭,反倒觉得一丝欣慰与高兴,毕竟老人没留下什么遗憾,他是笑着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也庆幸着自己在老人生命的最后一刻到来之前,给了老人一个想要的结果。
走进小屋,屋子里面那一切依旧没有变:一架摆满了书的书架、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台折断了天线的收音机和一架火炉。钉子依旧趴在火炉旁边,看到庄仲,一下子奔了过来。庄仲抱起钉子,仔细地看着它那细细的瞳孔,想从那一丝黑色中看清薛大爷在这片墓园里面那最后的影像。但是,那瞳孔里面却只有庄仲那细细的面容与身影。
这时,钉子猛地跳上桌子,不停地用那肥肥的爪子蹭着桌子的边缘。庄仲走到桌边一看,几个歪歪扭扭的刻字显现在他的眼前,很清晰,也很刺眼。
“谢谢,加油!”
他伸出手抚摸着这几个刻字,抚摸着老人留给他的最后一样东西。而那一笔一划仿佛通过了他的手指刻进了他的心里,给了他无法形容的力量。
薛大爷的丧礼时,没有很大的排场,也没有那烦人的吹拉弹唱,更没有那漫天散布的纸钱与浮夸的烟花。在灵堂上,只有披着一身孝服、红着眼睛的薛强,一张微笑着冰冷的遗像和一具同样微笑着冰冷的遗体。庄仲冲着薛大爷深深地鞠了一躬,却感到从那冰冷的遗体里面散发出难以忽略的热量,那种热量虽然微弱,但却很特别。
后来薛强来墓园找过他,说小屋不会拆,他会把薛大爷的墓安置在这里,安置在他母亲的身边。他希望庄仲还可以留在这里守着,在这个无数次庇护他的地方守着。他还说这不是施舍,更不是补偿,而是请求。庄仲答应了这个额头上留着永远褪不去的伤疤的人的请求,用他的话来说,为了钉子,为了那几个刻字,为了那化解了一切冰封的人,他同意留下来,也愿意留下来。
过了几天,庄仲无意中发现墓园中又多了一座碑,上面映着那熟悉的慈祥的面孔。庄仲像薛大爷那样,擦拭着那座碑,把它从头到尾擦得干干净净,把这个被救赎的灵魂的污点擦得干干净净。
“尘缘如梦,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
老人就这么去了,带着庄仲的原谅,带着对这个世界的不舍和无上的责任感去了另一个世界。庄仲经常孩童般地想人死后会去哪里,但是却不能好奇地去尝试。他想知道,想知道他的父母在那个地方生活的可好,是不是还在一起,还是因为现世的缘分已尽而经受着无休止的别离。而如今,他更想知道上天会给予薛大爷这样曾经隐藏着那罪恶的事实但却进行着无休止的救赎的人怎样的结果。但是他希望会是一个好结果,就像现世里努力救赎着一切的姜山那样,有一个好结果。
这也许正是救赎的意义吧。
第九章 聚散
不知不觉,三个月过去了。这三个月,庄仲过得很踏实,也很快乐。虽然没有了薛大爷,切断了对家名的想念,删除了对父母的牵绊,但是他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感受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份存在感,这是姜山带给他的,是王雅温倩黑军带给他的,也是薛大爷和薛强带给他的。如今,心中那一块挥之不去的阴霾就像被一根散发光芒的棍子一下子打散一般。那份隐藏在心里面父母双亡的痛苦如今看来却也是被那神圣的救赎所击退。
而这三个月里,他又见到了那些故人,那些在他换了心境之前遇到的、曾经让他的心更加冰封的故人。而如今,虽然他们可能还像之前一样对着那块墓碑咒骂、抱怨、哭泣、绝望,但在庄仲眼里和心里,他渴望着,渴望化开那些冰封的人和事,化开那些冰冷的墓碑下面那对现世存有抱怨和绝望的灵魂——就像这些日子身边的人化开自己一样。
那个有着两个不肖侄子的老人曾经来过,他说,两个孩子为了遗产后来对簿公堂,现在也断绝了联系,或者说基本断绝了关系。他仍旧像之前那样,点起一支烟放在他哥哥的墓碑上,等着它燃尽,然后看着那随风飘扬的烟灰和烟头对庄仲说着抱歉。
“我没有孩子,所以从那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我就特别疼爱他们,可是没想到,唉……”老人吸着闷烟,说:“不管了,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也没义务管他们,不过还是盼着他们能像以前一样……”
后来,那个丈夫跳楼的女人又在儿子和孩子的姑姑陪同下来了,不过相对于那一天,那个女人气色好了很多。孩子的姑姑也没再穿着那死气沉沉的黑衣,取而代之的是天蓝色的长裙。这一次,孩子的姑姑不再一直张望着那个绝望的女人了,而是带着孩子来到小屋里找庄仲说着话。
“来,哥哥陪你玩一会儿。”庄仲拉过那个孩子。那个孩子也不认生,好像和庄仲很合得来,和他打'。 '着闹着,逗着到处乱窜的钉子。
“孩子的妈妈最近精神也正常了许多,”孩子的姑姑说,“但是生活还是很苦,不过我们几个亲戚帮帮她也倒是能渡过这一阵子,只能盼着以后情况能好些。”
女人领着孩子走了,庄仲看着这三个人的背影,却也失了当时的那种凄冷。就如同那个恨着两个不肖侄子的叔叔和那个苦命孩子的姑姑口中的“盼着”两个字一样,庄仲相信,只要还有去“盼着”的信念,一切都会变好的。
这三个月,庄仲时不时还要去学校完成毕业设计,时不时地去招聘会上投递着自己的简历——他已经能熟练而不违和地以一个正常人的心态去做一些正常人应该做的事。在摩肩接踵的招聘会上,他感受到那年轻力量的律动和那不能够完全囊括这分力量的空间,那揉皱的衬衫和歪歪扭扭的领带下面永远是那被这个世界认为尚且幼稚的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面试官问。
“庄仲。”庄仲自信地回答,俨然没有了当年进学生会时的那种羞涩。
“你认为你有什么优势?”面试官又问。
庄仲笑了笑,看着眼前这个像是对着一个个愚人的商务人士,说出那原来的和最近培养出的优点。
“独立和自信。”庄仲回答。
那个面试人似乎对庄仲这种“泛泛”的回答没有什么兴趣且不是很满意,这是从之后没有一家公司给庄仲发来后续消息的这个情况看出来的。但是,这确实是他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没有几个人可以替代和超越。
当然,庄仲也不会放弃墓园里面的活儿。几乎每天傍晚,无论多忙,他都会把墓园里面扫一扫,无论扫得仔细还是粗糙。虽然他知道,这片墓园本不需要一个打杂工的扫墓人,但是无论对于薛大爷还是自己的父母,或是那一个个沉眠在地下或罪恶或中庸或神圣的灵魂,他的这些一举一动都是一种荡涤,一种对美好归宿的指引。
姜山有时会找他来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