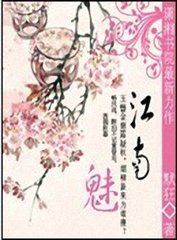烟波江南-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当时看见躲在一边的手下就有气,心想要是有个有能耐的帮我,也不至于一上任就被人砍了。六槐说这话就说明有商量的余地,这样的人有本事又重义气,治他的罪不如纳他为自己所用。所以我乖乖地代前任付了钱,为此花光了积蓄,又拒收了几回大礼,六槐果然心里过意不去,自己找上门来帮我的忙了。”
听到此处,秦海青与池玉亭心中不禁暗赞这位安海县令的气量,其实压治不如疏导这个治民的道理很多官场上的人都懂,只可惜能做到的却不多,安海县能够做到实是不易。
一个水卒跑了过来,“秦小姐,可以上船了。”
二人于是站起来与县令告别,安海县令拱手相送:“二位一路平安!”
第四章
船离了码头,往深海里去,渐渐的风浪大了起来。秦海青大江大河上坐船也不少,可是那总比不得海里的浪大。今日的海风有点儿大,船行平稳,秦海青虽不觉头晕,但甲板起起伏伏还是让她觉得不习惯,走在棉花上好象也是这种感觉。
秦海青忽然想起她初出道时的一件事,笑了起来。
“老头儿,你还记得江南的棉花堆吗?”她问。
池玉亭想了想,也笑了起来,“记得,抓强盗的时候你一脚踩进装棉花的大车,陷进去出不来,直呼‘救命’,好容易才把你拉出来。”
“那时可真是什么都不懂,好不容易找到的强盗也趁机跑了,事情差点不可收拾。”秦海青笑道,“现在总算明白些了什么,可是这一行也算做到头了。”
“大小姐,安定下来并不是件坏事。”池玉亭劝道,“毕竟,老爷还是希望你有个好的归宿。”
秦海青沉默了,伏在船栏上望着浮在海面上随浪起伏的一只海鸥出神,好久,她慢慢地说:“其实,这次出海,我也有不妙的预感。”
“大小姐?”池玉亭的神色有点吃惊,但他没有开口劝她。
“怎么?不劝我‘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吗?”秦海青扭过头,微笑着望着池玉亭问。
“箭已离弦,说了你也不会回头。”池玉亭平静地回答,“既然知道前面的路不好走,只好小心地去应付了。”
“是啊,反正是最后一次了。”秦海青又回头去看海,“老头儿,你老实告诉我,我爹是不是对你说过什么?”
“你指什么?”
“我是说……你娶嫂子之前,爹就不太喜欢我跟着你出去办案子。”秦海青慢慢的说。
“那是当然的,老爷心疼大小姐,不希望你在外面受苦。”池玉亭笑眯眯地回答。
“算了,就当我什么也没问。”秦海青无表情地说道。她解开裹着手的绣花帕子,就着松手,帕子落入海中。
“伤还没好罢?”池玉亭有些诧异,“这么好的帕子,扔了怪可惜的。”
“老裹着也不行,”秦海青不以为然,“让手透透气。至于帕子嘛,我懒得洗,以后有的是时间,可以再绣。”
池玉亭觉她说得也有点道理。
“我给婉儿买了个项圈,很漂亮呢。”秦海青淡淡地笑。
池玉亭听了,神色有些尴尬:“是么?谢谢,我倒是忘了给她们带点什么。”
“老头儿就是这么迂!”秦海青摇头直乐,“江南的胭脂好,嫂子那么漂亮,不给她带点儿可说不过去!”
“回来再买罢……”池玉亭的脸竟少见的红了。
两只大船乘风而行,不觉已走了半日,先前一望无垠的海前方影影绰绰出现了一些黑点,那是海中的一处岛群。肖将军传下令,各船上水卒都紧张起来,做好临战准备。
原来这是江浙一带偷往闽东沿海去的船路,明朝海禁甚严,海上行船并不多,偶有胆大的违规行船,却常在这里遭劫。此处虽不是被抓的海盗所指的海盗老窠,但从此处过,是不得不小心一些的。
“肖将军请二位不要在船上随意走动,以免有危险。”一位水卒传来另一艘船上肖将军的嘱咐。秦海青与池玉亭应了,退到舱口观看。他们是来找人的,不是来打海盗的,并不想参予这种争斗。
船渐渐驶近岛群,将从其中一些岛屿间穿过,两船四方都有水卒注意海况,而高高的桅杆上,亦有水卒四眺。
此处的岛群多为礁石,也有些上面覆盖些薄土,但多长满密密的草木,疑为毒虫蟒蛇出没之地,绝非人迹所能至之处。
秦海青二人正细观海中诸岛,忽听驶在前方的大船桅杆上传来“呜呜──”的螺声。吃了一惊,知道有事发生,果然见水卒们俱将兵刃提在手,脸色郑重的聚到船边,而所乘这条大船亦随前行船方向拐了个弯,直驶向其中一个岛屿。
“如果遇上海盗打起来怎么办?”秦海青问。
“有些麻烦,若是与他们交恶,只怕在他们之中找人就难了。”池玉亭答道。
“那末,我们退舱中去罢?”秦海青向舱中退去。
“等等,先看看是不是遇上海盗了。”池玉亭拉住她。
前面的礁石岛屿成半环形,船转过弯后,众人果然看见礁石环抱中有一船型的物体异样地在海面漂着,驶近一看,正是一条中型海船。船身破烂,甲板上一片狼籍,似被洗劫过,而靠船舱的甲板处,棕子般绑着八九个人,这些人不停地挣扎,见有大船靠过来,越发挣得厉害,被堵住的口中发出“嗯嗯”的声音。
秦海青远远看见被绑的人中有几个面熟,仔细看去,却见其中的一个妇人正是昨日街上卖解的艺人。
“哦……”她明白了,“是从安海县出来的艺人,好像被劫了。”
剿盗船在肖将军的指挥下小心翼翼地接近了被劫的海船,七八个水卒持刀跳过船去,不急于解开被缚的船上人,先仔细地把整艘船搜了一遍,确信没有陷井,这才将他们松开,押过剿盗船上来。
秦海青二人在这边船上看着,见那几个艺人个个如烂泥一般四肢瘫软,想是被吓得够呛。秦海青心里记挂着那个卖解的妇人,眼睛便直盯着她瞧,见她被一两个水卒搀上甲板,一付神志不清的模样。不多时,那边船上传过话来,肖将军请秦姑娘过去,帮助照看一下女眷。
原来这趟出海虽说也有医者跟着,但船上除了秦海青外清一色是男丁,这卖艺的妇人神智不清,需人照看,而艺班又没有其他女子,反正秦海青又没有剿盗的责任在身,肖将军不免打起她的主意来。
秦海青如何会不知道肖将军的主意?想那肖将军原本就不喜欢女子跟着上船,据说是不太吉利之故,现在给她找些事情做,也不妨顺他的意思来,何况秦海青也想知道那女子的情况。
两船间搭上跳板,秦海青扶着池玉亭的手走了过去。肖将军见她来,拱了拱手:“秦姑娘,有劳你照看伤者。”秦海青手放腰间微微弓身,还了一福礼:“不敢。”
走江湖按江湖的礼数,在官场按官场的规矩,秦海青在这方面可是半点儿也不马虎。肖将军见了她的福礼,楞了一楞,待回过味来,秦海青已被水卒引进舱里。
“嘁……”肖将军瞪着铜铃一样的豹眼直吹胡子,“船上竟带上了女人!”
“不是正好派上用场了吗?”池玉亭没跟着进舱,站在肖将军身后眯着眼睛笑。
肖将军回过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以为我会随便让一个女人上船吗?可是,她居然有四品的官衔!”他不满地吼道,“你们把出海当成什么了?这可不是你们在京城里出外踏青!”
池玉亭搔了搔脑袋,不气不急:“我想,大小姐不是出海来玩的吧?”
肖将军见他那模样,又好气又好笑,可又不好再发作,“你们……可真难缠!”他叹道。
难缠就难缠,没这点缠人的韧劲,天下很多事就做不成了!秦海青倒也不一定知道肖赤雷在甲板上气乎乎的嚷什么,但她根本不在乎。“反正你在背后骂什么我也听不到。”她笑眯眯地自言自语。那卖艺的妇人睁开眼睛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秦海青那张自由自在的笑脸,然后,她听见秦海青温柔地说道:“我想,你该不会是贾秀姑吧?”
第五章
再次见到卖艺妇人之前,秦海青对于她的身份是一点儿也没有怀疑的。那不过是街头常见的艺班,几个箱子,几个汉子,再加上一个女子,表演一些走绳、弄丸的小节目,日日在江湖行走,不过为找碗饭吃。走江湖的杂耍艺人几乎人人都有些功夫,这个并不奇怪,虽偶尔也会有些武艺高强的世外高人隐身其中,但艺人们多半却只是些护场健身的把式。
秦海青昨日在街头见这女子耍玩水流星,便知这女子身上负有武功,她手上的玩艺儿系上装水的碗是水流星,但若换了尖刃便是线镖,换了铜头便是流星锤。这女子招招式式可放可收,把握得度,秦海青只道她是杂耍艺人中本事较高的那一类,倒也没有多想。何况海盗袭船,多是近身肉博,用的砍刀为多,怎么也不可能用这样的长软兵器,故而是无法将她与贾秀姑联在一起的。
可是再次看到卖艺妇人后,秦海青的想法动摇了,她原本就是个诸事小心的人,在这敏感的时候遇见卖艺的妇人,不免就有些猜疑。秦海青突然想起了妇人微笑着对自己说“小姐好心,好心必有好报”的样子。杂耍班昨日出现在县衙附近,今日出现在剿盗的必经海路上果真是偶然吗?贾秀姑,这个传说中聪慧而又深得众海盗拥护的女盗首明知手下被擒,会如此不动声色?最令秦海青不放心的是她突然想起昨天从杂耍班旁走过时,那个正在收拾道具箱的杂耍班汉子与同伴闲聊说的话,那是西北口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贾秀姑正是从西北回乡的!
妇人却是一付迷惑的样子:“小姐,贾秀姑是谁呀?”看模样要支撑着起来,身子却只是打颤。秦海青见她虚弱的模样,温和说道:“这样说来,莫非是我弄错了吗?”伸手作扶状,将及妇人肩头,一翻掌,并指向妇人肩窝穴道点去。妇人下意识的一缩肩,抬手反格,刚一抬手,秦海青的指头却已收了回去。
“果然,你根本没事,我已给你把过脉,不用装了。”秦海青抱拳含笑道,“在下秦海青,京里来寻朋友的。我对大嫂并无恶意,不管你是哪个,先报个名吧。”
妇人听了这话,楞一楞,身子也不颤了,含笑望望秦海青,“秦姑娘果然了不得,既是这样,与你装下去也无益。”她亦是抱拳还礼,“我就是贾秀姑,你要找的朋友,可是南儿带回家的那位玉版姑娘吗?”
贾秀姑的爽快着实把秦海青噎了一噎,随即点点头。
“秦姑娘,我虽是南儿的姨母,但亦是好久未见,关系较为生疏,你和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我不便多管。我到这船上的意思想必你也是清楚的,如果你不插手,事毕之后我会给个便利,允你与南儿他们一见。”贾秀姑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可句句话儿份量极足。
秦海青摇摇头笑道:“贾姑若能允我见玉版真是感谢不过,只是贾姑也当明白我也是官场上的人,若是为了自己的一点事儿放着这两船百十号兄弟的性命不管,只怕贾姑允得,海青自己的良心也是不允的。”
贾秀姑叹了口气:“秦姑娘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怎么也只听些传闻断事呢?”
“此话怎讲?”
“秦姑娘是据什么断定我们便是海上杀人劫货的盗贼?”
“……难道不是吗?我虽不是本地人,但来此后也没少听人说起,这条海路上多劫匪,杀人越货,煞是嚣张。”
“这事倒也不假,只是秦姑娘又是据什么断定这杀人的劫匪便是我的人?”
“我不敢断说这便是贾姑的错,只是沿海一带提起这周遭最有名的海盗,人皆指贾姑,只怕也不是无缘故的罢?且不说这些,贾姑的地盘远在海中,若非打劫,又何来绐养养活你手下那一帮兄弟呢?”
贾秀姑听秦海青的语气硬朗起来,也不生气,反问道:“我们若是杀人越货的海盗,那足以在海上养活自己,又何必派人来岸上进货,以至被捉住呢?”
秦海青听了此话,心中确感蹊跷,问道:“贾姑这样说,是指杀人越货的海盗另有其人?”
“只怕我这么说了,你也不会信吧?”贾秀姑苦笑道,“秦姑娘不是海边人,自然不清楚这儿的情况。若说我们是海盗倒也不错,不理海禁私自出海的人,若想保全性命,若不倚仗些刀兵绝对不行。可是我们虽说自成气候,却也是穷苦人出身,与岸上人原是一家子,怎会轻易杀我乡亲呢?”
“那末,贾姑自认自己是什么人呢?”秦海青反问。
“生意人,”贾秀姑轻松地答道。“我们只是一群有自己领地的生意人,与东瀛等地做点生意罢了。”
“私自做海上的生意是不允的罢?”
“若真依了海禁,那么许多人便断了生路,即使我们不做,东瀛人也会偷偷来做。我们不依海禁做生意,所以官家与我们结下怨仇便深了些。不巧我们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