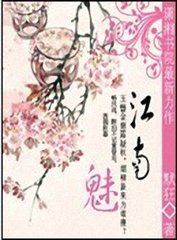烟波江南-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儿就好了。”
常妈妈始终是个稳重的女人,尽管不难看出她内心的不安,但她却安静地听完了冯吉所有的话,这使冯吉在私底下也不得不佩服她的冷静与贤淑。“就按冯先生说的办吧。”常妈妈听完了冯吉的话,深深地施了个礼,神色自若地说,“夫人的事也就是奴婢的事,奴婢没有什么可说的。”冯吉点了点头,停了停,他用一种关切地语调说道:“常妈妈好久没有回乡去探亲了吧?这次事完了,我让帐房上多支些银钱,你好好回去探望一下吧。”常妈妈脸上浮起一丝淡淡的苦笑:“谢谢冯先生挂念,奴婢与侄儿家已久没来往,去不去已不打紧。”冯吉心中沉了一沉,常妈妈自从守寡后,侄儿便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现在看来这份亲情也是极薄的。
“冯先生,许爷回来了,现在灵堂。”一个家人的声音从院外传来,声音不大,很守冯府的规矩,不进这院子也不大声喧哗。“知道了。”冯吉轻轻应了一声,回头深深看了一眼常妈妈,常妈妈垂首送客。冯吉向院门口走去,那常妈妈便又回房中去扶冯夫人出来接着梳头。走到院门口,冯吉下意识地停了一停,复又站在院边那阴影中向内看去,不一会儿,见常妈妈扶冯夫人出来在原先的地方坐下,用那木梳替她梳着长长的黑发,继续对那个什么也不知晓的女人絮絮说了开去:“夫人啊,您不知道我那侄媳妇有多贤慧,人长得好,性子也不错,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当年可是我们那块儿远近闻名的好姑娘,我那侄儿为娶她不知给了托媒的肖妈妈多少好处,只可惜命苦,养下的三个娃儿都满月便没了……”
冯吉看着,忽然觉得对常妈妈有了一种深深的歉意,这是个好女人,他想。不带一丝儿声响,他默默地离开了这个青竹环抱的小院。
许年在前面的灵堂内,面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冯吉从后院走过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似乎没有离开灵堂的意思,这使冯吉想到他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办。于是他走了进去,走到许年的身边开口说话。
“你最好不要带着凶物到这里来。”冯吉皱着眉头指了指许年腰间的长剑。许年没有反驳,只是微微颔首:“是我疏忽了。”“那么,你是追掳走冯小姐的人去了,可追到什么没有?”冯吉问。许年指了指灵位,冷冷地说道:“你认为在他面前谈好吗?我看还是换个地方吧。”冯吉正欲反诘,抬眼遇见许年的目光,只觉得那目光很深,有些他不太喜欢的东西,于是,他决定不直接去接受这个挑衅。“好吧,我们换个地方谈。”他向门口走去,许年跟在他身后。走出门,冯吉突然停下脚步,回头问许年:“你……怎么想到来这里?”许年的品级高于冯年瑜,冯年瑜死后,与他没有什么私人感情的许年根本就没有兴趣来这里。许年的嘴角难得地浮起一丝笑意,“一个迂人,我来瞧瞧他的结局。”
冯吉自然不好多说什么,许年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已经不太清楚,其实大家都变了,与其说是旧交,不如说两个人才又重新认识。或许是因为还没有从刚刚那种思绪中解脱出来的缘故,冯吉忽然想起了七年前在开往塞外的北伐大军中遇见的那个叫李年的小侍卫,那个有着明朗笑意,满是自信和傲气的家伙。“啐……什么都是可以变的。”冯吉心底暗暗地骂道,但他毕竟是个有涵养的人,什么也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只是默默地将许年领到他的房间。
许年走进来,仔细打量师爷的这间居所。房间不大但很整洁,摆设也十分的简单,靠窗的几桌上整齐地摆着一撂帐本和文房四宝,此外,还有一个算盘。“差了件东西。”许年说。“什么?”冯吉冷眼看着许年在房中踱步。许年将腰间的长剑解下,贴在对面的白壁上。“我不需要这种东西。”冯吉皱了皱眉头,“拿下来。”许年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收剑回腰,在屋中的桌边坐了下来。
“要不要喝酒?”冯吉问。许年点点头,冯吉走到橱边,拿出一壶酒,当他回过身来时,突然看到一道白光直向眼睛刺来。冯吉没有动,白光在碰见眼睫的一瞬间停住了。“不需要这种东西?”许年收剑回鞘,重又回桌边坐下,“一般人就算不知道怎么反抗也会试着躲避,你连眼皮也不眨一下,这又怎么解释呢?”冯吉的脸色丝毫未变,他走到桌边坐下,给许年和自己斟上酒。“处事不惊和舞枪弄棍有必然联系吗?许公公这次来曹州,好象对我意见很大,不是来叙旧,倒是来找事的。”许年不回他的话,将杯内的酒洒了,自己动手再斟上。
“这么不给面子,连酒也不屑于和我喝了吗?”冯吉皱眉问道。“这只是我的习惯,很多年了。”许年面不改色的回答,将杯子伸过来,在冯吉的酒盅上轻碰了一下,一饮而尽。“很多年?是啊,已经过了很多年。”冯吉有些恹恹的回答,这带着些惆怅的语调不经意地挑起了许年心中的某种愁绪。“我记得,我还欠了你一条命。”许年把弄着手中的空盏,轻轻地说。冯吉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那种事情,还记着干什么?”他提壶再为许年满上,许年也不接话,只是小酌。“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这样对着来,”冯吉的声音变得和气了许多,“自打见面我们之间的味儿就不对,许公公对我生疏了很多嘛!”许年抬眼看了冯吉一眼,答道:“只怕生疏的不仅是我罢?”
冯吉不看许年,将眼光游离在外,似乎是很漫不经心地问道:“许公公还记得我们上次喝酒的情形吗?”许年看着冯吉,一种难言的滋味涌上心头,“记得。”冯吉脸上也有一丝也许只有许年才能体味的愁思。怎么会忘记呢?那是在土木驿站的最后一夜,有城墙的怀来镇只在几里之外,然而因为王振公公的阻止,皇上拒绝了进城避难。蒙古人于是包围了这支没有水源供应的军队,兵破就在眼前。在那个漆黑的夜里,将做殊死一战的儒将冯吉遇见了持剑逡巡的公公李年,两个相识于战场又将相别于战场的朋友对视无言,凄怆地大笑几声后,在胡营传来的号声中分饮了冯吉身边最后一壶酒,洒泪而别。
忽然,冯吉扭过头认真地对许年说:“许年,还当我是朋友的话,听我一句:你走吧,别管这里的事了。”
许年楞住了,半晌,把酒杯慢慢放下,“你还当我是朋友?”他问。冯吉望着他,眼神渐渐地又转为先前的那种冰冷,“什么意思?”许年道:“你操纵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却让我在里面乱转。”“我?”冯吉放下酒杯,“我什么也没做。”许年哼了一声:“我不知道冯吉居然会成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总管,而且一做七年。”“你想说什么?”冯吉面无表情地问。“你在这里是有目的的,你计划了很多事,冯瑶环的藏身处是你告诉的蒙珠尔嘎,”许年直盯着冯吉说,“而且你也很清楚冯年瑜被刺的事。”
冯吉的面色有些发白,但仍然看不出他有什么紧张。“我还是那句话:许公公不可瞎猜,需知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许年冷冷一笑:“我先前或许是瞎猜了,但要我相信这整件事仅仅是复仇只怕不行。蒙珠尔嘎背后还有人,我要知道那是谁。”
冯吉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拿起酒杯继续喝酒。许年也不逼他,也啜了两口。“冯夫人住在哪间房?”忽然,许年问道。他看到冯吉拿酒杯的手微微颤动了一下,“你问这个干什么?”冯吉抬起眼睛。“如果你不说,我去找蒙珠尔嘎,她会说的。”许年用指尖轻轻叩着桌面,很轻松地回答。冯吉的脸色十分阴沉,“够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他说,“我也知道你来曹州是为了什么,好吧,我们谈谈。”
从冯吉紧绷的脸上不难看出他心中的极度不快,但是,许年为什么要在意呢?那是冯吉的不痛快,不是许年的。许年没有说话,冯吉却也明白没有回避话题的可能了。“想必你是为钱御史前一阵拜访冯年瑜一事来的,如果我猜得没错,姓秦的丫头也是为这件事而来。”冯吉的话语里带着一点嘲意,“很可惜,除了已经死的那两个当事人,没人知道他们当时关着门谈了些什么,不过从钱御史心满意足的样子来看,他并不是空手而归。”
“你认为他得到了什么?”
“他想要的东西。”冯吉并不正面回答许年的问题。顿了一顿,冯吉意味深长地舒了一口气,接着说道:“这里虽然远离京师,但毕竟冯家当年也是那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京城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也还有些个人传信。钱御史暴死天香楼的事冯年瑜和我都已经听说,不过从哪个角度看,这件事和南宫完全扯不上干系,惊动了许公公的大驾倒是很出人意料之外啊!”
“这个需要向你解释吗?”
“不用,当然不用。”冯吉胸有成竹的笑了起来,“让我猜一下:太上皇早已不管朝政,除非是事关玉体圣安的事,是不会把你派出来的。”许年抬起眼皮:“那么你怎么看这件事?”冯吉摇摇头:“我只是个小卒子,没能耐了解什么大事,不过,要我看,这是太上皇多虑了。”“怎见得是多虑?”许年问。冯吉沉呤了片刻,似乎在考虑怎么向许年解释。然后,他慢慢开了口:“太上皇派你查访钱御史,大概是因为钱御史这趟下江南走得神秘,死得又蹊跷,满朝官宦竟没一个知道他身上倒底负着什么使命,那架势,不难猜出要出大事。这件事传到南宫只怕也不是偶然,太上皇有某种顾虑也就不奇怪了。”
许年啜了啜杯中酒,不紧不慢地说:“听你的口气,对整件事的了解并不象是仅仅听人的传言而已。如果真如你说,太上皇有某种顾虑,那么这种顾虑有没有根据呢?”“没有。”冯吉肯定地回答。“为什么?”冯吉的干脆颇出许年意料之外。“冯年瑜能干什么?他在曹州七年,没兵没权,不过是个管着点地方小事的寓公罢了。以他小小的力量,如何去对太上皇不利?何况冯年瑜是太上皇的旧臣,胆子很小,又是个迂人,无论如何是不会做出什么杵逆的事来的。太上皇实在是可以安心休养,许公公也大可不必为此奔波辛苦的。”
“既然是这样无足轻重的人,为什么有人要抄杀他的全家?”许年问,“而且很明显,你的消息渠道并不仅限于京里的传报。”他直盯盯地望着冯吉说道:“你在替某个人做事,替他收拾冯家人。如果冯年瑜不是对太上皇不利的话,那定然是对你的主人不利了。”冯吉脸上挂着矜持的笑意:“让你安心也好,你这么想也无妨。”许年沉默了。冯吉等了一阵,不见他答话,语调慢慢变得强硬起来:“看样子,许公公已经明白了这件事与你们无关,那么就可以安心回京了。反正南宫不管政事,就此打住吧。不客气地说,再往下,也由不得你们管了。”
冯吉的话让许年有一种被鞭子抽的感觉,抽得许年感到刺痛,让他不由得微微颤抖了一下。但是,许年没有反驳的理由,冯吉是对的,如果这整件事只是当今皇上与臣子之间的纠葛,就算是倾朝大事,他这个被抛弃的先皇的内宫臣子又有什么权利去问呢?毕竟太上皇已经不能干政了。
冯吉的脸上有一种胜利者对无可奈何的输家的怜悯,“许年,所以我早说让你走了,这些事,原本就与你无关。”这时,他看见许年眼睛里突然有了一种不同于以前的东西,一种不同于刚刚的那种阴冷的坚定神色。“除了许公公,我还是许年。”许年缓缓地说,“许公公可以不管非南宫的事,但许年可以管朋友的事。”突然,许年眼中放出精光来:“冯吉,你该不会是锦衣卫的人吧?”
冯吉脸色瞬间煞白:“为什么你会这样想?”胜利者的怜悯神情很快转到了许年这边,许年就那样盯着冯吉,不动声色地说道:“我只是猜,你何必反应这样强烈?我这样想是因为除了他们,世上似乎还没有谁会有这样的耐心,指派他的人在几乎没有什么出错可能的地方小官身边潜藏七年。这种事只有锦衣卫才会干,只有他们才会设下如此不计成本的监视网。而且,能够指派得动象你这样的人物。”
冯吉脸上忽然有了一种凄怆的神色:“是不是锦衣卫又有什么区别?我这样的人又算得上什么人物?指派我还需要有什么身份才行吗?”许年确实也有一些诧异,于是索性说了出来:“这的确让人奇怪,当年的卫所指挥冯吉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冯吉的声音里带着苦涩:“有什么奇怪的,当你突然发现活着很不错,而有人能让你继续活着时,那么有什么不能干呢?”
什么东西涌上来梗在了许年的喉间,让他有种窒息的感觉。冯吉会说这样的话?这不象是冯吉的想法。至少不象七年前的冯吉该有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