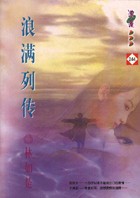浪满列传-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许考不上也说不定,只是先让她考考看。”爸嗫嚅着。
妈忽然说:“阿雄呢?他好一阵子没打电话回来了。”
李宝婷立刻接说:“你别想打阿雄的主意。人家阿雄都娶老婆生小孩了,有自己的家要养,哪有钱供阿满花。”
“我又没有说要找他要钱。”妈有些生气。
李宝婷被妈抢白一句,咕哝几声,说:“反正这没有我的事,我不管。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硬是要宠阿满,舍不得她去工作,到时可别怪我没警告你们。好了,我要走了,我还得回去煮饭。”
我听见开门关门的声响,“砰”地一声,天塌了似,强烈撞击我的心脏。我又在房间坐了一会,才走出去。
妈看到我,皱眉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中午。”我说。
她没再说什么。我看看爸,他也没说什么。
晚饭的时候,爸忽然问说:“什么时候考试?”
“还有两个礼拜。”我回答。
他点点头,同样没再说话,低头喝他的鸦片剂。
妈吃着饭,也不看我,说:“四年要花多少钱!?你就算考上了,我们家也没那个钱让你念书。你爸三不五时没工作,阿顺又不可靠,我看你也别考了。”她绝口不提李宝婷和李正雄。
我沉默一会,然后说:“可是,报名费都缴了。”
“随便你!”妈打断我的话。“你要考就去考,但没钱就是没钱!”
她打开电视,黄金档连续剧演得正热烈。
我一口一口吃着饭,忽然想起不知在哪曾看过或听过的一些话——我们以为繁衍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以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不过是受了基因的控制。所有的胎儿也不过是寄生在母体的客体,吸取宿主的营养借以得生存。
不管什么事,抽掉了感情的因素,就变得丑陋;所谓的事实,也通常让人觉得不是那么愉快。这时我才有点明白,不管是自欺或欺人,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都那么爱说谎。
它使我们的生活容易一些,使我们的人生美丽一点。
第十章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阳明这么说。
不用他说我也知道。但就算立了志,事情也不一定可成。聪明的我,很容易就可以看穿这种现实的吊诡。
靠着陆邦慕给我的笔记和浪平简直形同强迫的辅导,我的英文考了四十八分,数学拿了六十三分,侥幸地挤进北部一间国立大学。
但是……中文系?能于什么?不都天天讲了,还要花四年的时间去读它吗?爸妈很疑惑,我自己也很疑惑。
“念那个能干什么!还不如趁早去找个工作。”妈眉头深锁,并不怎么感到高兴。
爸说:“这个每天都在讲的东西,还要花四年去念啊?怎么会这样?”
我不知该怎么解释。爸妈沉默一会,然后爸开口说:“如果没考上也就算了,但既然都考上了……”他没再继续说下去,只是低下头去。
妈好半天没说话,自顾忙她的事。隔许久才说:“打个电话给宝婷吧。”
爸默默低着头,我也低着头,说不出的难堪。
李宝婷的声音很大,我坐在桌子另一头都可以听到她喊说:“我怎么会有钱!”
妈默不作声地挂掉电话。我看她又拨了一个电话,那头久久没人接,她不得不放弃。
“阿雄好像不在家的样子。”妈说。
她和爸相对坐着。两个人眉额间的皱纹一式的深。爸低声跟妈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然后他说:“我看我还是去找阿坤吧。”阿坤是村子里专门放款借人周转的债主,虽然不致太黑心,但利息也很可观。
妈没说话。爸看看她,便起身出门。
妈叫了我一声。“阿满,过来。”要我跟她去房间。
我站在门边,妈坐在床边,从床柜下摸索出一包破旧的小布袋,深深叹口气说:“就剩这些了。好不容易攒下的一些钱就都被那个何仔拐跑,就剩下这些——”妈小心地打开布袋,又一层布包着。她小心地打开,里头几只金戒指和项炼。
“把这些卖了,加上跟阿坤借的,凑一凑大概够付第一期的拉杂费用。”她停一下,眉头紧皱。“要是叫你别去念,你一定不肯,但家里就只有这些钱,以后你要自己想办法——”我咬着唇,喉头涩涩的。
就这样,高利贷借了,金子卖了,凑出我第一学期的费用,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种流浪。
※※※
那四年简直是恶梦一场,仿佛老是在打工筹钱;也似电影过场的一个桥段,片段的镜头加上配乐,只是一种交代。
毕业后,因为成绩不太好,我连想留校当助教部没那个资格。我先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然后到一家杂志社担任采访记者,也当过代课老师。每个工作我都做不长,老是在换工作,也不停的搬家。赚来的钱除了拨一点给爸妈,全都叫房租和通货膨胀给吃了,简直一贫如洗。
浪平当完兵后在一所私立女中教英文。他跟我一样——从大学开始不停的打工,他兼了很多份家教,钟点费都相当高,赚的钱除了拿回家,还救济我。如果没有他的帮忙,我根本捱不过来。但他的成绩一直相当好,还拿了书卷奖。
不过,他并不喜欢教书,之所以选择这个工作是因为薪水高、稳定,课余还可兼补习工作,另有一份可观的收人。
我们双双住外头,离家很远。他总是选择公寓楼顶加盖的房子栖身,只跟空气为邻。我虽然不像他那般偏执,我得到合乎条件的地方就住,但我从不跟邻居来往。
每次搬家,感觉就好像动物迁徒;看我那样搬来搬去,老是不安定,浪平索性把他住的地方让给我,他自己则在附近找了另外一间公寓。
这一次,我在一家公关公司找到份工作,脱开不了跟人的周旋,我根本不是那个料,没三天我就走人了。我在街上呆了一晚,看了两场电影,夜深人静了,才摸黑回公寓。门口有一堆烟蒂,看样子浪乎来过了。
打开门,地上有一个信封,从门底下塞进来的。浪平写的,里头有一万块。
我拿着钱想了半天,看看时间,将它塞进口袋,抓了外套重新出门。
五分钟的路程,不算太远。我爬上最顶楼,用力敲了几下。
过了一会,浪平才来开门。我听见里头有女人的声音在问“是谁”什么的咕哝着。
“你有朋友在是不?”我说。
大学那几年忙着打工,我不太去关心浪平的社交生活,但我知道他偶尔似仍和薇薇安见面。浪平成为老师后,习性仍然不改,依然一个女友换过一个女友。甚至有学生会大胆的跑来找他,自动献身——我撞到那么一次,后来浪平就把他那住处让给我,搬到这里来,地址电话一概不对校公开,学生查也查不到。有时他学校临时有事通知他,还会搭上我在用的那只电话,更是问东问西的,有点烦。浪平不晓得怎么处理的,总之,现在变得清闲多了。
“没关系,进来吧。”浪平侧身要让我进去。
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了。但我老是无法觉得自在。我摇头,把钱掏出来。“不了。哪。我只是要把这个还给你。”
浪平看也不看它一眼,倚着门,双手交叉在胸前,盯着我,说:“我今天打电话找你,他们说你辞职了。”他的口气平板直叙,用的也不是问号,但很明显的,他的态度就是一种询问,而且等着我的回答。
“嗯。”我说:“那工作我做不来。”
不用我说,他也知道。我想,他应该也知道我做不太长。
“我学校附近那所国中要找一个代课老师,去试试看好吗?”浪平说。“我有个同学就在那所学校,我请他帮你介绍——”
“浪平,是谁啊?”屋子里头的女人在叫,有点娇嗔。
“你朋友在叫你了。”
“不必理她。”浪平的态度十分无所谓,甚至有点冷淡。“就这么决定了,我明天会找他谈,你后天就过去。”
“浪平,我没关系,我会尽快再找个工作,你不必那么麻烦。”我知道他并不喜欢跟别人牵扯。浪平生活放荡,女友交过一个又一个;人际关系虽然处理得不错,但他不和人深交,也不跟别人密切来往。
“你放心,没那么麻烦。”浪平好像很无所谓的样子,表示他可以处理得很好。“你别再找理由,后天去面试。”
“知道了。”浪平的固执和坚持我很清楚,虽然他从没意愿解释他做的任何事。
“哪,这个。”我把钱递还给他。
他没动,反问:“你身上还有多少?”
我皱个眉,比个手指。
“两佰还是两千?”他又问。
我瞪瞪他,说:“两千。但我——”他没让我说完,不发一语地抓起我的手,把那只信封袋更塞在我手上。
“到底是谁啊!浪平。你怎么去那么——”那女人边娇嚷着边走了出来。看见我,说到一半的话咬了回去,大眼睛骨碌地盯着我,揣测着,打量着。
“朋友?”她转个眼彼,看向浪平。
浪平没回答,说:“你可不可以先进去?我们还有事要谈。”
“秘密吗?不能让我知道?”那女人嘟嘟嘴。
“这跟你没关系,你知道那么多干什么。”
我发现浪平的态度有些冷酷,那讲话的口吻、神情实在有些没心肝。他跟这些女人交往,从来也没有把心剖开。
“时间很晚了,我也该走了。”我匆匆开口,随便把钱塞进口袋。
“我送你——”浪平走出来。
“不用了,反正很近。”我看见那女人抗议的表情。
“走吧。”浪平好像没什么在乎的事,跟别人的意愿毫不搭调。
“浪平,”他此刻的女朋友叫嚷起来。“你要去哪!你打算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吗?我不管!你如果就这么出门,我可就要回去了。”语气不无几分不满与威胁。
“好吧,”浪平回头说:“那你就回去,我再打电话给你。”
不再多看那娇俏的女人一眼,转向我说:“我们走吧。”
“浪平!”那女人气急败坏。“什么嘛!浪平!”
我听见她在跺脚,浪平却显得麻木,没有兴趣回头。我实在也没想到他竟会那么说,那么没心肝。浪平对爱情的态度一直就是那么亵读。
“你还是赶快回去吧,不然她真的要走了。”走到巷子口,我忍不住开口。
我实在不喜欢这种感觉,好像制造了什么混局似。
“我明天会打电话给你,别乱跑。”浪平对我的话充耳不闻。
“知道了。”我蹙个眉,对他叮咛小孩似的口气有些不以为然,说:“谢谢你,我是说那些钱。”
他伸出口,像要摸我的头似,还没碰触到,突然又缩了回去。“有什么事尽量来找我,都可以跟我说的。”
他的负担其实己经够重,赚的钱不仅要维持他自己的生活,还要供他两个弟弟念书,还要救济我——但我仍然点头,说:“嗯。谢谢你。”我们认识已经太久,我也只有他可以依赖。“你回去吧,那么近,不必担心。”
但他坚持陪我到住处,等我开了灯锁妥门才回去。
我掏出钱丢在桌上,脱掉外套,累得一古脑扑倒床上,好一会才不情愿地爬起来洗澡。
我其实很想就那样把自己“腌”起来算了,痛快地睡觉,但一整天在外头游荡,搞得蓬头垢面,一身的脏。
哪知才洗到一半,门铃贸然地响了。
我匆匆冲水套上衣服,心里有些预感。开门一看,果然是浪平。
“怎么了?”我问。
他大步跨进来,一直走到客厅。
“借我住一晚。”把手上的钥匙丢到桌上,便往沙发一躺。
我知道我问,他大概也不会说。
浪平“闷”,闷在不解释。
“你这样会感冒。”我把毯子丢给他。
我也不想问,不外乎一些女人任性的灾难。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他已经离开。我发现他钥匙忘在桌上,拨了电话过去却没人接。
我跑去一趟,想赶在他去学校前把钥匙交给他,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干脆自己开门进去。屋内凌乱的景象看得我一呆。
屋里头能砸的东西全被砸了,一地破碎的玻璃片,书柜里的书有一大半被扫到地上。还没得满地是水。窗户破了;床铺被割得乱七八糟;连电话线也被剪掉。
我慢慢巡视屋子一圈,不禁想起那年在速食店里浪平被一个女孩泼了一脸是水的往事。
我叹口气,慢慢收拾那一片狼籍。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才总算收拾干净。破的窗户、被剪断的电话线、被泼湿的书籍,我留着让浪平自己去处理,至于那被割得不能睡人的床垫,我也留着让他去费神。
我决定好好吃顿午餐,在一家安静的餐厅什么也不想地待了一个宁静的下午。
有些幸福是无法视为“太平常”;如果这“不寻常”的宁静是幸福,那就算是了。
午后偶有阵雨,间刮强风。我发现自己的头发有些凌乱,杂又长,突然升起一股冲动,想剪了算。经过一家发型设计店,我想也不想便推门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