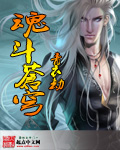碧落苍穹-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董榆生拉开门,说:“娘,我知道了。您先歇着吧!”
母亲又说:“叫梅生早点过来休息,不要耽搁太久”。
董榆生说:“行,娘,梅生这就过去”。
梅生用毛巾擦干了脸上的泪,停止了哭泣,两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说:
“我给你写过绝交书。我用刀子扎过你的心,我还讥笑你当了四年兵都没入上党。这个世上最对不起的人是我呀!不是为了儿子,我绝对进不了你们家这个门,我也无脸向你求情下话。可是到了这般地步,我不求你再也没有可求之人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呀!”
董榆生到了这个时候.也不容他再多想什么。他把烟头扔到地下,用脚踩灭,诚恳地说:
“梅生,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遇到了难处。我怎能见死不救呢?明天早上我开车,咱们一道上法院。行吗?”
梅生眼圈一红,又要流下泪来。她忍了忍,说:“榆生,你的恩德我终归是要报的。这一辈子报不了,就等来世吧!”
“亏你还是党员呢?什么来世不来世的,我们不是从小一块玩大的朋友吗?”
“不,我不配做你的朋友。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抛弃了你。我做了对不起朋友的事。老天爷要报应的。”
“是要报应的.是要报应的。”董榆生腾地站起来,两眼发出怒光,他连忙把头转过去,望着窗外,窗外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到,他还在重复着刚才那句话,“是要报应的。真的,梅生,但不是你。有些人已把坏事做绝了,我相信他们笑不到最后。害害我董榆生一人也算不了什么,但愿不要害了天理犯了天条。”
梅生猛一接触董榆生的目光,禁不住心中战栗了一下。当然她最清楚这其中意味着什么,挫折可以把一个人压扁、压垮、压死,也可以使人振奋、使人坚强。有人给榆生设置了那么多的障碍,他倒下了吗?一个心胸坦荡的人是永远不会被战胜的。这一点恐怕朱桐生到死也不会明白。她好悔呀,当初她把一块到手的金子扔了,反而拣到了一堆垃圾。不想这么多了,生米已经做成饭,做过的事已过去了,何必还要打听哪儿有卖后悔药的。山上的石头滚到沟里,它永远不可能再滚到山上。梅生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惨然一笑,说:
“榆生,时候不早了,你也休息吧!大婶还等着我呢!”
法院没有公开审理,庭外做了调解处理:董榆生支付朱镇宇抚养费每月一百元正,直到年满十八周岁止.共计二万一仟六佰元正。由董榆生一次性付给侯梅生。朱桐生婚前即知侯梅生怀孕之事,而且还设置障碍不让县医院妇产科做手术,因此不构成精神赔偿一节。
朱桐生跑前忙后,以为既败坏了董榆生的名声,又可大捞一把钱。谁知机关算尽,白忙乎了半天,最后一无所获。董榆生的钱也让梅生如数拿了去,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反倒惹了一尻子臊。
三十七、生财之道
钱在世上不知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世上人谁不爱钱?穷人爱钱,富人也爱钱;好人爱钱,坏人也爱钱。钱是魔鬼,它可使穷人变富豪,也可让歹人受拥戴。虽说君子不言钱,有钱的君子总翩翩。古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没有听说,小人爱钱,怎样怎样?大概是手法太多,不便概括,所以就不说。其实细细归纳起来,并不烦琐,无非是坑蒙拐骗偷。至于拦路抢劫、杀人越货者,则不属小人行列,为小人所不屑。此为江洋大盗也,犯杀头之罪,命既不保,要钱何用?古人又云,钱能通神,此话不妥,当纠正。神仙在天上,吃穿不愁,想啥要啥,挥之即来。把钱装在身上,沉甸甸的,反误了腾云驾雾。由此想来,天上的物质早已极大的丰富,不须使用货币交换。谁听说玉皇大帝赶集抢购老白干?
钱是世人的事,与神仙无关。只有两个鼻孔出气的人,才要钱。就是深山修行的老僧老道,时不时地还要下山化些斋饭。据说,粮米不要了,要现金。粮米能背多少?还是现金实惠。一时没有现金,支票也行,寺院里开有账户。不过户头上不叫寺院,叫某某“协会”。“协会”不单要买粮米,还要买纸香,穿戴用具。现时的和尚已非当时的唐三藏可比,穿西装打领带,腰里别着BP机,手里握着手机,寺庙里有电视音响,偶而还可以“0K”几声。西天取经作甚?一个传真发过去,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网上浏览依妹儿了。省却许多路途劳顿不说,还招惹那些妖呀怪的觊觎馋涎。自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尚道人的开销用度也就大了起来,还需诸位善男信女不吝钱财,鼎力赞助。
赞助是自愿掏腰包,或多或少,量力而行。少拿一两块钱,老和尚也绝不会揪住你的衣领,怒目相向。毕竟是出家人,讲究慈悲为怀的。
罚款可就不是你情愿不情愿的事了。吐痰罚款、随地大小便罚款、汽车抛锚罚款、翻墙越沟罚款、银行门口左顾右盼罚款、来人打儿子罚款、吃饭擤鼻涕罚款……,等等、等等。没有人统计过罚款的种类何许多,大约有几十种,成百上千种吧!罚款本是种教育、处罚的方法,如处置妥当,合情合理,被罚人虽不情愿,也无话可说。更进一步讲,不知这笔钱财流入何种渠道?如当真进了国库,被罚人的心里尚平衡些。就算有些人一时疏忽,忘了上缴,顺便给妻子买点化妆品给娃娃买个巧克力,或者打半瓶酒、切二斤肉,也不能就说违犯了党纪国法,至多也就是沾了点小便宜吧!怕就怕积少成多、欲念升级、恶习成瘾,一发难收,到头来被查出,还不知谁罚谁呢?
朱桐生告董榆生,本想诈点钱财,没想到家里出了内奸。老婆和董榆生串通好,沆瀣一气,反倒把他卖了。朱桐生气个半死。后来转念一想,董榆生不是给了两万块钱吗,两万就两万,苍蝇也是肉,先弄到手再说。于是他三天一趟.两天一趟,没事总要往家里跑,软磨硬缠,非跟梅生要这笔钱。梅生心里有数,她早已打定主意,早晚要把这些钱分文不动地退给董榆生。人家董榆生已顶了屎盆子,再让人家破财,这笔人情债一辈子就还不清了。朱桐生不知就里,只是要钱。梅生不依,两个人吵翻了天。楼上稍一响动,楼下就有反应。魏秀枝为人良善,棉花嘴豆腐心,上下左右,谁家有个风吹草动,她都要出面调停,不管结果如何,出发点终归是好的。朱桐生压根就看不起这个矮个子胖婆娘,平时连话都赖得和她说。只是后来郭富荣转业回来当了局长,情形才起了变化。偶而见面点个头,叫声“胖嫂”,魏秀枝已是心满意足、受宠若惊了,因此也甜甜蜜蜜回敬一声“姐夫”,算是持平。
朱桐生最讨厌的就是魏秀枝这张嘴。张家长,李家短,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两口子刚交上火,魏秀枝就闻声敲门进屋。嘴像火烫了似地连声嚷嚷道:
“又怎么了?又是吵又是闹的,别人听见不笑话?猴子你也是,姐夫好不容易来一次,你咋一见面就吵呢?大小你在厂里也是个干部,大局不顾,小局总不能不考虑吧!……”
朱桐生一见这小个子婆娘登堂入室,满肚子火气无处发泄,怒吼一声,气咻咻下楼而去。
按照朱桐生的职务,远不到配备专车的级别。县官不如县管,人家是办公室大主任,县政府大车小车好几十辆,每次出门哪个司机不抢着巴结。今天的值班司机名叫常根福,叫来叫去,就叫成了“肠梗阻”。常根福正在招待所喝着小酒看电视哩,听说主任要连夜赶回去,以为县里出了啥大事,所以二话不说,立马发车就走。
常根福三十来岁,身材高大、长一对牛眼,脸上有好些不平等条约,皮肤漆黑,性如烈火,同事寻常都怯他三分。就是父母妻子在他面前也不敢高声大气。唯有领导那怕是司机班长,他也是言听计从,从不违抗,而且时常半会儿还有些小礼奉送。朱桐生是他所能直接接触到的最高级别干部。因而他对朱主任也最恭敬,朱桐生对他也觉着顺眼。常根福爱好广泛,抽烟、喝酒、下棋、打麻将等等。工资不高、花销又大,常有囊中羞涩、断烟缺火的会儿。此时他就找个借口,寻几张车票、发票,找朱桐生签字报销。一来二去,俩人遂成知已。朱桐生每次聚会,常根福总是不离左右,帮朱主任带杯酒.点个烟,给朋友们斟个茶、倒个水什么的,笑容可掬,十分殷勤。
常根福虽说喝了几杯酒,脑子还十分清醒。他看朱主任精神委顿、气色不正,忙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扔过去,说:
“主任,先抽着。”
朱桐生走得匆忙,香烟忘到家里的茶几上,这阵正像缺了什么呢。也不说话,接过来点上就抽。
一会儿车就要进城了。只见前面黑压压停着一长溜车,路边几个警察,小红旗一举,挡住他们。一位年轻的交警走过来,敷衍了事地敬个礼,说:
“检查。你的执照?”
常根福还未开腔.朱桐生发话了:
“眼睛瞎了,你不看这是谁的车?”
“谁的车都得查!上面有任务。”
也是,朱桐生憋了半天的火,正愁没地方发昵!常根福仗着有人撑腰,来了精神,牛眼一翻,说:
“查个球哇?没看后边坐着朱县长!”
这一招他用过.上次在凉水泉子,就唬住不少乡巴佬。
小警察虽是新来,多少也识几个数,把手一挥,说:“什么猪县长、驴县长?还不如说是省长才好哩!高原县多大,多会冒出个朱县长?”
“你这个驴日的,眼睛长到尻子上去了!”常根福此时不表现表现,也辜负了朱主任平时对他的另眼看待。他推开车门,照着那位小警察当胸就是一拳。年轻警察未曾提防,趔趄几步,仰面跌倒。常根福不依不饶,仍旧骂道:
“你狗日的起来,让你认一下马王爷有几只眼?”
年轻警察被打倒在地.旁边几位警友火了,大家上来,也不问青红皂白,拳脚相向。常根福虽是雄壮高大,但双拳难抵四手,不一会便被打得鼻青脸肿,身上有几处软组织受损。
“下来吧,大‘县长’。别狗娃子骑骆驼,装成高大犬了。”
朱桐生是有身份的人,犯不着和这些不谙世事的愣头青们论高论低。他大模大样地下了车,和常根福一道走进检查站。
“说吧,你们究意是怎么回事?”警察中的一个问道。
“他还是酒后驾驶。你们闻闻满嘴的酒臊气。”挨打的警察说。
“跟你们说没用,叫你们司站长说话。”朱桐生摆摆手,不耐烦的说。
“哟,好大的架口,还找我们站长昵。我问就问不喘?”还是第一个发话的
警察说。
“他还冒充县长呢!”
“蒙谁呀?就球大一个高原县,哪一个县长没见过?”
“给他们罗嗦什么?酒后驾驶、殴打警察、妨碍公务还冒充县长,每人罚款四百,连夜送拘留所关十五天得了。”
说罢,几个就忙忙乎乎开单子。单子开好就等站长签字盖章。一个问:
“站长这会儿怎么样?”
“还高着哪。喝了一下午,一会半会能缓过来吗?”
“那这两位怎么办?”
“先到隔壁房间呆一会。站长醒了再处理。”
这一下可真苦了朱桐生,他一辈子何曾受过此等窝囊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梅生那儿将就一夜,再怎么着总比在这受罪强。房子又潮又冷,只有一把椅子还是三条腿。常根福把椅子靠墙,让朱主任坐好,再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到朱桐生的身上。朱桐生心大,迷迷糊糊,还真睡着了。
朱桐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打赢官司。尽管董榆生咆哮公堂,但是在法官的严厉训斥下,还是老老实实交出一大叠子钱。朱桐生好高兴啊,他想有了这么多钱,这后半辈子的开销就不用发愁了。他在梦中还琢磨着,这不是做梦吧,千万不要做梦……
正在这时,外面门开了,有人喊:
“出来出来,睡的还倒挺舒坦,没做恶梦吧?这个房子可是死过人的。”
朱桐生在心里恨恨地想:你们这伙狗怂别狂,见了你们的头,看你们咋收场?昨天晚上他故意不说清楚,暗中就留着这一手。
司站长名叫司耀先,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左手夹着一支烟。右手拿一支圆珠笔.桌子上一杯酽酽的浓茶正冒着腾腾热气。见朱桐生他们进来,头也不抬,两眼盯着“罚单”,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跑这儿撒野来了!叫什么名字?”
朱桐生也不做声,照直走过去,端起那杯酽茶先啜了几大口。
司耀先恼怒地抬起头来,不看犹可,一看是朱桐生,火烧屁股似地急忙站起来,说:
“啊呀老兄,怎么是你?你跑这儿做啥来了?”
朱桐生一边喝茶一边说:“问我干啥,问你的人呀?看我的司机,也让他们修理好了。你们就是这么做工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