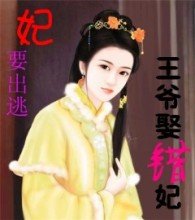不如,我们重新来过-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书生吭哧吭哧地咬了半天,直咬到嘴角白沫横流,磨牙磨得自己心中发毛。他一发狠,决定要祭起自己切金断玉的一对犬齿,将眼前的白布条条撕碎。他掰着姑娘的肩膀将她翻转过来,想从正面入手,免得咬到头发。这一翻正好和姑娘瞧了个对脸,书生看见白布下她的眼睛微微一动,面孔也红了一红。一愣之间,只听到〃嗤〃的一声轻笑,姑娘倏地逃离了书生的掌握,一晃便出了庙门。书生兀自着牙怔在那里,直到雨声再次响起,才醒觉怀中已经空了。
下山以后,书生放弃了打柴这份自由职业,转而去学打草鞋。这不是说草鞋比柴火好卖,实际上,因为连月阴雨,柴价已经翻了一番,草鞋则根本卖不出去。书生之所以要学打草鞋,是因为这是一门手工编织的艺术。而手工编织就是打结。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学会解开一个结,就要先学会怎么打它。三个月后,书生打草鞋的技艺在当地已无人能出其右。他可以用一根绳不间断地打出六双鞋来,当然,每只鞋中间都有一截绳子连着。当地的衙门买了他的鞋去给囚徒们穿,穿上后六人一列走起来整齐划一,让前来巡查的官员们看了啧啧称奇。然后,书生又去了三十里外的渔村,学习编织鱼网的技艺。半年之后,他编出了像筛子一样细密,又能重叠好几层的渔网,将当地的鱼虾捞得一干二净,然后离开了那里。又过了一年,这个渔村因为水产枯竭而被废弃了。这时,书生正在六十里外的州府,为即将来临的新年扎着史上最大的一个中国结。完成之后,这个结有九十九丈高,九十九丈宽,摆在地上有两个人那么厚。城里的人们结伴来看,沿着边缘慢慢地往里走,一不留神就走迷了,再也没能出来。
然后,书生又离开了州府,去了许多别的地方。他学会了十字结、双钱结、团锦结、酢浆草结,又学会了童军结、苦力结、帆工绳头结和水手绳头结,还学会了千张结和海带结。把这一切通通学会之后,他荣归故里,开了一家杂货铺,专卖草鞋、渔网、巫毒娃娃、线绳吊床等手工编织品。当时的风俗,男女恋爱之前,主动之一方需将心爱的手巾或罗帕挽一个同心结,抛在对方经过的路上。假如被捡起来,那这事就成了;假如绕着走过去,那就是没戏;假如看也不看一脚踩了上去,那多半会引发流血事件。而这个同心结呢,当然是打得越难解开越好,否则二人花前月下之际,拿出定情信物来对之起誓道:〃生某某,妾某某,今誓愿永结同心,生生世世,长相厮守,有如此结。〃言罢将手一指,此结不解自开。发生这样的状况,场面难免会有些小小的尴尬。所以青年男女们听说当地有这样一位打结的奇人,纷纷找上门来,掏出各色手巾、罗帕、红缎、黄绫,要求在上边打一个既美观又结实的同心结,拿去丢在帅哥美女们的面前。来的人多了以后,书生便把这作为一个收费项目,每天光是打结赚得钱便足以吃穿度日,干脆连杂货都不卖了。
再后来,又有些恋爱失败的人们哭哭啼啼地找上门来,说当初打的结过于结实,分手后自己无论如何都解不开,又舍不得把一块上好的手帕剪坏,只好拿回书生这边来要求解开。在书生这里解结不收钱,算是一项售后服务,这一点给顾客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些姑娘在解开了结之后立刻又让书生再打一个,然后把手帕丢在他店门口。书生看到了就从窗子里跳出去,绕着门口走一圈,再从另一个窗子里钻进来。于是姑娘只好把手帕捡起来,让书生再解一遍。
有一天,书生的小店里进来了一个人。她穿着一身白色长裙,乌黑的头发直垂到腰上,乃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子,她的眼睛上蒙着一道白布。书生看见了,赶紧迎上前来,扶她坐下,沏上一杯好茶。姑娘指了指眼上的布条,做了一个解开的手势。书生点点头,双手捧起她的脸颊,指尖划过布条,触到了后脑勺上的那个结。
为这一刻,书生已经准备了多年。他默默地调匀呼吸,摒弃了心中的杂念。然后,他的手指脱离了大脑的指挥,像流水一般舞动起来。
十分钟后,姑娘的长发被编成了一个硕大的〃寿〃字,配有蟠桃、仙鹤、祥云等饰纹。等手指终于停下来之后,书生睁开眼睛,看到了自己的作品。那无疑是他完成的同类作品中最精彩的一个,然则,那个结还是在原处,丝毫没有能被解开的迹象。
于是,书生走到姑娘身后,先解开她的寿字发型,再把她所有的头发分成若干股,在头顶上扎起高高的一根发辫来。这样一来,她雪白的脖颈,和脑后的那个结,就清清楚楚地显露了出来。然后,他把她摁倒在桌上,从容不迫地弯下腰去,亮出犬齿,奋力撕咬起来。午后的斜阳从窗口照进来,屋子里半明半暗,沉浸在晕黄的光影之中。偶尔有门口路过的人探头往屋里张望一眼,立刻飞也似的逃走了。
书生全心全意地咬着那个结,直到口水流干,牙齿淌血,嘴也合不拢了。最后,他放弃了,颓然坐倒在桌边。窗口的阳光渐渐暗淡下来,姑娘站起来,整了整衣衫,走出门去。在跨过门槛时,她深深地向后仰起了腰,让头上那个高高的发辫得以安然通过。而书生一直坐在地上,看着门外,看着天色一点点变暗,不知何时又下起雨来。
他就这样在地上坐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书生从梦中醒来,听见窗外稀疏的雨声,恍惚间又回到了多年前的山神庙中。他想:我为什么要解开那个结呢?
这一天,没有一个顾客上门。到了傍晚时分,姑娘又来到了店中。书生请她坐下,沏上了一杯好茶。然后他搬出文房四宝,开始研墨。研得了墨,他取出新浸开的羊毫一管,饱饱地蘸上,细细地掭干,然后提起笔来,在那道解不开的白布上,画了一对眼睛。这是一对笑盈盈的豆荚眼,细细长长,眼神有些过于凝聚。画完后他将笔一抛,大笑着走出门去,从此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书生和狐
By胡叉
从前有一个书生,上山砍柴。当他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时,看到一只纯白色的狐狸,从道旁的灌木丛中蹿出来,朝他看了一眼,然后急匆匆地跑掉了。
书生看到那只狐狸的眼睛也是白色的,带着点灰和透明。
于是书生说:〃噫!好好的一只狐狸,没想到竟然是个瞎子。不如我拿一支毛笔,给它点两个眼珠子上去好了。〃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开始下起雨来。书生抛下砍了一半的树,揣着斧子,急忙忙跑进山神庙躲雨。正当他脱下短衫,哗啦啦拧水的时候,庙门吱呀一响,又进来了一个人。
书生定睛一看,来人一身白色长裙,腰间扎着纯白的丝带,是位身材苗条的姑娘。他心头噗通一跳,赶紧抖开短衫,捂在胸前。再一看,那位姑娘的眼睛上蒙着一道白布。书生叹道:〃噫!好好的一位姑娘,没想到竟然是个……〃还没说完,他心头又是噗通一跳,想起了山路上的那只狐狸。于是他赶紧闭上了嘴,退到角落里蹲了下来。没想到那位姑娘却径直走到他身边,坐下,双手环抱住膝盖。书生偷偷地侧身张望,想看看她身后有没有尾巴,却只看见及腰的长发。他又轻轻地吸了吸鼻子,想闻闻有没有某种以狐冠名的味道,却只闻见一点点雨后白梅那样的香气。
书生想:嗯,也许她不是狐狸变的。可能今天我命中犯白,又犯瞎子。嗯,今天是白瞎的一天,注定一事无成。我不如早点回家睡觉去吧。
正在这时,那位姑娘缓缓地转过头来,说:〃你……猜……猜……我……的……眼……睛……是……什……么……样……的……呃呃呃呃呃呃……〃
他和她对视了几秒钟。接下来,书生的心脏做了一个艰难的抉择,直接影响到了本文的走向。假如它紧紧地缩成一团,然后就此不动,那将产生一个恐怖小短篇儿,以〃三天以后,人们在庙里发现了书生的尸体〃而告终。但是,之前的那两下〃噗通〃让它做好了热身的准备。所以它艰难地、小小地又噗通了一下,为书生的大脑提供了必需的氧分,让大脑得以想道: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什么样的?是巨大的布满血丝的球体?还是涌动着蛆虫的两个黑窟窿?也可能那里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
这些念头让他的心脏接受了又一轮的考验。这颗年轻的心脏,在巨大而不可知的死亡面前,顽强而又勉强地唱出了,可能是最后一句的生命之歌。这首歌是这样唱的:(喂?喂?血管那头的朋友们,听得见吗?接下来要为大家献上的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做)噗……噗噗噗噗……通。
凭着这一下,书生的大脑在彻底空白之前,又获得了一次思考的机会。它稍稍地犹豫了一下,然后想道:是白色的,灰,而且透明……这个念头,赋予了心脏继续跳动下去的勇气。于是大脑也得以继续想道:也许是蓝色的。或者,像蛋清那样,带点黄绿色。也有可能像兔子,是红色的。或者是水塘那样沉甸甸的绿色……
他这样想着,手不知不觉伸了过去,想揭开蒙着姑娘眼睛的那道白布。那位姑娘没料到有此一手,一时间愣住了。书生两个指头捏住白布上沿,想把它提到额头上去。但那白布绑得很紧,提之不动。于是书生又想把它往下扯,但那白布确实绑得很紧,扯之也不动。他换成两只手一起来拉亦是无用。于是书生探手到姑娘脑后,想把绑起来的那个结给解开。结果两手抓来抓去都只有满把的头发,找不到那个结在哪里。书生心中焦燥起来,他似乎听到姑娘在轻声地说:〃嗤……〃
冷静呀,要冷静呀!书生定了定神,收回手来捧着姑娘两颊,指尖贴在布条上,缓缓地朝脑后包抄过去。那个结就在后脑勺的正中位置上。书生很高兴地想把它解开,然则它又坚硬又光滑,简直无从下手。书生耐着性子,专心致志地解着,姑娘也很配合地坐在那里,任自己的脖颈被环在书生的双手之间。约莫过了一炷香的时间,书生终于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是在拨弄自己的几个指头,而那个结安安稳稳地待在一旁,完全没有被打扰到。
于是,书生怒了。他将姑娘的脑袋拽了过来,拨开头发,与那个结开始了面对面的PK。他发现这个结外表上看来普普通通,就是我们常常会用在海带和千张上的那一种。但每当试图解开它的时候,手却总是从上面滑开,即使有几次牢牢抓住并且使上了全部的力气,也不能使它稍稍松动一下。书生与之搏斗了一番,败下阵来。然后,他采取了当我们用手无法解开一个结的时候,通常会采用的那种手段。
他将姑娘的脑袋牢牢地摁在自己膝盖上,开始尝试着用牙咬开那个结。这一切,发生得都符合逻辑。但是当我们把时空的联系切断,只撷取这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在破败的山神庙中,一位披着湿布衫的青年男子蹲坐在地上,一位身着白衣的年轻女子俯在他的膝头。男子拨开她一头如云的长发,对着她后脑勺大力撕咬,不时发出咯啦咯啦的磨牙声。与此同时,雨在窗外淅沥沥地下着,整座青山被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这正是丧尸系作品中难得一见的祥和场景。
书生吭哧吭哧地咬了半天,直咬到嘴角白沫横流,磨牙磨得自己心中发毛。他一发狠,决定要祭起自己切金断玉的一对犬齿,将眼前的白布条条撕碎。他掰着姑娘的肩膀将她翻转过来,想从正面入手,免得咬到头发。这一翻正好和姑娘瞧了个对脸,书生看见白布下她的眼睛微微一动,面孔也红了一红。一愣之间,只听到〃嗤〃的一声轻笑,姑娘倏地逃离了书生的掌握,一晃便出了庙门。书生兀自着牙怔在那里,直到雨声再次响起,才醒觉怀中已经空了。
下山以后,书生放弃了打柴这份自由职业,转而去学打草鞋。这不是说草鞋比柴火好卖,实际上,因为连月阴雨,柴价已经翻了一番,草鞋则根本卖不出去。书生之所以要学打草鞋,是因为这是一门手工编织的艺术。而手工编织就是打结。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学会解开一个结,就要先学会怎么打它。三个月后,书生打草鞋的技艺在当地已无人能出其右。他可以用一根绳不间断地打出六双鞋来,当然,每只鞋中间都有一截绳子连着。当地的衙门买了他的鞋去给囚徒们穿,穿上后六人一列走起来整齐划一,让前来巡查的官员们看了啧啧称奇。然后,书生又去了三十里外的渔村,学习编织鱼网的技艺。半年之后,他编出了像筛子一样细密,又能重叠好几层的渔网,将当地的鱼虾捞得一干二净,然后离开了那里。又过了一年,这个渔村因为水产枯竭而被废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