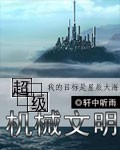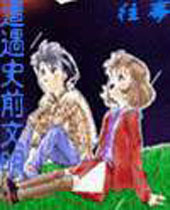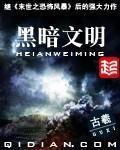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看的txt电子书
人的标志。此外,当有德性的人称他们自己为罪人时,他们并没有错,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能满足的诱惑——因为众所周知,诱惑只是在频频受挫后才会增强,而对它们的偶尔满足却会使它们至少是暂时地被削弱。道德学领域充满了问题,它呈现给我们另一个事实:即恶运——外部挫折——大大增强了超自我中良心的力量。当一个人一切都顺利时,他的良心便是宽容的,并且让自我做各种事情;但是当恶运降临到他头上时,他就检查他的灵魂,承认他的罪过,提高它的良心的要求,强制自己禁欲并且用苦行来惩罚自己。
整个人类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在这样做。然而,这一点很容易地用原初的、早期阶段的良心来解释。
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良心进入超自我阶段后,这一早期的良心并没有被放弃,而是始终和超自我在一起,并作为它的后盾。命运被认为是力量的替代者。如果一个人不走运,那就意味着他不再为这一最高力量所爱;并且由于受到这种失去爱的威胁,他就会再一次服从于他的超自我,即父母的代表——在他走运时他总是忽视这一代表。在严格的宗教意义上,命运被看作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在这里,上述情况更显而易见。以色列人相信他们自己是上帝的宠儿,而且当伟大的天父将一场接一场的不幸降到他们头上时,他们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于天父与他们关系的信念,或者怀疑上帝的威力和正义。他们用先知作为天父的代表,向先知宣布他们所犯的罪过。由于他们的内疚感,他们创造了具有教士的宗教,它包含极其严格的训诫①。
原始人的所做所为则极为不同。如果他遇到了不幸,他不是责备自己,而是责备他的物神(fetish)显然没有尽到责任,并且他不会自罚而是鞭打他的物神。
因而,我们懂得了内疚感的两个来源:一个是起源于对于某个权威的恐惧,另一个是后来起源于对超自我的恐惧。
第一个坚持要克制自己的本能的满足;第二个也是这样做,迫切要求进行惩罚,因为被禁止的欲望的继续存在是瞒不过超自我的。我们还知道了超自我的严厉性——良心的要求——是怎样被理解的。它只不过是外部权威的严厉性的延续,它继承了后者而且部分地取代了后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本能的克制是在怎样的关系中坚持内疚感的。最初,对本能的克制是对外部权威的恐惧的结果:一个人为了不丧失外部权威的爱便放弃了他的满足。
如果一个人实现了这样的克制,他就可以说是服从于外部权威了,并且也不再有内疚感了。
但是对于超自我的恐惧,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对本能的克制是不够的,因为本能的欲念依然存在并且不能瞒过超自我。
因此,尽管做了克制,内疚感还会发生的。这就是超自我的建立过程中,或者说是在良心的构成中,造成了一个很不经济的条件。对本能的克制再也没有全然自由的结果了;虔诚的节欲也不再保证会得到爱的奖赏了。外部不幸的威胁——失去爱和外部权威的惩罚——已经换成了永久的内心的不幸
①〔对于以色列人与其上帝关系的更为广泛的解释,可在弗洛伊德的《摩西和一神教》一书中找到。〕
和加剧了的内疚感。
这些相互关系既极其复杂又极其重要,因此,我不怕重复,将再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这些关系发生的时间顺序如下所述。首先,由于恐惧外部权威的进攻而产生了对本能的克制(这当然就是对失去爱的恐惧,因为爱可以使人们免除这种惩罚性的进攻)。
然后是内部权威的确立和由于对它的恐惧,即对良心的恐惧而产生的对本能的抑制①。
在第二种情况下,做坏事的企图和做坏事的行为是相当的,因此就有了内疚感和对惩罚的需要。良心的进攻性接替了外部权威的进攻性。到目前为止,事情无疑已经弄清楚了;但是这种接替在什么地方加强了不幸(从外部强加的、抑制的)影响(见第108—109页),以及使最善良、最温顺的人们形成了良心的惊人严厉性呢(见第108页)?
我们对良心的这两种特性已作过解释,但是我们大概仍然觉得这些解释并未触到问题的根本实质,仍然还有一些没有解释的问题。最后,在这里出现了一种观念,它完全属于精神分析领域,它是与人们的一般思维方式不同的。这种观念可以使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研究的题材好像总是混乱和晦涩的。因为它告诉我们良心(说得更准确些,是后来成为良心的焦虑)实际上是最初对本能实行克制的原因,但是以后这种关系就颠倒了。每一种对本能的抑制现在都成为良心的一个有力的源泉,并且每一种新的抑制都增强了后者的严厉性和不宽容性。如果我们
①〔“Gewisensangst(内心谴责)”,在《抑制、症状和焦虑》(标准版,第20卷,第128页)一书的第七章编者注释中可以找到对该术语的解释。〕
能把这一说法与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良心起源的历史较好地统一起来,我们就要维护下面的这种似非而是的论述,即良心是克制本能的结果,或者说对本能的抑制(从外部强加我们的)创造了良心,然后良心又要求进一步抑制本能。
这一论述和以前关于良心起源的说法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并不太大,而且我们发现了进一步减小这一矛盾的方法。为了便于阐述,我们把进攻的本能作为例子,并且设想这里所谈到的抑制总是指对进攻性的抑制(这当然只是作为暂时性的假想)。于是,抑制本能对良心所产生的作用便是:主体停止予以满足的进攻性的每一部分都被超自我所接管,并且加强了后者(对自我)的进攻性。这一观点与良心最初的进攻性是外部权威的严厉性的延续,因而与抑制无关的观点不一致。但是,如果我们为超自我进攻性的这一最初部分假设一个不同的起源,这种差异就不复存在了。不管外部权威要求儿童放弃的是哪一种本能,它都使儿童不能实现其最初的、但却是最重要的各种满足,所以在儿童中一定会形成对外部权威的相当程度的进攻性;但是他必须放弃满足他的报复性的进攻性。借助众所周知的种种机制,他找到了逃出这一困境的途径。
利用自居作用,他把不可攻破的外部权威变为己有。
权威现已变成了他的超自我,并且具备了一个孩子原本要用来反对它的所有进攻性。儿童的自我必须满足于扮演倒霉的权威即父亲的角色,因为这样一来,父亲的地位就降低了。
在这里,事情的真实情形常常是颠倒的:“如果我是父亲,你是孩子,我将会对你更坏。”
超自我和自我之间的关系是尚未分化的自我和外在对象间的真实关系经过愿望变形后的再现。
这种情况也是具有典型性的。但是根本的区别则是超自我最初的严厉性不代表、或者说不完全代表一个人从对象那里所体验到的或者归之于对象的严厉性;它毋宁说是代表一个人自身对外部对象的进攻性。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断言,良心一开始是通过对进攻性冲动的压抑产生的,后来则由于进一步的同类压抑而得到加强。
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是对的呢?先提出的那种观点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似乎是无懈可击的;而新提出的这种观点则以上述令人满意的方式圆满地完成了这门理论。很显然,同时也是根据直接观察的事实来看,这二者都应当肯定。它们相互并不矛盾,甚至在某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因为儿童的报复的进攻性部分地是由他所预料的来自父亲的惩罚的进攻性的程度所决定的。然而经验表明,儿童所形成的超自我的严厉性绝不是和他所受到的待遇的严厉性相对应的①。前者的严厉性似乎独立于后者的严厉性。一个在宽容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可能会有非常严厉的良心。但是夸大这种独立性也是错误的;我们不难相信,养育的严厉性也会对孩子的超自我的形成发生强大的影响。这就等于说,在超自我的形成和良心的出现过程中,天生的气质的因素和来自现实环境的影响是联合起作用的。这根本谈不上令人吃惊;相反,它是所有这
①正如默雷埃。克雷和其他英国作家所强调的那样。
些过程的一个普遍的原因条件①。
也可以断言,当一个孩子用极其强烈的进攻性和相应的严厉的超自我来对他的最初的本能挫折做出反应时,他是在模仿种系发展史中的模式,并且将超出被普遍认可的反应;因为史前期的父亲无疑是严酷的,并且大部分进攻性可能应归于他。因此,如果我们从个体的发展转移到种系的发展,就会看到关于良心的起源的两种理论间的差异进一步缩小了。
另一方面,一个新的重要的差异就会在这两个发展过程中出现。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设想,就是人类的内疚感是从俄底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中萌生的,并且在弟兄们联合起杀死父亲的时就存在了②。
在那种情况下,进攻的行为不是被压抑而是被实施,但正是对这同一种进攻性行为的压抑,应被认为是儿童内疚感的源泉。在这点上,我不会对下述情况感到吃惊,譬如读者气愤地喊道:“那么一个人是否杀死自己的父亲就无关紧要了——他在两种情况下都会有内疚感。我们在这儿可以提出几点疑问,或者内疚感并非产生于对进攻
①关于两种主要导致儿童患病的养育方法——过度严厉和过度娇宠——弗兰兹。亚历山大(FranzAlexander)在他的《对总体人格的精神分析》(ThePsyAchoanalysisofthetotalPersonality,1927)——关系到艾卡豪恩(Aichorn)对少年犯罪的研究〔《任性的青年》〕——中作了准确的评价。“过度宽容和溺爱的父亲”是孩子形成过分严厉的超自我的原因。因为在他们得到爱的影响下,他们没有发泄他们进攻性的方法,只有把它转入内部。少年犯在没有爱的情况下长大,他们缺乏自我和超自我间的紧张状态,他们的整个进攻性只能向外部。所以除了那些可以认为是存在的气质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说严厉的良心起源于两个因素的联合作用:本能的挫折,它释放了进攻性;以及被爱的经验,它使进攻性转向内部并且把它交给了超自我。
()免费TXT小说下载
②〔《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143页。〕
性的压抑;或者杀父的故事是杜撰的,原始人的孩子与今天的孩子杀父的次数一样多。此外,如果这不是一个杜撰的故事,而是一段可能存在的历史,那么它将是每个人都希望发生的并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一个人感到内疚是因为他确实干了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事情。而关于这件毕竟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精神分析却没作任何解释。“
读者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将弥补这一遗漏。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当一个人做错一件事,并且因为这件事而有了内疚感时,这种情感应该叫做悔恨(remorse)更为合适。它只是与已经做过的行为有关,而且它的前提当然是良心——感到内疚的准备状态——已经在这一行为发生之前就存在了。因此,这种悔恨永远不会帮助我们发现良心和一般的内疚感的起源。
在这些日常情况下发生的事情通常是:本能的需要不顾良心的反对而获得了实现满足的力量,因为良心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由于被满足,本能需要就自然减弱,于是以前的力量平衡重新恢复。因而,精神分析是有理由在现在的探讨中把由悔恨产生的内疚感的情况排除在外的,不管这种情况出现得多么频繁,也不管它们实际上的重要性有多大。
但是,如果把人类的内疚感上溯到杀死原始时代的父亲,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悔恨的情况。
我们应当假设(在那时候)良心和内疚感,像我们已经假设的那样,在杀父之前就存在了吗?如果不应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悔恨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将会向我们阐明内疚感的秘密,并且最终解决我们的困难。我相信这是能够做到的。这种悔恨是人对于父亲的感情的矛盾心理的结果。
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