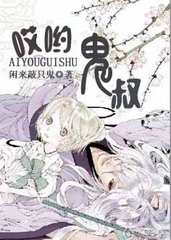别说我神经-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加紧了对我的看管,她常说一句,三儿,别理那些兔崽子,过来,我给你讲你姥爷、姥姥的故事让你静静心。我骂骂咧咧地甩开那帮孩子,他们依旧在背后雀跃着,声音放肆得让我联想到了我的童年,嘴巴忍不住送上一句:这帮小人渣。
我姥爷的英雄救美成为当地三四户人家竞相传颂的美谈,随着事件的数次转口,事实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他们说,姥爷听到一声呼救,踏着一块河边的石头飞跃过去,一把拽住我姥姥的手,及时挽救了一个妙龄少女的生命。而事实的一个微小差别在于,我姥爷当时脚底一滑,拽着我姥姥的手一起掉进河里。姥爷还算识水性,扑通几个猛子就钻了上来,这才发现姥姥不见了。他很着急,就在原地大喊:来人呐,救人呐,有人掉河里了。大概因为千里传音的功力不够,没有一个人闻讯赶来。带着失望的心情,我姥爷转身欲走,他想还是回去找几个长工过来打捞尸体吧。可再回头一看,发现我姥姥已爬上来了,正在大口大口地吐着吞下去的河水。我妈说着还笑着,她显然不会造谣中伤她的老爸,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一开始,我姥姥对我姥爷肯定是没有太多的好印象。
我姥姥当时跟姥爷素不相识,她明白姥爷尽了最大力量,所幸河水不是很深,转了几个圈,喝了几桶水就漂了上来,大家风范的她临走不忘向我姥爷道谢。我姥爷很不愿意听到她说谢谢,连忙回答,应该的,应该的。
姥爷后来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在河边散步,只是过程不浪漫,他独自一人在河边逡巡,不带他的元配,婚姻的轨道就这么开始偏离。我姥爷的解释是,对不住那位姑娘,一定找到她,对她有所帮助,尽自己所能之事。
这是男人的借口,六十年前男人亦如此,如今,男人把那样的一场经历定性为邂逅,姥爷和姥姥的邂逅是美丽的爱情的开始,也是幸福的婚姻的结束。
姥爷在姥姥失足掉下的河边等了好几天,他在期待一个曾经让他置生死于不顾的溺水的美丽姑娘的出现。我姥爷可真傻,他痴情于此,乐此不疲,每天一大早就到了那条河边,举目望去,不见一个鬼影。他低头走在曾经失足的地方,那是一块圆滑的小石头,他蹲下去抚摸着它,像是抚摸一瓣柔软的Ru房,摸呀摸,辅以天马行空的想像,姥爷竟然面色红润,呼吸急促起来,全身似有万千个蚯蚓般爬行,随之“哎呀”一声,姥爷全身颤抖起来,这种感受只有新婚之夜揭开新娘面纱时才有。万簌俱寂啊,他停下手,眺望前方,神态像看一帮歹徒群殴般专注。
我姥姥是撑着一把油脂伞走过来的,她彳亍着,张望着,看得出来,她有种叹息般的眼神,身子一歪三扭地向姥爷走过来。四目相对,霎时,天地定格,时间静止,姥爷缓缓站起来,抬腿向姥姥走去,口中喃喃自语:美丽的姑娘啊,你终于出现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还算不错,一日三餐总会有鸡鸭鱼肉蛋什么的,菜好,胃口就好,吃饭特别的香。老毛病几乎被人遗忘,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鸡的问题,农村那地方野鸡特多,但现在品种濒危,再不控制一下我的肚皮,我怕它们会灭种;比如肉的问题,吃了不少肉,别的地方哪也不长,尽朝我的脸上长,我妈说我一脸横肉,我还不信,对着镜子一照,我的腮帮子从内圆弧变为外圆弧;再比如蛋的问题,毛豆炒鸡蛋吃得我每天肚子跟怀胎五个月似的,常此以往,我担心会被毛豆的体形同化。这个时候,我妈说,你该去看一看杨阿姨了。
我不能再装孬了,杨阿姨我其实是认识的,她是养大了小花,给我碗里夹过很多菜,非要我娶小花的那个。据我妈讲,杨阿姨现在孤苦伶仃,杨叔叔和小花相继离去,剩下她一个人天天对着墙壁发呆,有时一坐就一整天,熟悉她的人知道她承受了丧夫丧女的巨痛,不熟悉她的人以为她神经病,我得拎只鸡去看望看望她,神经病这毛病吃鸡蛮管用。
杨阿姨正歪着头想啥心事,看到我进来,她立刻向我扑过来。我赶紧扎稳马步,看那阵势,杨阿姨冲过来的力度有好几百牛顿。另一方面我也很感动,毕竟有母子般的亲情,见到我,她失控,向我表达她感情脆弱的一面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一大把年纪了,若伏在我身上嘤嘤而泣,我也不会感到意外——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杨阿姨猛冲过来,伸手敏捷地接过我手中的鸡,啧啧说道,三儿啊,看你客气的,来我家还带啥东西,都是家里人,以后再也不要带鸡了……我说,好,好,下次带只鸭来。杨阿姨又说,不用不用,家里鸡都吃不完哩——要带就带鸡蛋吧,家里都是老公鸡,生不出来蛋。
据此,我认定,杨阿姨脑筋正常,既能分辨公鸡与母鸡的特征功能,也能对比出实用的价值,选择最受益的东西。幸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的成本价值为零——那只鸡是野鸡,我窜到竹林里用弹弓将它射晕裹在包里转移地点,因此,杨阿姨很是喜欢地告诉我,三儿啊,你可真细心,逮了只鸡还把它给杀了,这些活儿是该我干的。
因此,我又不太相信自己的判断,杨阿姨到底成为了哲学家还是精神错乱的平凡村妇。但她的记忆应该是超人级别,要比我胜出很多倍,她口口念叨的小花和我的故事跟她们说的一字不差。我又经历了一次故事的熏陶,耳朵里长出老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是,天生多愁善感的我已经被故事里的人和事所感动。这种感情的滋生不知道是好是坏,对于现实生活来说,我还是觉得先前不为故事所动的冷酷更容易找到边缘的快乐,因为,听杨阿姨讲那过去的事,我已经泪水涟涟,心情相当糟糕,就想嚎啕大哭,心里不停地呼喊:李雪啊,你在哪里?
李雪成为我重点回忆的对象不是因为她的美丽动人,故事里的李雪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些人说她非常聪明,长得忒俊;有些人说她爱慕虚荣,过于现实;而我关心的问题是,她有多能耐,竟然视我的好感不存在,毅然扑到张平的怀里。那个家伙有点钱也是事实,但外表畸形也无法反驳,难道钱比我的相貌堂堂还重要?把钞票看得如此重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苦苦思索,是我与这个世界有了隔阂还是李雪脑子有问题。
有这么些个问题需要解答,一天的时间容易打发得多,犯神经的次数明显又降低,我俨然成为一名准哲学家,不再有吃饭发呆的表现,也没有犯遇到事情慌乱失色大喊人渣的老毛病。我像个乖宝宝一样安静,从不乱跑,有水喝水,有饭吃饭,当然,我的杰出表现在于,不随便尿床,不会随地打滚。
我妈把我当正常人对待,放心大胆地让我去数里之外的地方走亲戚,她不怕我迷路走失,也不怕我精神错乱失手伤人。看情形,我不再属于非正常人类,我有了自由和主张,我想干嘛就干嘛,我跟猪聊天,喂它们吃最棒的猪食,我妈伸出大拇指表扬我,说做得好,养肥了杀掉它们吃肉;我跟鸡说话,逗引公鸡和母鸡谈恋爱,我妈说,好,开始恢复人性了。我“嗯”了一声,表示我妈说得对,我希望它们早日生小鸡,然后杀掉它们吃肉。我也认为从逻辑上或者从日常生活里看我正在逐渐痊愈,很长时间没尝过意识混乱的滋味。那天我去大舅家串门,回来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是蒋小红。她手里拎了很多吃的东西,朝我笑个不停,我忍住上前接过东西的冲动,以良好的姿势对她还以笑容。其实内心里我开心过度了,这么多天在六安,见过各种形形色色的女人,但没有像蒋小红那样让我产生愉悦感的女人。无论环境还是人都让我有了阶段性的快乐,因此我一直循规蹈矩,没有什么过头的举动。但接下去的一幕改变了多日以来的平静状态,蒋小红没有扑过来,这一点我有些意外了。在医院里,虽然我常常向她身上扑去,但来到六安,也该轮到她忘情地与我拥抱了。我甚至怀疑在精神病医院呆久了,蒋小红已经被同化,思路混乱,不认识我无计了;或者感情呆滞不向任何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再者她反应迟钝,在我抛给她数个媚眼后,她依然理解不了男女之间的表达方式。这也就算了,惊人的一幕无情地发生了,一个高大的男子从蒋小红背后站起来,有篮球运动员的身架,坦白地说,相貌还是不错的,虽然仅次于我,但在这个地方也是数得着的角色,他突然也朝我笑了笑,嘴巴像个无底洞,神情跟傻子似的,我猜测他一定是蒋小红从医院带回来照顾的病人。
我对帅哥肯定有排斥反应,那小子刚一露头我就浑身不舒服,继而就有呕吐的冲动,也有下泄的欲望,脑袋嗡嗡一片,鼻子微微发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一个男病人跟蒋小红有如此亲密的近距离接触。和她寸步不离形影相随的应该是我哦,早已习惯了蒋小红的说话方式,熟悉她的笑容,依赖她说的故事。现在我逃到乡下养病,她就有了新伙伴,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像一个恶毒妇女狠心丢下她的孩子,然后态度决然地说BYE BYE,置孩子的哭泣于不顾,撒尿拉屎也不管。这就叫无情的抛弃,蒋小红现在就是这样对我的。
我说,小红,你怎么把病人带这来了?
他不是病人,无计。蒋小红说,她的态度显得很认真,我的眼睛很惊恐,不相信她会拐骗别人,于是善意地提醒她,不能这样啊,小红,人家有病你也不能不管不问,抛弃人家不是一个好护士的行径,把他卖到这鸟不生蛋的地方更不是人干的事,小红,快送人回去,要不,我找公安局的送他回家。
无计,你病还没好么,说了他不是病人,他其实——蒋小红脸一红,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说,小红,你就承认吧,他其实是自己跟踪来的,对么,我不怪你。
不是的,无计,你误会了,不要再乱猜乱想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少想多吃,那样对脑子恢复才有帮助。他其实是我男朋友,这次来就是想让你们认识认识的……
蒋小红说中国话怎么如此清晰流畅,非要让我一字不差地听到耳朵里才能达到她伤害我的快感么?顿时,我脑袋里所有图像消失,鼻子颤抖不停,眼前有五六颗金星跳跃,我确实被这番话击中了,男朋友啊,什么概念?是想拉小红的手就拉她的手,想摸她的奶就摸她的奶,想亲她哪就亲哪,这是一个可以明正言顺占一个女孩子便宜的角色。气恨的是,这个角色被别人捷足先登,一个|乳臭未干、长相崎岖的小白脸,他夺去了我记忆里篇幅最多的一段,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想着想着,我的血压就陡增上来,眼前一黑,匍然倒地,在这一刹那,我快速伸出胳膊垫住后脑勺,水泥地儿硬得很,再被摔成植物人,我连蒋小红也记不住了。
倒地后,我双目紧闭,嘴角漫出几滴白沫,口中控制不住地叫,天啊,地啊,小花啊,你在哪里啊?蒋小红立刻奔过来,扶住我的头,无比悲痛地说,你又怎么了,无计,老毛病又犯了么,谁刺激你了啊,你醒醒,说两句话……
她晃着我的脑袋,我的头本来没感觉,被她摇着就痛了起来,我困难地睁开眼,扯开笑容,淡淡地说道,你……我没事,刚才太激动,现在清醒了。那小白脸也凑过来对着我问,怎么了,怎么了。我甫一见到他,头便向一边歪倒,语无伦次呢喃着,小花啊小花,你在哪,我要来找你……这一招很灵,我耳朵里听到蒋小红对他说,你先出去。我很快又睁开眼,缓缓地说,没事,刚才受了刺激,现在清醒了……
我妈见这阵势,慌张得不得了,手足无措,对我又喊又叫,看我没什么反应,她眼睛一转,灵机一动道,三儿啊,我来跟你讲你姥姥的故事,你一定要醒过来啊……
姥爷不是个花花公子,但绝对有着跟我一样多情善感的秉性,还是个想像力丰富的知识分子,他为了讨好一见钟情的姥姥,用尽了各种手段,借以俘获姥姥的芳心。姥姥坚守阵地的决心很容易被突破,究其原因,依当时来看,我姥爷花花肠子特多,现在来看他只是学问多些,知识面广些。姥姥当时习惯说一句,讨厌,你真讨厌。骨子里谁都知道女人越这么说心里越喜欢,不是有哲人说过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早晨空气很好,行人少,野狗多。姥爷从家里带了两根煮熟的玉米棒子,一小袋热腾腾的豆浆,按部就班地来到失足过的池塘边。姥姥会很准时地提着一篮子衣服过来,身子被篮子压得沉沉的,姥爷“哎哟”一声赶紧跑上去接下篮子,姥姥顿时脸颊一片飞红,努着嘴不好意思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