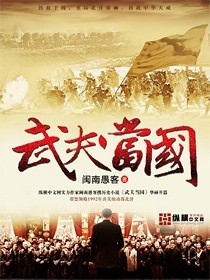袁氏当国-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袁世凯曾说过他大儿子是“残废”,二儿子是“假名士”,三儿子是“土匪”。他如果做皇帝,实在传位无人云云。这话似乎颇具诚意,不但使冯国璋信以为真;连当时驻华的美国使领馆也信以为真。他们竟据之报向华府,说袁总统“不会恢复帝制”。上章曾略有交代。我国古人说,知子莫若父。其实反之亦然。他那个“残废”的大儿子袁克定,就不把老爸的话当真。他知道他老爸迟早还是会做皇帝的。另据他最宠爱的三女儿叔桢(自号静雪)晚年的回忆(参阅本刊三三八期袁静雪《袁世凯的家庭与妻妾子女》),袁氏早知冯之来谒,是向他唱衰的,所以说出上述语言,来把冯“封嘴”的。冯刚辞去,袁即气冲冲地上楼向家属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云云。此事克定岂有不知之理?所以克定这时就雄心勃勃,千方百计,促使老头子跳火坑,改总统为皇帝,庶几十年八年之后,他也可以君临天下。
袁克定在当时国人眼光里,虽是个大草包,可是袁世凯心里,却不是这么想啊。后来袁氏死了,继起当权的黎元洪和段祺瑞,曾把当年袁大总统所封存的金盒子(所谓“金匮石室”)打开了,看看袁当年所内定三位接班人究竟是谁?启封一看,原来是:黎元洪、袁克定,和徐世昌。克定居然是第二名(其实是第一名,但是根据约法,黎毕竟是饶汉祥这个“巴黎人”笔下的“储贰”不得不暂列为第一也。有关黎元洪和他的秘书的故事,迨老黎当总统时再详叙之),足见袁皇帝对这位“太子”的看重了。据说在他从“皇帝”退位之后,还想回头当总统时,才把克定之名,改为段祺瑞的。(故事见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页三四一)
袁克定当然深知乃父思想的底子。针对袁家无人活过六十岁的老传统,克定便直接或间接的,不断的向老头子明言和暗示,这一不祥的家族命运,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另外他更制造无数中国传统帝王,最善于欺人自欺的所谓“祥瑞”,所谓“显圣”等等以突破迷信老人的心防,使他深信“天意”。例如此时湖北某地发现“龙骨”,长数丈。上书者言之凿凿,事实上,或许就是一种恐龙遗骨,是实有其事,使当时中国的第一大阿Q,不得不信。还有更荒唐的真龙显圣的笑话,说某次袁氏午睡方醒,服务生小童以总统最心爱的玉杯进茶,竟失手把玉杯摔得粉碎,说是在床上看到一条“五爪金龙”,惊恐之下,才摔掉玉杯的……,这些荒唐故事,都是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得自“内廷”的消息。据说袁在表面上斥为迷信,不许外传,而内心暗喜云云。这种事或是出自小服务生的创作天才,或许是出自“东宫太子”的巧妙设计,但都是阿Q心防最弱之时,最能接受的莫大安慰。这些都是当时北京城内盛传,而有相当真实性的小道消息。朋友,不要小看这些封神鬼话,它在适当的关口,那些原在天堂地狱之间徘徊的政客,何择何从,往往就会因它而决定在一念之间,袁世凯和汪精卫二人,在历史上对天堂地狱的选择,都是最具体的例子。他二人不但无情的毁灭了自己,也几乎把我们全民族的命运带到毁灭的边缘,言之可叹。
袁克定那时“欺父误国”的行为,最不可恕的还是他伪造《顺天时报》,来欺骗老头子和阖家上下,骗说日本人也赞成袁总统做皇帝。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八国联军(一九○一)之后,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一贯是代表日本政府讲话的。袁世凯因对日本的态度最敏感,所以每天都读顺天时报。袁在中国政坛上一直都被看成“英美派”;日本政府一向也对他虎视眈眈。但是二十一条之后,袁自觉日本已暂餍所欲,不会反对他做皇帝了。这原是他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克定在此关口,乃助其美梦成真;每天都印了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来向他行骗。报内消息,不用说都是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的,这一伪报,对袁氏决心称帝,实在是有其关键性之影响的。后来这伪报被袁克文和其胞妹叔桢在无意中发现了,他们兄妹乃向老头子告密,才东窗事发,“皇帝”为之大怒,竟至将“太子”罚跪,用皮鞭抽打,并大骂其“欺父误国”,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夫复何言。(见上引袁静雪文。)
【莫到琼楼最上层】
可是他那位“假名士”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自始至终都是个反对派,他曾赋诗暗讽老爹,千万不可做皇帝。易经之首卦不云乎,“九五之尊”已到顶点,不即时煞车,而要继续上冲,冲到“九六”,就要“亢龙有悔”,甚或追悔莫及了。
民国以来,写政治诗的诗人,而有诗可传世的,真不下几十百人。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士大夫文学。陈寅恪教授晚年就写了十多首藏头不见尾的,在民国诗坛上有极高度文学价值的讽政诗。这种屈原式的灵感,是八十年来中国新诗界,至今还无法企及的高层文学。也是一般目前新诗人的文学涵养,所无法欣赏的“文字游戏”。但它却是绝对没有死掉的传统文学里,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不论新诗人们如何的诅咒和漠视,它还是老而未死的,中国文学里的一种极其崇高的表达形式,胡适所谓“要下几十年的功夫”是也(胡氏亲口告诉笔者的)。
陈寅恪的讽政诗,也曾使我的两位杰出的老乡——余英时和汪荣祖两教授,打了好几年的官司……。余说他怀念国府,汪说他只是厌烦老共,却并不怀念国民党……。吾人旁观者不清,究竟不知道陈公这位瞎和尚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不论怎样,这才是第一流的诗、第一流的文学。“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它不是“轻薄为文”者流所可了解和信口雌黄的。但是在这些政治诗当中,汪精卫的那首“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只是喊喊革命口号,不够传统诗评中的所谓温柔敦厚也。至于毛泽东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鸟儿问答》),那就是转型文学中,地道的放屁了。
在笔者的谬见中,我却十分看重袁寒云这首讽父诗。这位“假名士”的作品,实在不是和他同时的“南社”之中的数百个“真名士”(像易实甫、樊樊山等人),无病呻吟、搔首弄姿的作品,可以望其项背的。这当然是读诗人各有所喜的偏见,但是我想读者贤达中,或不无偏见同调也。为与海内外同好共品之,谨就个人记忆所及,将青少年期就能背诵的“假名士”的讽父诗,七律一首,抄录如下: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寒云这首讽父诗的重点是最后两句,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其他六句都是搭配的,所以上六句,他嫌配角不好时,就换来换去。笔者在青少年期所读的寒云讽父诗,至少就有两种。上录为个人可以背诵,而比较喜欢的一首。下面一首则是在上引袁静雪忆父文中发现的。二者略有不同。并录如下:(见本刊三三八期页一三○)
「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其最后两句都是相同的,只是其他五句有别。是所谓“推敲”。推敲出新的灵感和音韵来,对旧作又不肯“割爱”,就多首并存了。这也是一般“下几十年功夫”的,旧律诗作者的通病。也是他们彼此在诗坛见高下的标竿。“南社”当年解体的原因,便是宗黄(仲则)和宗郑(孝胥)两派争执不休的结果。胡适对旧诗的欣赏,显然便是倾向于“宗郑”的。
毛泽东那首“占领南京”的七律中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联,他的老师胡适就说他“不通”。不通的原因就是他的文学“境界”太低,作律诗的汉学底子也不够。作律诗重在“推敲”,而毛公的推敲本领,也只能到此为止,所谓“黔驴技穷”也。下棋的人有句话叫做“棋高一着,逼手逼脚”,其实做旧诗词,也是如此的,所以毛的旧诗词,尤其是那有限的几首“七律”,在宗黄、宗郑的两派诗人的眼光里,就诗论诗,就只能算是“登堂矣未入室也”。所以柳亚子说,“(诗)儿子毛泽东”,就诗论诗,并不是什么吹牛也。但是在“诗歌转型”期中,毛公诗以人传,写旧诗能写到“平仄无讹”的程度,也就算是难能可贵了……。笔者原只是评那位青帮老头子、“假名士”袁寒云的讽父诗,为何又把毛主席请出来糟蹋一番呢?无他,毛主席太有名嘛!所谓毛主席的诗词,全国同胞至少有上千万的人可以背诵吧,讨论袁世凯儿子的诗,把毛主席家喻户晓的诗也找出来,比较比较,就容易说明了,不是笔者故意要和毛主席过不去也。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以上所说是当时反帝制文学中的“反帝诗”,可圈可点的一首高级作品,竟出于“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云楼主自嘲的笔名之一),故访录之,以与有文学兴趣的读者,共赏之也。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汉学底子”是江河日下了。今日吾人发政治牢骚,就只能搞搞“顺口溜”了。当然今天的新诗人,也还有以新诗形式来代替顺口溜的,但是新诗界以外的读者,就很有限了,虽然翻成外文却可以引起国际属目。
袁氏帝制时,反帝论文,也是雪片横飞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当然就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那一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而有深远影响的佳作了;为保存史实,不能不简略述之。梁氏在此万言长文上,他第一要把“国体”和“政体”的界说弄清楚。他说“共和”与“君主”国体也。而“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也。如今君宪救国论者,认为只有“君主”才能“立宪”,而“共和”就不能“立宪”,是何种逻辑呢?
第二,若说国情,继承式的君主立宪,比非继承式的共和立宪,更为适合于中国,则现行的《大总统选举法》(见上章的金匮石室制),不是既能传子,亦能传贤,岂不更优于帝制乎哉?何必改变国体?
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国古德诺顾问之言,奉为圭臬,要据之以恢复帝制,废弃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当他为维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人士论战时,所阐发君主立宪之精义,实十倍百倍于古德诺之所言。(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时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论确较古德诺之短文精辟多矣。历史家可为佐证也。)而当时诸公(包括筹安会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对我梁氏之言,充耳不闻;梁氏之书,过目不读,岂因“吾睛不蓝,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当年为坚持君主立宪制,曾为共和人士所诟病,今日要推翻中华民国,翻为当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为维护共和国体者,翻为当年的君主立宪派,亦可怪矣。
最后,梁说他原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并无理由要为共和制度做辩护人,他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革命得不偿失。可是当时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民国成立四年以来之所以糟乱若此,便是当年共和人士不听他的话的报应。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而当年的翻云覆雨之士,又要再来覆雨翻云,乱来一泡,民不聊生,国亡无日,不难预测也。今日之动乱,已充分证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虚。“十年以后真知我”,梁氏以“常带感情”之笔痛诋筹安会中之众莽夫说,尔等今日不听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总统拖下粪坑,与尔偕亡,十年后将再知吾言之不虚,而追悔莫及。尔曹其毋河汉余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余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己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原是我国文学转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笔端常带感情。他的鸿文钜著,一经京报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