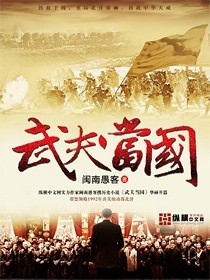袁氏当国-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个造反成性、认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一九○七),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舢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孙公那时在炮火中作战之勇猛,后来竟吓得在一旁发抖的蒋夫人陈洁如女士小便失禁。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呢!本质上他老人家也是一条“砍掉头,碗大疤”的梁山好汉呢!他也是个列宁式的英雄。为着革命倒袁,啥鸟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因此在这“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和战两派并没有一致的政策,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却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所驳回,许认为不向地方法院起诉,而另组法庭,是干涉司法独立。可叹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动之下,为组织“政党内阁”,这时北京的国务员,自赵秉钧总理而下,当然包括许氏,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对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就授入以柄,让袁总统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动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儿科了。他们没有大兵可调、地盘可据,却在武汉市内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动,被黎元洪破获,说他们是“谋刺黎副总统”,报入中央,而大开杀戒,党人宁调元、熊越山等被捕,后来都被枪毙了。总之,国民党内议论未定,袁世凯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战争的空气正弥漫全国之时,袁氏也早就调兵遣将,着着进逼,准备动武了。
【善后大借款,不能善其后】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事实上打政治麻将,则鬼更多矣。在这场袁、孙两派的政治麻将里,孙党就手气奇差,简直没一张好牌;而袁党则手气大佳,好牌不断涌现。当老袁决定对国民党动武时,忽然来个“杠上开花”,他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了两年的善后大借款,这时忽然马到成功,由六国中的五国(美国退出)联合借给中国政府两千五百万金镑,合两万万银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迫不及待的便于四月二十七日,未经国会表决,就正式签字接受了。这消息一出,袁党军心大振,而国民党则全党大哗,认为是非法借款,发动内战,党人领袖与参众两院议员,亦函电纷飞,抵死不能承认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讨袁的口实。其实当年各省都督,仅有四省反对借款;向通电赞成者则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年后,恩怨已断,历史家秉公以论之,借款案与刺宋案一样,也是个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之内,两造律师在法律之前也是争辩不尽的。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迨孙公解职,把这烂摊子转让袁公,眼看纵是南京留守一个衙门,裁兵之需即为二百五十万元之钜。孙公解职让袁,岂不真是无官一身轻。后来在孙、袁蜜月期中,中山为袁的经济困难,借箸代筹,也认为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是那时列强环伺,都以借债为蚕食中国主权之不二法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何等复杂,我政府应付之道,稍一不慎,便丧权辱国。笔者昔年曾为此乞教于曾任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的顾维钧先生,以及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和江浙财团首要的张公权先生等,试图探其奥秘,谁知所钻愈深,愈不见底。盖外债一项,不特牵涉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朝野公私的各种建制,深不可测,其在债权国家,各帝国主义之间朝野公私的纠结亦不在债务国之下。稍一深入探索,则三五百页之钜著,未必能见其项背也。有暇当列专章略探之,在本篇中,我们只可说,袁党这个大赌客“手气好”,在他正需钱打内战时,交涉经年的善后大借款刚在此关口签字。原来本为善后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后,也是国运多舛吧,夫复何言。(为了解善后大借款的大致经过,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一四六~二六○,“善后大借款”。)
【第二次革命,第一次内战】
总之,袁、孙两党的对峙至此已剑拔弩张,正如早年的美国内战(一八六○~一八六四),蓄势已成,就看谁开第一枪了。林肯是个聪明人,他等着(甚或是以调兵遣将行动引诱着)南方来开第一枪。一枪既发,他就以国家元首之尊,为维护国家统一,下令讨伐了。林肯这个狡猾的手腕,后来又被罗斯福学到了。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氏深知美日之战不可避免。但他格于国内孤立派之反对而不敢公开叫嚣,只有制造战争形势,希望日本小鬼来开第一枪。谁知他手腕玩的太灵活了,连中国给他最机密而可靠的日本发动战争的情报,他也故意的延宕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吃了珍珠港那个大亏。但是,朋友,美国是吃了大亏了,日本开第一枪的代价就更大了。非关本题,暂时打住吧。
我国民初的二次革命的形势也是如此的。他们那时转型还在初级阶段,打内战还不知啥叫保密。中山的叫嚣联日讨袁的种种“策略”,应夔丞阶段的特务虽然很原始,这点情报袁党还是有的。至于袁的调兵遣将(他把李纯精锐的第六师于五月初自保定南调武汉,另调精锐从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开的了。而国民党此时,黄兴的主和派的声音,已早被中山主战派的叫嚣所淹没,战争形势已成,这时国民党还在宣传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则中山的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又何尝“合法”?大家都无法无天,那就由枪杆来决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实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打他们个一千次了。第一次是个“偶然”一千次就是个“必然”了。小民何辜,罹此百年浩劫,也是命运使然吧。
【国民党扫地出门】
当然这第一次内战,强弱势殊,袁世凯这民国史上第一位强人,此时是采取主动的。六月九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部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继之粤督胡汉民(十四日)、皖督柏文蔚(三十日),亦相继被免。同时黎元洪在武汉亦大捕地下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时粤、皖两省党人,皆有窝里反,胡、柏二人虽心有不服,还是遵令去职。李烈钧因在江西掌握较稳,被撤职心有不甘,乃潜沪与中山密商之后,又潜返江西湖口,约集心腹同志,及武汉避难党人,密谋起义抗袁;举棋未定,李纯已受命为九江镇守使,率军步步进逼。李烈钧不甘示弱,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鸣炮,公开起义讨袁,打响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附注:这第二次革命和民国开国后的第一次内战,便带有严重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色彩。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种“回避”的制度。如汉制便规定,本郡人不能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所谓“制衡制”,是很科学的。此制断断续续地实行,两千余年末尝废。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抚的传统制度。所以再有清两百余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后,再未发生藩镇割据的现象。民国成立之后,首先就把这一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民初各省都督几乎全是本省人。这就开启了本省军阀盘据本省的恶例了。国民党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们闹窝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广东,那时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将: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广东人。二人不和,弄得两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钧掌握得比较严密,窝里反问题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为着革命的利益,显然没有他们抗拒“北军”(客军)心情的严重。其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蔡为湖南人而任云南部督),对此日益滋长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虽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时他却助袁,通电痛斥李烈钧“以前行为,本难宽忍”。(见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云南蔡锷艳电》,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一四四。此电在原书中误印为一九一五年)。此一区域主义,后来竟滥觞于军阀时期。至台湾而变本加厉,可悲也。〗
这时愤恨袁氏专权,或仅为不满现状,欲为自身另找出路的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义旗一举,各地也纷纷响应。民党的老巢在江西、广东、安徽、上海,固无论矣。纵在较北的徐州驻军之内,也不乏反袁义士。须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并没有它自己的军队。它所有的不是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正规国军,慕义投靠,就是地方杂牌民军,就食而来,他们的战斗力和纪律,有时且远不如老的“北洋六镇”。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说的“驱市民为战”。不但战斗力有限,而军纪之败坏,亦不下于“北军”。加以弹械粮饷皆缺,又师出无名,士气不振,上海由陈其美指挥,连个制造局亦屡攻不下,徐州、广东、湖南一触即溃。稍微能坚持一二周者唯湖口与南京两处,伤亡溃败亦惨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军起义,然由于苏督程德全首鼠两端,弃职潜往上海,孙派之激烈军官何海鸣等确有意死守南京,苦撑待变。中山亦曾有意亲临指挥,终以黄兴抱奋勇而来作罢。然黄氏觉事无可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从安徽战场败至南京,曾痛批黄兴为“一将无能,千军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实觉孙公之发动二次革命,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对麦帅有意侵华之评语曰:“斯为一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错之战争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on a wrong place,at a wrong time)焉有胜利之望?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墨,国民党全党上下,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全盘失败。孙公就要调换方向,“以俄为师”,去搞独裁专制了。袁公早就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见他和顾维钧的对话),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今从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于美东新泽西州〗
四、中山要做独裁党魁,袁氏先做终身总统
发生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墨,一败涂地。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一大里程碑。此话怎说呢?原来辛亥革命的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不幸这个“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注意:不是“破产”,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的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做“进步人士”吧——他们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保皇党”的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national concensus),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上述数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转型运动的启蒙期。在这启蒙期中,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是个“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他们对所谓“国体问题”,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慧(wisdom)和机运(chance)。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有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我们大致也可给他们戴顶帽子叫“吵闹的少数”(a quarreling minority)吧。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海峡两岸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转型进展中的“阶段问题”,阶段不到未可蜡等也。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现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