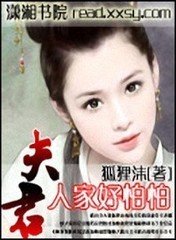河套人家-第5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虎仁疑惑地看着她。
她妈也沉人了迷雾中,愣愣地盯着她。
“爹。”引弟低下头,难以启齿。
“引弟,你这是咋啦? ”李虎仁心中的疑团迅速扩大了。
引弟鼓起勇气,口齿清楚地说:“爹,你那天看到的是……”
“谁? ”父母异口同声。
“我……”
“你? ”
“对,我,还有……”
“还有谁? ”
“二青。”引弟说完,掉转身,跑出了屋子。
李虎仁和女人交换了一下异样的目光,他噌地坐起来,忽然哈哈大笑:“狗日的,真个阎王叫鬼捉了。”
他明白了一切,一切都明白了。他的病也自然而然地好了,他又有点老羞,那会儿,他对成波女人念叨的那些见不得人的话,不知引弟和二青听去了没有?
女人惊喜地说:“你没病了? ”
“还病甚呀? 便宜了苏神官! ”这会儿,真相大白,他又心疼给苏凤池的钱物了。
女人一叠连声:“好了就好。”
“赶紧闹口吃的,饿死我了。”李虎仁开始抽烟,招弟被拘留带来的不安和烦恼先放在一边。着急也没用,生米成了熟饭,慢慢吃吧。
女人手忙脚乱地生火,滚水。
这时,从外头走进来两个面生的中年人,直杵杵进了家,其中一个说:“你是宝弟的老人吧? ”
李虎仁满心不快:“干甚? 这又不是车马大店,说进就进来了。”
“老人家不要生气,我们是来要账的。”另一个嬉皮笑脸地说。
“要账? 谁短下的? ”
“宝弟,你儿子! ”
“放屁! ”李虎仁勃然大怒。
来人也不恼,向他展示了一个纸条:“押上骡子一头,李宝弟……”
“他赌输了,这个骡子,就是我们的了。”来人从容不迫地说。
李虎仁跳下炕,一把揪住其中一个的领口说:“好呀,你们教会我儿子赌博,还挺有脸面哩,敢打上门来要账。”
三个人撕扯起来,引弟和她妈又喊又哭。
引弟妈急中生智,吩咐引弟:“快去叫刘村长。”
引弟赶紧跑了,这边的三个男人在地上滚成一团,叫骂声喘息声纠缠在一块。
李虎仁气得七窍生烟。
3
宝弟这两天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他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精神委靡,心灰意懒。
地里的营生,他根本不想干,父母也不敢多指拨他。
白白告诉他,从从的“思想工作”不好做,他跟从从当头对面说了一回,效果也不理想。成波女人一死,对从从来说是“瞌睡给了个枕头”,最大的障碍不存在了,宝弟对从从抱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村子里有几个游手好闲的光棍,拉他去赌博“讨宝”,他一沾手就上了瘾,通宵达旦地干,不知是手气不行,还是心情不好,反正是输多赢少,把他大姐给的二百多块全抛了进去。
这天一觉睡到半后晌才起来,脸也不洗,头也不梳,一脸土气,浑身臭味,点根烟,吧吧地抽。
李虎仁自顾不暇,没工夫管他。母亲心疼儿子,赶紧在挂面里头卧了两个鸡蛋,招呼儿子吃。
宝弟无精打采,稀里哗啦吃完,一抹嘴,就往外走。
引弟在东屋里看见他,把他叫住:“宝弟,你过来。”
宝弟稍一迟疑,慢慢腾腾走到她屋里。
“看你成了甚样子啦! ”宝弟的憔悴,使引弟又惊讶又心疼,“白衬衫成了黑的。给,哪天进城,去买件新的。”
引弟拿出二十块钱,按在他手里。
“我不要,二姐,你又没收入,我不花你的钱。”宝弟看她一眼说。
引弟扑哧笑了:“我叫你花你就花,寡话少说。”
宝弟把钱装上,仍然闷闷不乐。
“宝弟,你碰上甚烦心事了。说给姐听听。”引弟拿把梳子,梳理他乱草似的头发。“你照照镜儿,成了甚样子了。”
李宝弟叹口气,又摇摇头。
他不想让二姐为他操心,她自己还不够麻烦的吗? 他不知道,引弟的地平线上,正在冉冉升起一轮红日呢!
“咋? 不能叫我知道? ”引弟在脸盆里拧了一块毛巾,“给,把脸擦一下。”
宝弟草草地抹了两下,就把毛巾放在脸盆架上,这时,他才认真看了看二姐,不禁使他暗暗吃惊,二姐可今非昔比了,她完全恢复了从前风韵动人的丰采,目光清亮,面颊微红,过去笼罩在她脸上的愁容,被神采飞扬代替了。
“二姐,你……”他不知该问什么。
“我咋啦,宝弟。”引弟含着笑,嘴角微微往上歪,挑出一个俏皮。
“我看二姐,变了。”宝弟只能这样说。
引弟格格地笑。
宝弟莫名其妙。
“宝弟,我把苏神官治住了。”引弟一副扬眉吐气的样子。
“咋治住了? ”宝弟好奇地问。
“……一块手绢,把苏阴阳闹得疑神疑鬼……”引弟把经过告诉他,宝弟恍然大悟,“原来那块手绢是二姐的呀! ”
“咦,你咋知道? ”引弟感到诧异了。
宝弟笑了笑说:“二姐,你能治住苏神官,还得感谢我和丕丕呢! ”
“你们俩? ”
宝弟点下头,把手绢的事一说:“奇怪,它咋又回到你手里头了,二姐,谁给你的? ”
引弟的脸红红的,小声说:“是二青。”
“噢,”宝弟一拍脑门,“我想起来了,那天成波女人死了,对吧? ”
引弟点点头。
“二姐,二青咋知道手绢是你的? 上头又没名没姓的。”宝弟用调皮的目光注视她,心里明白了一大半。
“他,猜见的吧! ”引弟别过脸,嘴角漾着笑影。
“哈,他好猜手,乘我和丕丕不注意,他就把手绢偷上走,送了人情。不行,我得去问问他,咋能猜到,手绢就是你的! ”
说完,就往外走,引弟一把拉住,说:“不能问。”
宝弟故作惊讶:“咋不能? 手绢又不是他闹到的。”
引弟把他打了两捶:“你快不要装神弄鬼了! ”
宝弟哈哈大笑了,这些天,他还没有开心地笑过。
“二姐,二青跟你好上了,对吧? ”他一本正经地问。
引弟红着脸点点头。
“二姐,他是个好后生。”宝弟情绪变得低沉了,“你有福气,有人爱你! ”
引弟吃了一惊,从弟弟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
“宝弟,你看上谁家的女子了,二姐去跟她说。”她猜测到了弟弟最近丧魂失魄、无精打采的原因。
“从从。”宝弟一语道破。
“从从? ”引弟讶然反问。
“从从。”宝弟肯定一遍,摸出烟点上。
他不想隐瞒,也没有必要隐瞒。为了这个女人,他陷入了苦恼的深渊。他甚至恨恨地想过,那回去广州,早知从从叫什么经理好活了,还不如他先下手呢。
引弟的手放在弟弟的肩膀上,反复地念叨:“从从,从从……”
“二姐,我就看上她了! ”宝弟痴痴迷迷地说。
“她呢? ”
“她跟水成波好。”
“你说甚? ”
“她看上了水老师。”
引弟的惊诧和迷惑,都写在脸上。
“真的,千真万确。”
“你咋知道? ”
“从从跟我说过,我也亲眼看见过。”
“看见过? ”
“从从那天把我当成了水老师……”
“那你还……”
“二姐,这种事能由人呀。”
引弟深有感触地点下头。
是的,人爱人,人想人,不由人,她想劝劝弟弟的念头也随之打消。
大路弯弯小河多
这种事不由你和我
苏凤池的山曲儿,早就下过定论了。
“那你也不要糟蹋自己,往开想哇。”引弟明知开出的药方不会有什么用。
“唉! ”宝弟长叹几声,从这儿走出去。除了耍钱,可以使他全心身地投入,忘掉一切地投入,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发现,这些日子丕丕也不像原先那么欢天喜地了,眉头拧了一个圪垯,走路踩着自己的影子。
有一次,他在丕丕家,两个人喝了一气闷酒,索然无味。宝弟建议赌钱,丕丕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两个人各怀心事,形影不离。
宝弟从家里走到村子里,向田家方向张望,看见丕丕正从院子里往外走。
在村子路上,两个人碰了头,一块往赌场走。
丕丕说:“我爹叫我进城看对象,我说行,他给了我二百块钱。”
“那你不去吗? ”宝弟疑惑看着他。
“我又不是没对象……”
“你有了? ”
“有了。”
“谁? ”
“月果! ”
“她? ”
丕丕点下头,又唉叹一声:“这几天,她又不理我了。”
“咋回事? 女人的心是咋长的呀? ”
丕丕不便说出因为月果大爷爷的事,闪烁其辞:“嫌我……”
“咋? 你下手了? ”
丕丕不置可否地笑笑。
“哎呀,你这个小叫驴,真吃上青果子了? ”宝弟拧着让他交待,“甚滋味? ”
“咱能干那号事? ”丕丕言不由衷地笑着。
“那月果嫌你什么,总不能嫌你一表人才,家境又好,又亲她哇。”
“唉,谁知道,女人真难琢磨呀! ”
宝弟应了一个叹息,他不再往下问了。
他心里亮亮的,人家丕丕跟他的苦恼不一样,人家的关系,早越过警戒线了,说不定,早把“子”给月果种上喽。
不像自己,纯属剃头担子——一头热,不要说亲热一下,连句好听的都没有。
这个女人,又是丕丕的姐姐,叫他咋说呀?
两个人不做声,一直来到赌场。
这是间孤独房,离四邻挺远,住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光棍。
家里几乎没有什么摆设,一条大炕上,只有一块羊毛毡,剩下的大半个光炕,正好做赌摊。
宝弟和丕丕一进来,门就关得黑贴贴的开始押宝。
宝弟一连几天不顺,连手表都贴进去了。今天想狠狠捞它一家伙。
一注,他就把二十块钱全放上去了。
这赌场上的变化,也让人神鬼难测,何况其中又有多少窍道、诡计、花招、圈套,丕丕和宝弟阅历有限,哪能掌握。
只见输来不见赢
输得眼红就偷人
这是赌徒们的必由之路。
又输了,宝弟心急上火,向丕丕借了五十块钱,又一回押上。
可能为了“诱乱深入”,欲擒故纵吧,这一回,宝弟居然转败为胜,而且一连几庄下来,捷报频传。
宝弟喜形于色,把几天输出去的差不多全捞回来了。
赌场上的不成文法,输了可以一走了之,但赢家却不能席卷而去,必须再干下去,宝弟只能再接再厉。
宝弟还了丕丕的钱,两个后生越战越勇,到了晌午,主人做了饭,让他们吃,还供上烟。
这一切都不是免费的,一切开支,都在主人的“抽头”里。
宝弟和丕丕手气很好,赢得扬眉吐气,输的垂头丧气。
好像午饭是分水岭似的,宝弟和丕丕再干下去,战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不到两顿饭的工夫,赢的钱全部又回到人家的口袋里去了。
两个后生不服气,又向人家借了三百元继续赌,结果,形势依然对他们不利,不一会儿,又赔进去了。
宝弟和丕丕红了眼,都脱了背心,赤膊上阵了。
“再借二百! ”
两个人异口同声说,汗流浃背,嘴脸变形。
主人说话了:“后生,这钱,你们借下,拿甚还? ”
宝弟略加思索,说:“拿我家的骡子顶账! ”
丕丕不如他胆气壮,畏缩了:“那我不干了。”
主人说:“不干也行,刚才借的钱要立下字据。”
丕丕给人家打下欠条,脑袋夹在膝盖间,完全一副败军之将的沮丧样子。
宝弟气壮如牛,立下了骡子顶账的字据,还按上了手印。
丕丕说:“宝弟,我去尿一泡。”
他走出来,再没回去。宝弟也没留意。他的手臭极了,一头骡子,连皮带毛全输了进去。人家拿上他的字据去牵牲口,还不让他走,当人质扣住,宝弟已经精疲力竭,倒在土炕上睡着了。
要账的人气急败坏地回来,没有牵上骡子,还差点叫刘村长送到乡派出所去,几个人把睡梦中的宝弟提溜住,劈头盖脸一顿好打,宝弟孤掌难鸣,出击不力,不一会儿,就不省人事了。
人家把他拖到屋子外头,扔在一边,把门一锁,扬长而去。
脸青鼻肿的宝弟直到天黑才苏醒过来,腰背疼痛难忍,爬也爬不动。
第十三章
她的天塌了,她的地陷了。
刘改芸死人一样躺在炕上,已经两天两夜了。
这个家,也真成了坟墓。被水汇川救下的刘玉计比死人多出一口气,嗓子坏了,只能呜呜地哀号,在苏凤河兄弟的帮助下,刚刚把改芸妈下葬,点过的纸灰,还在院子里堆着,叫人毛骨悚然。
刘改兴成了半大老汉,面容憔悴,两眼红肿,他顾了父亲顾不了妹妹,焦头烂额,痛不欲生。
他不能倒下去,这个家里,只剩下他一个还算完整的人了。母亲匆匆地走了,急促得让人疑惑,她究竞走了没有,也许是去串亲访友,过几天就回来了吧。